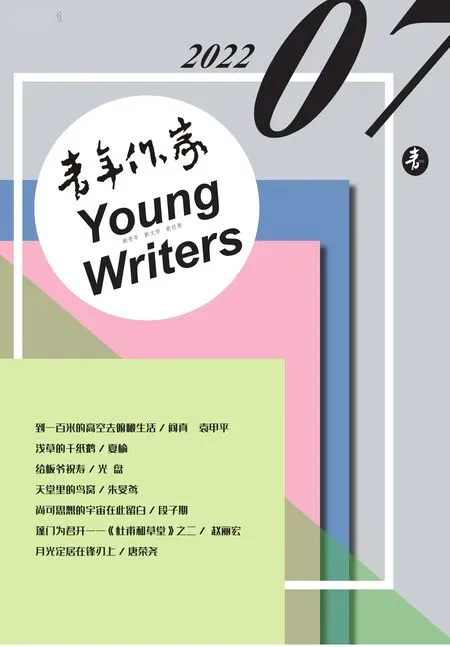讀閑書
四川省什邡中學高2018級 胡雨馨
最近在讀夏目漱石的《草枕》,讀到這一段:“過于理智會與人起沖突,感情用事則無法控制自我,堅持己見易鉆牛角尖。總之,人世難以安居。
難以安居到某種程度,就想搬去容易居住的地方。醒悟無論搬去何處都不易生存時,便產生了詩詞,出現了繪畫。
創(chuàng)造人世的不是神也不是鬼,是同樣在鄰里之間四處走動的普通人。普通人創(chuàng)造的人世難以安居,卻也沒有別處可以搬遷。如果真有也只能去非人之地。非人之地恐怕比人世更難安居。
難以安居的人世既然無法迂離,則無論多么難以安居,都得秉持寬容,讓短暫的生命在短暫的歲月過得更好。”
《草枕》的主人公離開“人世”,去往“非人世”,結草為枕,只為在非人情的天地里遨游片刻,我不禁想,人世難以安居,非人世更不可久住,那么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哪,現在找到了。
我想我以后會過半與世隔絕的生活,過有趣的日子,遇見一些有趣的人,創(chuàng)作一些好看的衣物,在一個繁華城市的偏僻小角落擁有一間小小的工作室,三餐能夠溫飽,不吃大魚大肉,但嗜辣這個癖好可能是改不了了。
閑時坐上車,去往市中心看一些有趣的展覽,回來時挑上兩三本書,放到桌上,得空了能翻幾頁,房間的燈不能太亮,昏黃就好,照亮屋內一角,太亮會讓人難為情,創(chuàng)作就無法進行,就像一個人可以在臥室穿很少的衣物,卻不敢在客廳同樣穿著,即使客廳無人,窗簾也拉上。如果每個角落都被照亮,思想就無法安放,靈感剛產生就被扼殺,尋不到一個幽暗的角落可以繼續(xù)生長并最終成形,就好比人站在水泥地上受太陽暴曬,哪兒還會有半點詩意,再美的心境也給破壞了。
叔本華也說,一覽無余不是美。
我大部分很荒誕的想法來自閱讀,從前也讀過很多書,大部分是小說,而我就像做語文閱讀一樣從來找不到重點,真正發(fā)現有些思想開始改變,大概是前年讀《夏摩山谷》的時候。那是第一次除言情小說外的一本書可以感動到我,初看時不太懂,其中很多關于佛教和宗教的概念都很陌生,看了五六遍才盡興,后來又買了她最受好評的《蓮花》。慶山在《夏摩山谷》的后記中寫道:“如果說十二年前的《蓮花》是一次朝圣的出發(fā)姿態(tài),那么對《夏摩山谷》來說 ,它是一條深入的路途。”我不幸地剛好搞反,所以并沒有體會到其他讀者初讀《蓮花》時的驚艷與震撼,遺憾啊。
感受到想要繼續(xù)閱讀的急切,受我很喜歡的藝術家的影響,買了黑塞的《悉達多》,看完感觸頗深。
悉達多,喬達摩王子,釋迦牟尼佛的前身。與其說黑塞是在描寫佛陀成為佛的一生的探索,不如說悉達多就是我們每一個,聽從靈魂和內體的安排,去經歷罪孽,卷入無盡的漩渦中,以學會放棄掙扎,不再將這個世界與所期待的、塑造的圓滿比照,而是接受這個世界,愛它,屬于它。
悉達多與喬達摩本是一個人,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但黑塞卻把他分開成兩個人,喬達摩已是活佛,而悉達多仍在流浪,悉達多甚至離開喬達摩去尋找屬于他自己的真理,我至今還未弄清楚原因。
后來又讀了《西藏佛教密宗》《西藏度亡經》《西藏生死書》一系列關于佛教的書,認識了他們關于生死、輪回、功德與頓悟的概念,但我不信輪回因果之說,或者說我認為沒有來生沒有任何意義,來生的我不會是今生的我,即使今生種下的因來世結出了果,承受業(yè)力的也是另一個生命而非我,既然靈魂記憶世世被清空,那么執(zhí)著于輪回轉世還有什么意義?
再談談我讀的詩吧。提到詩,一定得說說木心先生,他金句頻出,實在是太有趣了,常讓我忍俊不禁。最喜歡的還是倪湛舸,她每首詩都有一種奇異的畫面感,是我讀過的其他詩沒有的,每讀她一首詩,就會受一次啟發(fā)。我愛花木染,把花木茶墨組合成新的顏色,再加以褪色、縮水,布料最終呈現出跋山涉水、飽經風霜的模樣,其中涉及日本幾大美學概念之一的“物哀”,也是我最喜歡的設計師pengtai所有設計的靈魂所在,所以她的詩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無可取代。
也讀過倉央嘉措的詩,最喜歡這幾句:
“曾慮多情損梵行,又恐入山別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人生在世如身處荊棘林中,心不動則人不妄動,不動則不傷;如心動則人妄動,則傷其身痛其骨,于是體會到世間諸般痛苦。
如《大寶積經》所言:一念妄心才動,即具世間諸苦。如人在荊棘林,不動即刺不傷;妄心不起,恒處寂滅之樂。一念妄心才動,即被諸有刺傷。意為:人在世間時時刻刻像處于荊棘叢林之中一樣,處處暗藏危險或者誘惑。只有不動妄心,不存妄想,心如止水,才能使自己的行動無偏頗,從而有效地規(guī)避風險,抵制誘惑。
佛家將心放在第一位,強調心性的重要性,認為眾生皆有佛性。凡夫心像被風吹的燭火,搖來搖去,暴躁,易怒,充滿欲望和謀求算計,易沉溺在自己創(chuàng)造的極端情緒里無法自拔。心性藏語發(fā)音為“rigpa”,指本初的、原始的、純凈的覺知,萬事萬物皆具備心性,佛心被凡夫心蒙蔽,使世人愚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