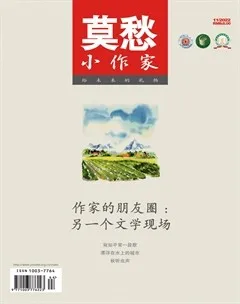風行荷上
紀太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著有《多少墨香》等作品。曾在《美術》等專業核心期刊發表數十篇論文。擔任中外多所高校兼職、客座教授、碩導、博導。擔任二十余家機構的藝術品投資顧問。
心里有燈
有人曾笑言,說紀太年的畫有安神之功效。這話不虛,我們站在他的一幅四尺工筆畫前,觀之十來分鐘,便覺得整個人都安定下來了,神清氣爽。紀太年的工筆畫自成特色,在業界所獲贊譽頗多,但其實這只是他的業余之作,他的主業是美術評論和藝術品投資,出版相關作品五十多部,被媒體譽為“藝術品投資的風向標和規劃師”。
每個人的精彩時刻都不是偶然得來的,更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一定源自深厚的精神底色,追根溯源,總能在原生家庭里找到對應的點。
母親,是紀太年在聊天時提及最多的一個高頻詞。他說:“我母親對我影響很大,我的生活、為人處世的方式,基本都有我母親的影子在其中。”
從紀太年的講述里,聽到了一個個閃亮如珍珠的小故事,那是母愛善良、智慧的光輝,像啟明星一樣懸在頭頂,給他指引和方向;又像冬夜的暖手爐,藏在懷里,藏在貼近心臟的地方,讓他無論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暖和、踏實。
母愛,這是紀太年心靈里的燈火,將他的人生照得亮亮堂堂。
一字千金,何不用心
紀太年有兄弟姐妹十個,他排行老八。父親曾經擔任過鎮上一家單位的負責人,母親略通文墨,這是個和睦的大家庭。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理念高度一致,凝練成八個字,那就是:一字千金,何不用心。意思是,既然讀書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事,當然就要盡心盡力把書讀好。
父親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但他有個習慣,就是過年基本不買年畫,把白墻留出來貼孩子們捧回來的獎狀。一面白墻的期待,就是對孩子們無限的信任和鼓勵,兄弟姐妹們由此爭先恐后地去讀書,那面白墻就是孩子們心目中最好的光榮榜。
父母親不但要求孩子們好好讀書,自己在生活當中也是處處勤學好問,母親做飯炒菜時最喜歡喊上老八來做幫手,因為老八看書多,能把書上的故事講給母親聽。無論老八講什么,母親總是聽得津津有味,總是聽不夠,總是喜歡不斷地問:后來呢?后來怎么樣了?
在母親反反復復地追問下,紀太年只能不斷讀書,及時更新肚子里的故事儲備,甚至有時還要現編現講。采訪紀太年時,我見識了他的這種說故事的本領。我們從早上八點半開始,一直到晚上八點半收工,他一直在不斷地講,表達生動,細節嚴謹,涉及具體的人名和時間,一口報出,熟稔且準確。
不同于那些畢業于美術院校科班出身的畫家,紀太年四十多歲時才開始握管作畫,一出手,竟然不同凡響。這里面有什么竅門嗎?
世上并無憑空而來的奇跡,人們所看到的鉆石在高光時刻的璀璨光芒,背后都有一個千磨萬擊的雕琢過程,人的成長、成才、成功也一樣。
紀太年說:“一是不斷讀書;二是謙虛地多向大家學習;三是找到適合自己的風格,在繼承中創新。”正因為虛懷若谷,勤學苦練,紀太年形成了獨特的畫風,清凈素雅而不單調,自然生動而不僵化,鮮活唯美而不凝滯。
這樣的畫風何來?紀太年認為是他多年讀書所致。文化修養是一種綜合因素,除了大量的閱讀,還有父母從小給予的熏陶,也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所帶來的淬煉,這些元素交織成廣博的知識體系支撐起他的“仙氣”,仙氣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在煙火人生里堅守著蓮花般的高貴品格。
那天看紀太年作畫,勾線時他在墨中加了一點花青,毛筆尖軟軟地蘸一點水,將花青與墨揉融調和,那一點花青在一團墨色里毫不顯眼,但一落到宣紙上,卻有了一層縹緲之氣。
紀太年說,如果畫暖色調的畫,他會在勾線的墨里加點胭脂,以增添一抹亮色。說著他一笑,說這些都是自己的奇思妙想,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
這么多年,紀太年始終保持著內心的寧靜恬淡,每年五分之二的時間用在讀書上,五分之一的時間用在交游上,五分之二的時間用來寫作和畫畫。他看的書特別雜,說:“很難說哪本書對我們有用或者沒用,有時就連《本草綱目》也會拿來翻翻。”是的,母親當年的那種“后來呢?后來怎么樣了呢?”式的追問,是他閱讀的最初動力。哪里敢有一點松勁呢,一刻不讀,便無以言對生活中不斷出現的形形色色的“追問。”
嘴上裝根拉鏈,可保一生平安
在兄弟姐妹的記憶中,父母從來沒有吵過架、拌過嘴。
母親總是面帶微笑,手腳忙個不停。無論遇到什么事,她從不在孩子們面前唉聲嘆氣。
日子不富裕,但因為有了母親臉上的微笑,家里始終洋溢著讓人心思安定的氛圍。
母親有著樸實的平凡生活的智慧,自律、善良,懂得感恩,無論境況如何,這些為人的根本,母親始終不會改變。她很少串門,不打牌,不拉呱,不讓自己陷入是非窩,東家長西家短的事她自覺回避。她的理論是:禍從口出,嘴上裝根拉鏈,可保一生平安。
紀太年的為人處世之道得到了母親的真傳,藝術圈子不是一塊凈土,但紀太年始終堅持“可以有學術上的爭論,但不言他人是非短長”,信奉藝術至上。因為他在美術評論界的地位,被媒體譽為“藝術品投資的風向標和規劃師”,所以常常有人讓他對某些人、事發表看法,比如有收藏家高價買了幅蘇東坡的帖子,一位學者說這是用雙勾添彩的方式造的假;另一位學者說這是真跡,因為沒有找到雙勾線的痕跡。媒體找到紀太年,讓他對此發表看法。紀太年信奉的是:不要為了嘩眾取寵,去對超過我們認知范圍的人和事指手畫腳。
“一個人能成氣候,一定付出過許多不為人知的努力,不要嘴皮上毀人。”這是紀太年為人處世的信條。人的一生中,難免會遇上兩種人,太陽人和刺猬人。太陽人給人溫暖和智慧以及力量,而刺猬人是會傷害人的,會以疼痛的方式教會我們學會生活。紀太年是個厚道人,交談時他所講的都是太陽人的故事,而沒有涉及任何一個刺猬人的往事。不是沒有遇上過,而是選擇了遺忘。這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為人之道。
所以,九十高齡的著名工筆畫大師喻繼高先生對紀太年特別欣賞,多次當眾說:太年這個人是少見的好,不站隊,不惹是非,把精力都用在了業務上,非常好。
地掃干凈了,屋里就亮堂了
一家大小十來口的生活全靠母親一人張羅,要操心的事情非常繁雜,但只要稍稍得了空閑,她總是安靜地坐在窗前,爭分奪秒地納鞋底、縫補衣服,手藝在周圍是出了名的好。
母親始終是以一種安詳的心態來面對生活,她說:“動嘴不如動手,盆子里的臟衣服洗一件少一件,地掃干凈了屋里也就亮堂了。”母親說,與其坐在那邊氣惱,嫌活多,不如動手去做,做一樣少一樣,把地上的臟東西打掃干凈,心里也就高興了。
母親的這些言行舉止,內化成一個家庭的家風,成了孩子們的護身符,孩子們始終在模仿著父母的樣子做人和生活,特別努力,晚輩當中涌現出許多名牌大學生。
紀太年也是深受母親影響,始終保持著勤學精進的狀態,至今為止,他出版各種專著52本,主編圖書128本,繪就工筆畫400多張,在南大、復旦以及耶魯大學等高校做過340場講座,內容主要分成三大類:藝術品欣賞、東西方文化比較和藝術品投資,有幾次講座的聽眾達到一千多人,走道上都是人。
一直到現在,紀太年始終不敢懈怠,凡事都以父母的言行為榜樣。他說:“沒有一件好事是靠走捷徑得來的,人要能吃點苦,日子過得才甜。”
舍得先給別人點燈,自己的路才好走
艱難困苦擋不住母親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而每受一點別人的幫助她卻能記一輩子。
當年父親被辦學習班,停發工資,一家人失去經濟來源。有一次家里沒米了,母親硬著頭皮出門找親戚去借,沒想到才一開口就被拒絕了。
回家的路上,母親一直強忍著淚水,但一位遠房親戚還是看到了她的異樣,親戚從自己捉襟見肘的家里勻出一袋子玉米送了過來。
幾十年過去了,對這件事母親一直念念不忘,反復跟孩子們說要記得人家的恩情,要做個好人。母親還舉例子告訴兒女們,要得自己走的路敞亮,就要舍得先把別人的燈點亮。母親說,能幫人的地方要幫人,心里存了這樣幫人的念頭,哪怕遇到再難的路也能走得通。
有一年,年三十的晚上,一大家子陪著父母親吃年夜飯。耄耋之年的母親感嘆道:“我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怎么能有這么大的福報,生養出你們這樣好的兒女啊。”老人哪里知道,這些福報都是他們做父母的給兒女掙來的,他們把做人的規矩從小就教給了孩子們,好家風是一個家庭最好的風水,兒女們自然能成大材。
母親的為人處世,內化成了紀太年的行事準則,也直接給他的藝術創作注入了靈感。
紀太年的作品追求畫面清潔、干凈,隨著他的講述,我慢慢梳理著他在審美上的情感來源。他說,幾十年過去了,他還記得父親當年經手調解的一樁青年男女的戀愛糾紛,后來父親受此事的牽連,挨了處分。但父親沒有因此放棄關心對方的家庭,主動幫助撫養對方一歲多的孩子。說到這里時,暮色漸漸涌起,但紀太年臉上起伏的情緒仍然清晰可見。
為了從這種沉默里抽離出來,我轉頭看看畫面上那些高潔、風雅、唯美、嫻靜的水禽、植物,我明白了紀太年這種“唯美才是唯一”的審美取向背后的情感來源,那就是對弱者的深切同情,對丑陋的刻骨摒棄,對自由的真切向往。他描繪在紙上的美,源于對現實生活深深的共情,紙是薄柔的,顏色是清淺的,附著其上的氣息是淡雅的,但人們從中感受到的情感卻是震撼的。
紀太年曾經說過一句話:不動情不動筆。這個情,不是小情緒、小情調,而是一種帶著對萬物、對生命的悲憫之心的大的情感,是媽媽當年所說的“舍得先把別人的燈點亮”。
說起自己所畫的水禽的神態時,紀太年說:“我畫的這些飛鳥、水禽沒有殺伐心,沒有血腥味,沒有悲傷。我不會畫一只鳥銜一條魚,不會畫一只老虎去追一個人,不會畫一個人張著網待著小鳥自投羅網,萬物在我營造的這種世界里是和平共處、協調共生的,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
紀太年一直在通過色彩和線條,痛快淋漓地表達著自己的藝術主張。同時,這也是一個孩子,獻給母愛的頌歌。
韓麗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作品多部。散文集《意思》獲第七屆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
編輯? ?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