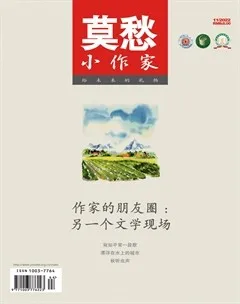跟隨大師的心痕品讀人生
我四十歲開始才真正靜下心來讀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沉淀久了,才慢慢發現小說的好,更體會到小說作家的不易,他們需要從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再從形而上回歸到形而下,通過輕描淡寫的人物刻畫和情節敘述,表現出哲學家、史學家用力想表達的東西。
一部真正高明的小說,其實有些類似于禪宗所講的頓悟。一些深刻的道理,不必說、不可說,也不能說。師傅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徒弟講出來,而是要以寄意深刻、無跡可尋的閑言碎語誘導徒弟自己體悟其中的機鋒,否則絕無頓悟的可能。這也許就是偉大的小說家比道學家高明的地方。儲福金先生的長篇小說《直溪》,講述了一個青年對個體生命精神困境的救贖之路,在時間和記憶的糾纏結構中實現了自我重構,無論是創作思路、敘事手法,還是人性刻畫、文化功底等方面,都令讀者感觸頗深。
說來也巧,和《直溪》中的主人公宋正明以及作者本人一樣,我在三十多歲時也有一年外派掛職的經歷,當時心中也出現過一些片段化的思緒和掙扎,比如:究竟是時間衡量了存在,還是存在包容了時間?過去、現在、未來……每一刻似乎都抓不住真實的自我,而自我究竟在哪里停駐,在何處實現意義和價值?一旦在找尋本我的過程中迷失,生命的趣味就會失去很多,苦惱也會增加很多。
儲福金先生輕松地把時間這條維度徹底打通,最終在一個節點實現圓滿融通的狀態。儲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到時間,也一直在思考歲月和人生之間的關系,有時覺得時間“用著心去感覺,總也是滴滴答答”;有時覺得“時間拉得長長的……以致有時都弄不清歲月的流動了,弄不清到底是真實還是虛幻的人生”;有時覺得時間是辯證的、相對的,比如“年輕時的歲月輕易失落了,偏是艱難的生活顯得特別長。意念在另一個世界里盤桓,行路在生活的世界也就顯得短了”,最終悟到“一生如一瞬。一生即一瞬。圓融一體,再不割裂”……
我以為,儲先生對時間概念的抽象思考和感性描寫,都是建構在對生命本體的解讀之上的,而生命在每一個具體時間節點上的停駐,則可以理解為海德格爾定義的“此在”,即人在某一有限時間內的個體存在,是活生生的、有喜怒哀樂的人的“客觀存在”,亦是“支撐著意識”的“現實存在”。我們若要理解存在者本身,就應當把握每一個“此在”在生命成長過程中所呈現的特征和價值。比如,宋正明年幼時寫給心儀女孩的“一段段如詩的文字”,是源于青春期的性沖動;看到季媚之后的魂不守舍,是基于純粹欲望的本能吸引;再到林向英給予他的感覺,既脫離于兩性,又回歸于人性……在這轉化的過程中,每個階段的宋正明,其實都是處于某個“此在”的存在者,相互之間既有矛盾又有瓜葛,既似曾相識又恍如隔世,這也是為什么作者會聯想到平行世界。
《直溪》的結尾也是整部作品的高潮,宋正明仿佛在瞬間感受到時間維度的變化,感受到過去、現在、未來……同時也再次如篇首所述聽到了“清晰的滴水聲,漏著的滴水。一滴一滴,滴滴答答……”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海德格爾的一句話:“我意識到我與我的時間不可分離,于是我決定與時間融為一體,盡心竭力于一無所是或者成為任何東西。”
駱威:博士,副研究員。任職于南京大學。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