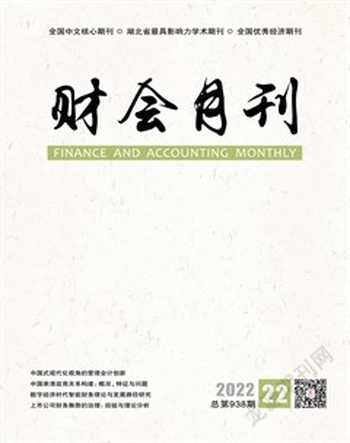數字技術何以賦能企業科技向善:耦合視角


【摘要】 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在帶來高效和便利的同時也引致新的風險和爭議。 在此背景下, 企業科技向善的呼吁應運而生, 如何向善成為重要議題。 本文按照“不善原因——突破路徑”的邏輯, 首先對科技創新與應用不善的原因展開分析, 再從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形態的影響、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的耦合統一, 以及企業可以借助數字技術賦能實現風險預測等方面, 思考如何促進企業科技向善和規避不善的問題。 研究表明, 企業科技向善不僅需要科技倫理治理, 而且需要作為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企業善利同構, 同時基于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發展將有助于降低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 從而有助于科技創新多元主體共同合作共治, 降低科技治理成本和提升社會生產經濟效率, 進而為科技推動經濟社會良性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關鍵詞】數字技術;企業科技向善;融合創新;數智賦能
【中圖分類號】F270-0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2)22-0148-6
一、引言
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基因工程等為代表的新興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 其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倫理和風險問題, 如信息繭房、數字鴻溝、算法歧視、人工智能侵犯個人隱私等[1] 。 在這樣的背景下, 科技是否向善越來越受關注, 科技向善的呼吁應運而生。 科技是否向善的本質在于科技的創新與應用是否向善, 而科技創新與應用的實踐主體主要是經濟社會的微觀主體——企業或新型組織形態商業生態系統。 因此, 如何促進企業或商業生態系統①科技向善就變成關系科技向善能否實現的關鍵問題。
如同新興科學技術的負外部性和風險已引起人們對新興科技倫理治理的關注[2] , 企業科技創新方面也涌現出基于已有管理理論的創新責任的討論和理論議題[3] 。 但正在以新一代ICT技術為基礎的數字技術引領的新一輪產業變革, 打破了已有工業革命下的管理情景, 譬如資源配置方式和市場交易關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4] , 過去的管理實踐經驗已不再適用。 如此, 在日益依賴科技推動的社會發展中, 作為經濟社會微觀主體的企業, 應如何應時而變, 基于科技創新使其發展和產品或服務合乎人類價值訴求、增加社會福祉[5] , 成為當前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和管理挑戰。 與此同時, 催生的科技向善理念及其研究的興起, 為微觀企業和科技創新的發展指出了新方向。
但是, 關于科技向善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 如何實現企業科技向善更是有待探索。 因此, 在新情景下, 思考如何促進企業科技創新與應用向善, 成為自然科學界、社會科學界和實務界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 本文將按照“不善原因——突破路徑”的邏輯, 從呈現科技不善結果的原因出發, 并基于新興技術中的數字技術引領的產業變革所帶來的影響, 即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形態與其根本驅動力的影響, 思考企業如何借助數字技術賦能——基于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發展應用, 探尋和回答新情景下何以促進企業科技向善這一問題。
二、相關概念與文獻回顧
數字技術和企業科技向善作為新的研究熱點, 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概念。 與數字技術相近的概念很多, 如大數據技術、互聯網技術、ICT技術等。 雖然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數字技術的內涵(如Nambisan[6] 的組合和元素視角、Yoo[7] 的特征視角、彭剛等[8] 的新技術群視角), 但都認同數字技術應用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 數字技術因其通用目的特征能夠實現無限復制共享和互聯互通, 從而具有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等優勢。 本文采用廣義的數字技術概念, 即數字技術是在由計算技術和現代通信技術等組成的新技術群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演變形成的具有通用目的的技術組合[9] 。
關于企業科技向善的概念界定, 不同學者分別從理念[10] 、戰略[11] 、行為[12] 等視角進行了探討。 本文選擇理念這一視角, 認為企業科技向善是指“企業在科技創新與應用時應規避因技術本身發展帶來的問題和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存在的問題, 旨在通過良性可持續的社會價值創造, 實現以人為中心的美好生活構建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10] 。 由此可見, 企業科技向善不僅有助于經濟社會良性可持續發展, 而且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 為了探究如何實現企業科技向善, 本文接下來將以企業科技創新與應用不善的原因為研究的切入點。
三、企業科技創新與應用不善的原因
從科技創新與應用不善呈現的結果——數字鴻溝、信息繭房、算法歧視、人工智能侵犯個人隱私等問題來看, 其產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新興科技應用的邊界不清及不規范引致不善的結果; 二是部分踐行科技創新與應用的微觀主體——企業仍然把追逐利潤視為生產目的和根本驅動力, 這就意味著在科技被應用到科技創新產品或服務時, 即使企業明知有一定的不善風險或危害, 也依然在設計或部署時無視其預期風險, 引致不善; 三是在有限的認知下, 無法預判科技創新本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 導致出現不善的風險。
1. 新興科技應用的邊界不清及不規范。 科技創新歷來備受爭議, 這不僅緣于新興科技應用與現有傳統產業之間形成的利益沖突, 還因為人們對新興科技應用益處的認知往往超過對風險的認知[13] , 以致擴大了科技益處的應用范圍, 導致出現不善影響。 如此應用無邊界或邊界不清, 是致使部分不善的直接原因。 優化問題的解, 對邊界攝動極為敏感。 因此, 優化新興科技應用尋求向善的解, 就在于對新興科技應用邊界的認知。 若能恰當和深度地了解新興科技應用的影響和人們對科技的反應, 劃分明確的使用與行為規范邊界, 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范行為。 如對無序性沉迷手機的時間或程序識別限制、助力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的適配服務提供等, 都可以降低新興科技應用的不善影響。
同時, 若缺乏對使用邊界的考量, 即在進行科技創新與應用轉化為科技創新產品和服務的設計與部署時, 未能考慮到微妙的過程和技術與社會的交互機制, 是形成科技創新與應用潛在危險的重要原因。 因此, 在新興技術與社會不斷交互影響和塑形的過程中, 也正在逐漸形成以科技倫理治理為主要規范來約束科技不善的治理, 如對于新興技術促生的新型產品或服務, 已有“數字使用與行為”法規、《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組建方案》等新的法規制度出現, 在不斷健全完善以防控或規避科技不善。 由此可見, 新興科技的不善治理, 不只限于生命倫理學的訴求, 還在于善治的訴求, 即科技倫理治理[14] , 尤其是善治的程序性問題(如邊界等問題)研究。
2. 企業將逐利視為其根本目的。 關于經濟社會的微觀主體——企業把追逐利潤視為其生產目的和根本驅動力, 可追溯到整個工業經濟時代。 從宏觀層面來看, 企業通過在市場中競爭, 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 以推動社會進步; 從微觀層面來看, 企業為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并得以存續和發展, 會以盈利為目標, 因此, 在市場經濟中逐利便成為企業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這種企業邏輯在沒有外部性的嚴格假設下是成立的[15] 。 但外部性促生了企業社會責任及相關理論, 為此有大量管理學文獻探討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 但這些動因剖析綜合起來幾乎都隱含地指向新古典經濟理論企業發展邏輯——利潤動機驅動發展, 對其影響機理的解讀也是沿著利潤驅動的邏輯予以解構, 解釋企業行為。 由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 企業逐利驅動發展邏輯是企業管理理論構建的基石, 但也為形成科技創新與應用的不善埋下了隱患, 有待解決。
3. 科技創新本身的不確定性。 關于科技創新不確定性引致的不善, 創新管理領域的主流學者都非常默契地把關注重點放在基于科技創新的應用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以及可能使企業面臨的生存風險上[16] 。 但是, 科技應用于社會而言涉及的風險到底有哪些, 如何規避?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理解和研究, 對某一具體技術或組織的純技術風險分析更是提出了挑戰。 這也說明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 越來越需要開展跨學科或多學科的綜合研究, 以便更好地理解科技創新與應用的潛在風險并規避不善。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 從微觀主體企業應對解決不善的視角又可以將科技創新與應用不善的原因歸為兩個: 有意視而不見和有待打破認知局限進而化解不善。 這樣, 能否解決或規避科技不善就轉化為: 能動的科技倫理治理與是否可以破解企業以利潤為根本目的, 以及如何基于認知能力提升來降低科技創新與應用的不善風險。 科技倫理治理已越來越受重視, 成為學者們較為關注的研究問題。 因此, 本文將主要針對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的影響和企業借助數字技術賦能優化向善選擇的交互影響進行分析, 尋求破解有意視而不見和認知局限所致不善的方法, 以促進企業科技向善的實現。
四、基于數字技術的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的耦合分析
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不僅使得經濟社會的資源和要素數字化、智能化, 形成了以數字化、數字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數字經濟形態, 而且推動了微觀企業的組織變革, 如不斷涌現出以雙邊與多邊平臺、在線社區、生態系統等為代表的新型組織形態[17] 。 企業新型組織形態變化是否重塑了企業利潤驅動的發展邏輯, 從而使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具有內在一致的相容性? 從組織理論角度來看, 商業模式反映企業創造和獲取價值的邏輯[18,19] 。 同時, 即使從工業經濟時代進入互聯網時代, 也仍沒有改變企業價值判斷和價值創造的本質[20] 。 據此, 有關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形態的影響, 本文從價值創造、價值傳遞和價值獲取維度識別出三個主要的企業新組織特征——價值共創化、及時透明化、互聯共享化, 并以此為基礎對新特征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 剖析數字技術情境下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的耦合一致性, 以破解不善和探尋向善路徑。
1. 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形態的影響。
(1)價值共創化特征及其影響。 根據邁克爾·波特在《競爭優勢》中的分析, 傳統企業價值創造是以企業為主體, 由價值鏈的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生成最終的產品和服務, 進而完成價值創造。 然而, 企業新型組織的價值創造呈現出價值共創化, 在價值創造過程中, 價值的使用者也可以是價值的創造者[21] , 即供需雙方不同的資源提供者和消費者同為價值創造主體, 借助互聯網等新興技術連接各方資源, 打破傳統企業對組織內部或地理臨近的資源依賴, 通過數字平臺或群體智能的互聯網連接互動和資源整合, 共同完成價值創造的過程。 價值共創參與者由最初的用戶和企業發展為包括價值鏈上的任一主體, 價值共創體系也越來越開放。
價值共創的形成來自消費者消費需求多樣性和個性化的驅動, 以及企業為了獲得異質性資源和精準滿足用戶需求以獲得競爭優勢的驅動。 他們在互聯網信息技術和數智技術的推動下, 基于網絡連接被納入同一價值創造系統, 開展協同創新、完成價值創造。 由此, 價值共創化更易整合各方資源和精準滿足消費者需求, 從而更高效地完成價值實現。 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嵌入并融合價值共創帶來的影響就是: 第一, 拓展了產品邊界, 將傳統成品轉向具有適應性調整特征的成長品, 如開源產品, 以更大程度地滿足個性化的需求, 但成長品的發展方向難以預測, 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價值衡量難度; 第二, 加強和改變了企業與消費者、傳統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關系, 使其由原來單純的供求買賣交易關系, 因協同創新而變為融合共生關系。
(2)及時透明化特征及其影響。 在產業價值鏈中, 傳統企業通過供應商、生產商、零售商和終端用戶的梯次傳遞完成價值傳遞過程。 而數字、數智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大大縮短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 使得產品和服務信息及消費需求能被快速傳遞和響應。
一方面, 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應用有利于信息的可追溯和透明化披露。 同時, 云計算和AI的使用, 有助于以極低的邊際成本和24小時工作模式提供連續、及時、高效的信息反饋。 此外, 基于信息技術和制度契約構成的混合治理機制, 比單一方式更能有效地確保信息的真實透明, 從而大大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 另一方面, 在開放式價值共創的基礎上,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而形成的B2B、B2C、C2C和C2B云端生態系統和新媒體, 使得價值傳遞由鏈式結構向網狀結構演化, 平臺供需雙方的價值傳遞也不再是被動接受和彼此割裂, 平臺用戶可以獲得可靠和相對透明的產品和服務。 所以, 企業新型組織形態在價值傳遞環節更及時、透明。 同時, 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距離的縮短, 也有助于生產者發現以往容易忽視的消費需求和社會問題, 進而增強市場預期, 形成新的更全面的價值主張, 拓展產品和服務的開發和應用。
(3)互聯共享化特征及其影響。 與價值共創化和價值傳遞的及時透明直接相關的是價值獲取的互聯共享化。 原來企業通過為目標顧客創造價值來獲取自身價值, 并主要在企業股東、債權人、員工等內部利益相關者間進行價值分配。 但是, 基于數字和數智化的價值創造及分配與以往相比有一定差異。
首先, 在企業新型組織的網絡化結構下, 價值獲取機制變為網絡效應和社會互動, 企業為實現價值獲取, 關注點會從內部利益相關者利益轉向所有參與者共同獲取價值[22] 。 而且, 其不再只追逐銷售紅利, 而是不斷與消費者進行價值協同和價值互動, 從中創造持續的價值以獲得收益, 如創生性產品。
其次, 數字技術作為一種通用技術, 不僅具有低成本、高準確性和高響應速度的優勢, 而且讓供需匹配日益精準化、定制化和一體化[23] 。 同時, 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并存在于生產、消費、生活等各個領域的數據要素資產化后形成的多方之間的大數據合作資產, 其本身就具有收益的多邊性特征[24] 。 這種大數據合作資產不僅反映了價值創造中的互動與協作, 而且反映了價值獲取的互聯共享化。
最后, 從反身性的角度來看, AI不但能加強公眾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 而且使傳統資本增值模式不再一味追求“速度”, 而是開始尋求“度”的把握, 還使AI等社會人工物承載人類的價值, 進而促進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25] 。 總而言之, 新技術的發展使得公眾成為創新創業和資本增值的內部成員, 多方主體之間相互影響, 形成某種共同體, 共享資本紅利和發展成果, 并促進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
2. 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耦合統一。 在數字技術背景下, 若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耦合統一, 實現善利同構, 則可破解“因利罔顧善義”的困局。 耦合(Coupling)最初是物理學概念, 后來被應用到生態系統和心理學等研究領域。 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耦合是指兩者具有高度關聯, 通過關聯要素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 形成一個新的系統。 如果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是耦合的, 那么, 在目前建構的經濟理論體系內, 基于“動因——行為”的邏輯, 科技向善就不再是企業的被動選擇或道德倫理的應然要求, 而是企業的主動選擇。
企業向利與科技向善現實相悖的深層原因是: 管理學的發展是由“追求使管理更有效率的科學主義范式和追求使管理更加人性的人文主義范式”兩種理論范式主導的, 這兩種理論范式也被很多管理學者認為是對立與相互排斥的, 而產生這種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對管理學或企業追求的目標和本質屬性的認知差異, 但管理學的方法或范式應是語境化或情景化的[26] , 當情景發生變化時, 管理學的范式和企業主體邏輯也隨之改變。 因此, 新的組織形態特征會促生新的企業發展邏輯。
本文基于企業新型組織形態的特征和影響的分析, 并按照Priem等[27] 提出的新興企業邏輯, 基于“市場——商業模式——價值創造——價值獲取”, 得出企業價值共創化、及時透明化和互聯共享化特征帶來的改變, 形成新的企業發展邏輯, 見圖1②。
圖1顯示: 供需雙方由原來簡單的買賣交易關系變為融合共生關系; 數字技術促生的組織關系網絡化和組織情景生態化, 也使得企業能夠發現以往容易被忽視的消費需求和社會問題, 形成更全面的價值主張; 只有在不斷的價值協同和價值互動中創造持續的價值, 才能滿足共同的目標需求, 從而獲得收益, 實現價值獲取, 多方主體之間相互影響, 形成某種共同體, 共享紅利與發展成果。 這種改變使得企業很難像以往一樣, 以盈利為根本目的。 在不同主體彼此聯系和影響更加緊密的共生情景下, 因共生互聯共享才能得以實現的價值獲取, 使得企業以科技為工具或手段的目的性就變成了共同體的合意——共同的美好生活。 此時, 企業的目標和本質屬性不再局限于基于效率和利潤追求的價值創造, 而是為了共同的美好生活而進行價值創造; 利潤不再是追求的目標, 而是如同科技一樣的工具, 服務于企業的存在。 利潤、科技和企業的目標與本質屬性得到形式和內容上的邏輯統一, 也實現了互惠互利、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 同時, 共生互聯共享契合系統論和共同富裕的主張, 也說明管理學以個體為主展開的分析方法, 應變為以系統為出發點而展開分析。
經典理論企業邏輯與新的企業發展邏輯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 在后一邏輯中, 供需雙方都有了雙重身份, 在任一環節互為供給者和需求者, 日益凸顯互聯互惠共生性。 也正是這種共生性倒逼企業重新審視企業和科技的目的與本質屬性, 致使科技向善成為企業自我存續的內在需要。
五、基于數字技術融合創新發展的向善路徑
由于已有認知條件的限制, 無法預判科技創新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潛在的不善風險, 這是任何新興科技出現后都備受爭議的重要原因, 也是一直以來面臨的難題。 但當前數字技術的發展, 以及其帶來的數字化、數智化驅動, 為基于認識論化解不確定性和潛在不善風險提供了有解的可能。
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全新的“突破性”技術, 顛覆了現有技術體系和原有技術范式, 使得產品、服務或工藝的成本降低、性能提升[28] 。 并且,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 其在與經濟社會活動不斷的融合深化中形成新方法躍遷, 進而形成進階的決策層面的前瞻預判[29] , 使得在原有企業管理決策情境中受限的“關聯+因果”訴求得以實現, 提高了對將發生什么的認知能力。 因此, 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發展也在不斷地改變著人們與組織的決策要素和決策行為。 科技、方法、理論的創新, 不但賦能價值創造, 而且實現了對價值創造影響的預判, 進而為選擇合意或向善的價值創造提供了實現基礎, 如基于預測優化模型降低不確定性[10] 。 已有文獻與實踐也佐證了數字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融合創新正成為降低和消除由科技創新自身不確定性而帶來的不善風險的重要方法和路徑, 例如: 無論是基于深度學習的工業缺陷檢測[30] 、硅谷的精益創業, 還是社會仿真模擬、跨時空實現虛實共生的數字孿生技術應用, 在數字化、數智化結果的反饋下, 都正在把基于有限認知的風險和不善控制在盡可能低的限度內, 以最大程度地逼近最優解、向善解。
那么在降低不確定性的基礎上, 價值創造是否向善的考量就成為最后的關鍵。 價值創造向善考量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 一是基于科技創新創造社會價值, 二是確保科技創新的向善導向性。 這兩個關鍵內容的本質都指向人的追求。 因此, 可以基于人的需要這一根本目標, 挖掘社會價值的結構維度和價值導向性的結構維度, 并根據識別出的維度進行組合分析, 據此提出適用于不同企業的科技創新與應用向善路徑。 按照社會價值的載體——商品或服務的重要性, 以及經濟學的商品重要性, 可以把社會價值維度劃分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價值導向性是企業科技創新的趨善避惡選擇, 而這種選擇是基于企業可能提供的成長品或服務未來的使用效果所做出的價值判斷。 因此, 本文借鑒同樣基于未來判斷的風險感知概念[31] , 把價值導向性劃分為向善性、不確定和向惡性。 綜合價值創造的重要性和價值導向性兩個維度的劃分, 可以識別出六種科技創新導向組合: 穩健型創新、擇優型創新、探索型創新、漸進型創新、謹慎型創新和規避型創新, 見表1。
其中: (1)穩健型創新, 即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必需品, 同時價值導向性為向善性時, 企業可以直接進入價值創造環節。 (2)擇優型創新, 即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非必需品, 同時價值導向性為向善性時, 意味著其產品或服務不重要或者有很多替代品, 這時應根據擇優原則進行創新生產。 (3)探索型創新, 即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必需品, 但價值導向性為不確定時, 應集中整體優勢(如舉國體制), 有步驟、階段性地進行探索或模擬試驗, 直至逼近向善性。 (4)漸進型創新, 即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非必需品, 而且價值導向性為不確定時, 企業可能追求的是新、奇、特需求或者進一步改進現有社會供給, 依據需求的重要性來看, 這類創新允許的時間比較充裕, 因此可以漸近地進行創新。 (5)謹慎型創新, 即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必需品, 但價值導向性為向惡性時, 雖“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應隨時改進并盡可能尋找多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謹慎進行創新生產。 謹慎型創新與探索型創新組合比較接近, 或者說相比于探索型創新多了去掉一種選擇項的優勢。 因此, 這兩種組合可合為一種創新路徑。 (6)規避型創新, 即當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非必需品, 而且價值導向性為向惡性時, 應直接摒棄這類產品或服務的生產, 避免其進入價值創造環節, 同時其也是以后進行生產或創新的負面規避參照, 可與漸進型創新合為一種創新路徑。 綜上, 本文對應提出企業科技向善的路徑為: 穩健型創新路徑、擇優型創新路徑、探索型創新路徑、漸進型創新路徑。
六、結語
新興科技的出現與發展引發了新一輪的科技爭議和科技倫理治理革命, 其中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也正在改變企業的組織形態與價值創造方式, 使其呈現出價值共創化、及時透明化與互聯共享化等特征, 這將促使科技創新多元主體作為利益共同體共同參與創新和風險治理。 同時, 基于數字技術應用形成的數智經濟也變革了企業的原有運行邏輯, 使得善利同構。 企業只有堅守長期主義、重視長遠合意的社會價值, 才能獲得持續競爭優勢。 這將有助于科技治理成本的降低和社會生產經濟效率的提升, 進而為新興科技推動經濟社會良性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 注 釋 】
① 關于商業生態系統是否將取代企業成為新型組織形態的微觀主體,目前新的系統的管理理論尚未形成,因此本文仍以企業及其對應的已有管理理論為研究基礎。
② 為了與基于新興技術形成的新興企業組織形態的發展邏輯相區別,稱原有的企業發展邏輯為經典理論企業邏輯。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謝洪明,陳亮,楊英楠.如何認識人工智能的倫理沖突?——研究回顧與展望[ 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9(10):109 ~ 124.
[2] 樊春良,李東陽.新興科學技術發展的國家治理機制——對美國國家納米技術倡議(NNI)20年發展的分析[ J].中國軟科學,2020(8):55 ~ 68.
[3] 梅亮,臧樹偉,張娜娜.新興技術治理:責任式創新視角的系統性評述[ J].科學學研究,2021(12):2113 ~ 2120+2128.
[4] 謝康,吳瑤,肖靜華.生產方式數字化轉型與適應性創新——數字經濟的創新邏輯(五)[ 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1 ~ 10.
[5] Hogenschurz Lukas.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s a Public and Social Good[ J].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21(1):10 ~ 16.
[6] Nambisan Satish.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17(6):1029 ~ 1055.
[7] Yoo Youngjin. Computing in Everyday Life: A Call for Research on Experiential Computing[ J].MIS Quarterly,2010(2):213 ~ 231.
[8] 彭剛,朱莉,陳榕.SNA視角下我國數字經濟生產核算問題研究[ J].統計研究,2021(7):19 ~ 31.
[9] 田秀娟,李睿.數字技術賦能實體經濟轉型發展——基于熊彼特內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 J].管理世界,2022(5):56 ~ 74.
[10] 李巧華,雷家骕,孟猛猛.企業科技向善:概念、邏輯起點與實踐路徑[J/OL].科學學研究:1-16[2022-05-25].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220307.002.
[11] 孟猛猛,雷家骕.基于集體主義的企業科技向善:邏輯框架與競爭優勢[ 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1(7):76 ~ 84.
[12] 楊淼,雷家骕.科技向善:基于競爭戰略導向的企業創新行為研究[ J].科研管理,2021(8):1 ~ 8.
[13] Calestous J.. Innovation and Its Enemies: Why People Resist New Technologie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 樊春良.科技倫理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J].科學與社會,2021(4):33 ~ 50.
[15] 金碚.工業的使命和價值——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理論邏輯[ J].中國工業經濟,2014(9):51 ~ 64.
[16] Ana M. Fernandes, Caroline Paunov. The Risks of Innovation: Are Innovating Firms Less Likely to Die?[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5(3):638 ~ 653.
[17] 魏江,劉嘉玲,劉洋.新組織情境下創新戰略理論新趨勢和新問題[ J].管理世界,2021(7):182 ~ 197+13.
[18] Nicolai J. Foss, Tina Saebi. Business Models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etween Wicked and Paradigmatic Problems[ J].Long Range Planning,2018(1):9 ~ 21.
[19] Spieth Patrick, Schneider Sabrina, Clau? Thomas, Eichenberg Daniel. Value Drivers of Social Businesses: A Business Model Perspective[ J].Long Range Planning,2018(3):427 ~ 444.
[20] 羅珉,李亮宇.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價值創造視角[ J].中國工業經濟,2015(1):95 ~ 107.
[21] 李巧華.新時代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與實現路徑[ J].財經科學,2019(6):57 ~ 69.
[22] 朱明洋,李晨曦,曾國軍.商業模式價值邏輯的要素、框架及演化研究:回顧與展望[ 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1(1):149 ~ 160.
[23] 寇宗來,趙文天.分工視角下的數字化轉型[ 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50 ~ 59.
[24] 齊佳音,張國鋒,王偉.開源數字經濟的創新邏輯:大數據合作資產視角[ 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37 ~ 49.
[25] 潘恩榮,孫志艷,郭喨.智慧集成與反身性資本重組——人工智能時代新工業革命的發展動力分析[ 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0(2):42 ~ 47.
[26] 羅珉.管理學:科學主義還是人本主義[ 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16 ~ 20.
[27] Priem R. L., Butler J. E., Li S.. Toward Reimagining Strategy Research: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ion on the 2011 AMR Decade Award Article[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3(4):471 ~ 489.
[28] 孔德婧,董放,陳子婧,劉宇涵,周源.離群專利視角下的新興技術預測——基于BERT模型和深度神經網絡[ J].圖書情報工作,2021(17):131 ~ 141.
[29] 陳國青,任明,衛強,郭迅華,易成.數智賦能:信息系統研究的新躍遷[ J].管理世界,2022(1):180 ~ 196.
[30] 羅東亮,蔡雨萱,楊子豪,章哲彥,周瑜,白翔.工業缺陷檢測深度學習方法綜述[ J].中國科學:信息科學,2022(6):1002 ~ 1039.
[31] Otway Harry, Thomas Kerry. Reflection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Policy[ J].Risk Analysis,1982(2):69 ~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