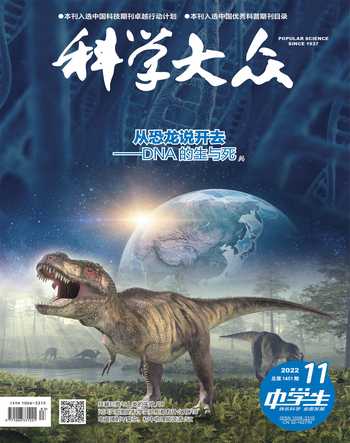從恐龍說開去
趙言昌



要說到2022 年票房火爆的那些電影,《侏羅紀世界3》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自從6 月10 日在國內(nèi)影院上映以來,《侏羅紀世界3》便表現(xiàn)亮眼,成為暑期檔不可小覷的一股力量,票房最終突破10 億元。
作為“侏羅紀”系列的完結(jié)篇,《侏羅紀世界3》的陣容比以往更加強大。除了“老朋友”雷龍、滄龍、霸王龍,還出現(xiàn)了身披羽毛的火盜龍、頑皮可愛的迅猛龍寶寶。恐龍一直是個讓人激動的話題,無怪乎,又有人開始問:“能不能復活恐龍呢?”
DNA 的死亡
復活恐龍的想法很誘人,只是很難找到恐龍的DNA。
說起生物學家,你可能很自然地想到一群穿著白大褂、搖晃玻璃管的人,其實生物學家也經(jīng)常“動粗”。2012 年,丹麥科學家摩頓·艾倫多夫領(lǐng)導的研究小組就動起了電鉆——在對158 根恐鳥骨骼進行取樣和分析之后,他們發(fā)現(xiàn),DNA 的半衰期是521 年。
生物課本上說,DNA 看上去像是旋轉(zhuǎn)的樓梯。其實,DNA 和樓梯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它們都由更為基本的材料構(gòu)成。樓梯由鋼鐵、玻璃、石頭等修建,而DNA 的基本組成單位叫作脫氧核苷酸。依據(jù)攜帶堿基的不同,又可以將脫氧核苷酸分為4 類:帶腺嘌呤(A)的、帶鳥嘌呤(G)的、帶胸腺嘧啶(T)的、帶胞嘧啶(C)的。鋼鐵、玻璃、石頭的組合方式,決定著樓梯的形態(tài);與此類似,DNA 攜帶的信息實質(zhì)上就取決于4 類脫氧核苷酸的排布順序。
核苷酸與核苷酸之間,也需要水泥一樣的黏合劑。具體一點說,要用到兩種力量:一種是分子內(nèi)作用力,比如共價鍵,將核苷酸連接成長鏈;另一種是分子間作用力,比如氫鍵、范德華力,將兩條長鏈連接在一起,形成雙螺旋結(jié)構(gòu)。
問題在于,這些力量不是永遠存在的,而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水分多寡、紫外線強弱、蛋白質(zhì)是否“聽話”、周圍有沒有細菌等。健康的生物,內(nèi)在環(huán)境較為穩(wěn)定、有序。等生命到了盡頭,維持秩序的力量消失,核苷酸與核苷酸之間的連接便漸漸崩壞,DNA 攜帶的遺傳信息也隨之漸漸消失。
每過521 年,核苷酸之間的連接就消失一半。由此推算,最理想的情況下,骨骼中的DNA 大約可以保存150 萬年。恐龍滅絕大致發(fā)生在6 600 萬年前,這意味著,我們幾乎不可能在恐龍化石中找到DNA。
DNA 的工作
那么,能不能在沒有DNA 的情況下復活恐龍呢?
你也許會脫口而出:“不可能,因為DNA 是生物的遺傳物質(zhì)。”沒錯,除了RNA 病毒、朊粒等特殊例子,絕大多數(shù)生物的遺傳性狀由DNA 決定。那么,到底是怎么決定的?
常言道:“眾口難調(diào)。”拿香菜來說,有人非常喜歡,也有人避之唯恐不及。2012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差異可能來自嗅覺受體。嗅覺受體是一類特殊的蛋白質(zhì),它們可以與空氣中的氣味分子結(jié)合,進而激活神經(jīng)元,讓我們產(chǎn)生特定的感覺。
是“誰”將這些蛋白質(zhì)制造出來的?主要功臣是轉(zhuǎn)運RNA(tRNA)。tRNA 長得像三葉草,功能則好比叉車,可以將氨基酸運到指定的位置,以便組合成蛋白質(zhì)。
又是“誰”告訴tRNA 將氨基酸放到哪里?奧妙在tRNA 的另一頭,上面分布著3 個堿基。前面說到,兩條DNA 長鏈之間存在氫鍵。其實,氫鍵的結(jié)合發(fā)生在堿基之間。而堿基的結(jié)合,十分專一。比如說,組成DNA 的4 種堿基中,腺嘌呤(A)與胸腺嘧啶(T)拉手,鳥嘌呤(G)偏愛胞嘧啶(C)。
當tRNA 帶著氨基酸游走的時候,很快會遇到一個合格的“指揮者”——信使RNA(mRNA)。mRNA 看起來像是DNA 單鏈,只是核苷酸數(shù)目較少。或者我們可以說,mRNA 如同一把縱向切開的梯子。梯子中間的橫檔,便是核苷酸向外伸出的堿基。依靠堿基之間的結(jié)合規(guī)律,mRNA 可以指揮tRNA,將氨基酸放到合適的位置。
mRNA 也有4 種堿基:腺嘌呤(A)、鳥嘌呤(G)、胞嘧啶(C)、尿嘧啶(U)。尿嘧啶雖然與胸腺嘧啶有些區(qū)別,在結(jié)合偏好上卻完全一致。因此,DNA 只要將自身的核苷酸排布順序告訴mRNA,便能通過上述機制指揮蛋白質(zhì)的合成,進而利用蛋白質(zhì)調(diào)控各種各樣的生理活動,比如影響我們對食物的感覺。
目前認為,11 號染色體上的基因與嗅覺關(guān)系密切。除此之外,它還影響著神經(jīng)的發(fā)育、胰島素的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活動決定了我們的喜怒哀樂,而胰島素是能量代謝的重要推手,影響著身體利用營養(yǎng)物質(zhì)的能力。
當然,遺傳性狀固然重要,卻不是生活的全部。舉例來說,帶有某些基因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腦血管疾病,不過,控制飲食、注意運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基因的影響。至于智力、志趣、性情,就更復雜了,后天的影響才是決定性因素。
DNA 的成長
于是,下一個問題又來了:為什么大多數(shù)生物不約而同地選擇了DNA 呢?遺傳信息大致按照從DNA 到RNA 再到蛋白質(zhì)的順序釋放。為什么要繞這么一個圈子,而不是以蛋白質(zhì)或RNA 為遺傳物質(zhì)呢?
直接用蛋白質(zhì),恐怕有一點麻煩。拿人類來說,一個細胞內(nèi)部就可能有數(shù)萬種蛋白質(zhì),至于我們體內(nèi)一共有多少種蛋白質(zhì),至今仍然不太清楚。相比之下,組成人體蛋白質(zhì)的氨基酸只有20 種。利用DNA 記錄氨基酸的組合方式,看起來繞了遠路,實際上更為高效。
直接用RNA,則會遇到變異問題。前段時間的新聞里經(jīng)常提到新冠病毒BA.5 毒株,“BA.5”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理解為族譜的編號。為了準確命名新冠病毒,科學家們按照基因上的親疏,給它們繪制了“家族樹”。BA.5 由B.1.1.529 突變而來,后者的父系是B.1.1,B.1.1 又是B.1毒株突變的結(jié)果……遺傳信息在傳遞的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一些變化,這就是為什么新冠病毒出現(xiàn)不到3 年,變種已經(jīng)如此之多。
DNA 卻穩(wěn)定得多,雙鏈相當于雙重保險。而且DNA 更長,編碼的蛋白質(zhì)更多。其中一些蛋白質(zhì)可以檢查DNA 中的核苷酸排列,假如出現(xiàn)錯誤,又有另一些蛋白質(zhì)負責修復。因此,平均來說,DNA 每輪復制中,核苷酸出錯的概率只有十億分之一。
DNA 的誕生
知曉DNA 的優(yōu)秀之后,很容易想到一個問題:最初的DNA,從何而來呢?
首先,早年間的地球上,哪里來的核苷酸?有些學者認為來自隕石。比如20 世紀60 年代,科學家們就在隕石中檢測到了腺嘌呤等堿基。也有學者認為,它們自然而然地就出現(xiàn)了。
1953 年,美國學者斯坦利·米勒搞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實驗裝置。裝置是封閉的,以免受到外界污染,里面只有一些小分子物質(zhì),如水、氫氣、甲烷等。按照當時的看法,原始海洋的成分也是如此。此外,該裝置還有加熱、放電的部件,用以模擬早期地球上的高溫和閃電。一周之后,他在里面檢測到了許多大分子物質(zhì),比如氨基酸。
不管來自天外還是自然生成,總之,在某個時刻,地球上出現(xiàn)了包括核苷酸在內(nèi)的大分子物質(zhì)。這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什么力量讓核苷酸組成了長鏈? 2000 年前后,學者們發(fā)現(xiàn),黏土可以促使核苷酸連接,比如蒙脫石。
蒙脫石你可能沒見過,蒙脫石散多半吃過。拉肚子的時候,醫(yī)生會開這種藥。蒙脫石散看起來像面粉,吃起來有點甜。如果將其放到顯微鏡下,可以看到許多小孔。這些小孔內(nèi)部藏著金屬離子,對人體來說,它們可以吸附細菌、病毒等有害的物質(zhì);若是遇到核苷酸,又會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早年間的核苷酸,可能就是在類似機制下變成了或長或短的鏈條。
接下來,就是進化的問題。如果將原始海洋比作一鍋湯,早期的核苷酸、氨基酸就像其中的米粒。核苷酸以隨機的方式結(jié)合,可能出現(xiàn)毫無意義的核苷酸鏈,也可能恰好像tRNA 那樣掛住氨基酸,甚至可能出現(xiàn)與mRNA 類似的復雜形態(tài)。不管哪一種,如果附近有游離的核苷酸,它們就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復制自身;如果沒有,大不了在時間作用下逐漸消失——為什么要往DNA的方向演化呢?
在早期地球中,必然有一雙負責篩選核苷酸鏈的“手”。帶著這樣的想法,有些學者將目光放到了海底——大約40 億年前,幽深的海底深處,大地露出了自己的胸膛。在巖漿的驅(qū)使下,冷與熱、酸與堿彼此交織,形成了充滿孔洞的石頭。
最早的大分子物質(zhì),就出現(xiàn)在這些石頭里。依靠分子間或分子內(nèi)的作用力,它們開始了盲目的結(jié)合,演變出各種各樣的形態(tài)。慢慢地,其中的某些核苷酸鏈像mRNA 一樣具備了合成蛋白質(zhì)的能力。蛋白質(zhì)一方面可以修復錯誤,讓核苷酸變得更穩(wěn)定;另一方面參與物質(zhì)代謝,為核苷酸復制提供更多原料。于是,當它們的子代沿著小孔進入其他孔洞時,輕易“擊敗”了那些只知道利用既有物質(zhì)復制自己的核苷酸鏈。
小行星時不時落到地球上,引起遮天蔽日的塵埃。地球慢慢出現(xiàn)了磁場,它在南北極與太陽風交匯,激發(fā)出炫目的極光。核苷酸鏈對此一無所知,只知道盡量忠實地復制自己。
第一次復制,沒有什么特別的事發(fā)生;第二次復制,仍然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如此堅持了5 億年,在35 億年前的某一天,終于出現(xiàn)了第一個單細胞生物。
結(jié)語
《侏羅紀公園》里有一句名言:“生命總會找到出路。”DNA 不懂得判斷,只知道不知疲倦地自我復制。正是這種堪稱悲壯的嘗試,催生了世間萬物。
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提出過一個“習得性無助理論”:將動物放到不可擺脫的困境中,它們會慢慢學會沮喪,哪怕情況發(fā)生變化,也沒有再次嘗試的勇氣。類似的現(xiàn)象,同樣出現(xiàn)在人類身上。人們會因為多次失敗,對運動、學業(yè)乃至家庭生活絕望,打心眼里認為不可能,拒絕再試一次。這或許是身為高等動物的代價,我們會根據(jù)既往的經(jīng)歷,決定自己的行為。
也許,這就是了解DNA 的意義:只有暫時跳出自我的界限,才有可能理解生命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