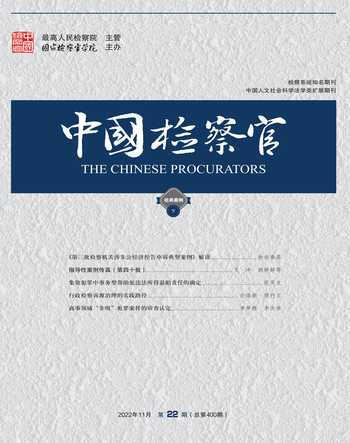集資犯罪中事務型幫助犯違法所得退賠責任的確定
摘 要:在集資犯罪中,對事務型幫助犯責令退賠采用連帶責任的做法,是一種司法粗疏的表現。錯誤地將“共同犯罪、責任連帶”這一判斷視為刑法理論通說,既不符合刑罰目的和刑法基本原則,也不利于維護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應予以糾正。責令退賠數額應與犯罪行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適應,具體可考慮以實際傭金為基數乘以適當倍數的方式加以確定,至于具體倍數,則由法官根據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裁量確定。
關鍵詞:集資犯罪 事務型幫助犯 違法所得 責令退賠 責任界限
追贓挽損是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的重要目標,而違法所得追繳與退賠又直接關系追贓挽損的成效,但現行刑法對違法所得追繳與退賠具體規則并未明確,實踐中往往以“共同犯罪、責任連帶”為由,要求所有共犯對全案違法所得承擔連帶責任,除追繳工資等實際收入以外,仍責令繼續退賠數百萬乃至數億的集資損失。由于以往裁判文書對退賠表述較為原則,加之司法實踐中對責令退賠是否屬于判項長期存有爭議,判后并不移交執行,這一問題沒有凸顯,但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逐步落實,責令退賠作為財產刑執行內容之一被明確,具體刑事執行工作則困難重重,連帶退賠合法性問題也開始被實務部門所關注。其中,由于集資犯罪往往涉及退賠數額巨大,與從犯實際違法所得差額懸殊,特別是事務型幫助犯違法所得退賠問題最為棘手,亟待研究。
一、違法所得退賠責任之爭議
[基本案情]2020年9月23日,S市S區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王某(1991年生、大專文化)參與某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擔任該公司實際控制人的秘書,從事廣告宣傳等具體工作,獲利人民幣20萬元左右,并認定在王某工作期間,該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所造成的實際損失數額為4億余元。因王某認罪認罰,且主動退出違法所得20萬元,據此,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罰金6萬元,扣押、凍結在案的違法所得發還各投資參與人,不足部分責令繼續退賠后發還,扣押在案的涉案物品,予以沒收。該判決生效后,2021年5月12日,該法院發出《執行通知書》,要求王某繳納罰金6萬元和未退出的違法所得4億余元。2021年6月15日,王某提出執行異議。2021年6月16日,法院駁回執行異議。盡管異議被駁回但王某依然不服,多次信訪。
針對上述案例中王某是否應對全案損失承擔連帶退賠責任,實踐中并非沒有爭議。肯定的觀點認為,王某作為幫助犯,應對全案犯罪數額承擔連帶退賠責任,理由是: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由共同侵權人對被害人人身損害承擔連帶責任,有法律明確規定;共同犯罪、責任連帶是刑法理論通說,而且符合以往司法實踐慣例;只有讓所有共犯都對被害人損失承擔連帶退賠責任,才更有利于追贓挽損;采用連帶責任還有利于平復被害人感情,有利于在涉眾型案件中維護社會穩定。相反,否定的觀點認為,王某作為從犯,不應對全案犯罪數額承擔連帶退賠責任,而只應承擔與其犯罪地位作用相適應的退賠責任。理由是: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從犯承擔的退賠責任只能是與其犯罪地位作用相適應的責任;如果要求從犯承擔超過與其犯罪地位相適應的責任,就有權力濫用之嫌,而且也完全堵死了從犯改過自新的道路,不符合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讓從犯對被害人損失承擔連帶退賠責任,難以得到從犯及其家屬配合,結果并不一定真的有利于追贓挽損,降低責任反而有可能激發從犯及其家屬退賠的積極性。
二、違法所得退賠連帶責任之否定
在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所謂業務型幫助犯往往指直接從事集資業務,并從集資業務分成或者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的幫助犯,如業務員、業務主管、業務經理等。與業務型幫助犯不同,事務型幫助犯是指不從事集資業務,僅負責行政事務,不從集資業務中提成,僅領取正常、固定工資的幫助犯,如上述案例中王某就屬于事務型幫助犯。如果說業務型幫助犯因其直接開展集資業務,對集資成功作用較大,部分甚至經手集資款,領取高額回報,判決僅要求其對參與數額承擔連帶退賠責任尚可理解的話,那么要求不從事集資業務、不領高額回報的事務型幫助犯對全案數額承擔連帶退賠責任,確實值得商榷,這也是連帶退賠在事務型幫助犯中矛盾最為尖銳的原因所在。
(一)“共同犯罪、責任連帶”并非刑法理論的通說
實踐中,法院責令事務型幫助犯對集資參與人損失承擔連帶責任時,往往以“共同犯罪、責任連帶”為由,認為此乃刑法理論的通說。對此,必須要說明的是,刑法理論中從來沒有“共同犯罪、責任連帶”的說法,與之相似的表述為“部分實行、全部責任”[1]。刑法中就共同犯罪采取“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分擔了部分實行行為,或者僅實施了幫助、教唆的非實行行為,也要對全部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然而,這一原則既不意味著共同犯罪人之間責任是無差別的,也不意味著共同犯罪人之間責任是連帶的。相反,根據理論界權威觀點,“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對各共同犯罪人處理時需要區別對待”[2],“共同犯罪人的社會危害程度不同,需要根據一定標準進行分類,據以確定不同的刑事責任”[3]。可見,理論界真正的通說乃“共同犯罪、責任自負”,或者說“違法共同,責任個別”。從目前理論界最為有力的階層犯罪論體系看,犯罪實體即不法與有責,而不法具有一般性,責任具有個別性,共同犯罪理論作為刑罰擴大事由,不可能解決責任層面的問題,而是主要解決違法事實歸屬問題,回答不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共犯行為為何具有可罰性的問題。共同犯罪中,盡管共犯行為并不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發生,但刑法也要求共犯對危害結果負責,似有連帶表象,但實際上共犯所承擔的責任并非連帶責任,而是與共犯行為對結果實現的加功相聯系,是共犯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表現,并非代人受過、為人所累。前述案例中,王某作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從犯,其所承擔的責任應當歸因于自身的幫助行為,而不是受主犯行為的牽連。
(二)退賠采連帶責任不符合刑罰目的和刑法原則
一方面,從刑罰目的看,不同于刑罰本質與正當化依據,刑罰目的只能在于預防,[4]如果犯罪分子無法通過刑罰改惡從善,就意味著特殊預防徹底失效。對事務型幫助犯,按照連帶責任要求就全案犯罪數額退賠違法所得,雖然有利于保護被害人權益,但往往使犯罪人背負了難以承擔的經濟負擔,幾乎堵死了其悔過自新、回歸正常生活的出路。在羈押執行期間,因不可能全額退賠,其無法減刑、假釋,即使是在刑滿釋放后,由于仍不能全額退賠,其不僅將終生被列入失信黑名單,還將陷入隨時可能被強制執行的恐懼,這對于那些剛剛踏入社會、失足觸犯刑律的年輕人而言,幾乎剝奪了其悔過自新的機會。前述案例中,王某作為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大專畢業生,家庭條件也比較一般,如讓其承擔4億余元的退賠責任,無疑意味著剝奪了其回歸正常生活的可能。
另一方面,從刑法原則看,違反了罪責刑相一致原則。所謂罪責刑相一致原則是指“刑罰的輕重必須與犯罪的輕重相適應,不能重罪輕判,也不能輕罪重判,也即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的大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依據,犯多大的罪就處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當、罰當其罪”。在共同犯罪中,事務型幫助犯作為從犯,與組織犯等主犯和業務型幫助犯等從犯相比,顯然地位和作用不同,社會危害性程度也不同,從主刑和附加刑的裁判結果看也存在顯著差別,但在責令退賠方面卻都一致要求對全案犯罪數額承擔連帶責任,有罰過其罪之虞。從王某的判決結果看,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罰金人民幣6萬元,可見王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遠遠小于主犯,甚至小于部分從犯,這種情況下讓其對全案犯罪數額承擔連帶責任,過于嚴厲。
(三)退賠采連帶責任不利于維護司法權威和公信
在集資類案件中,將全案犯罪數額作為違法所得數額,要求事務型幫助犯承擔連帶退賠責任,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追繳到位。事務型幫助犯主要從事行政事務,領取正常固定工資,實踐中往往是一些依靠工資收入維持日常生活的人員,本人及其家庭并不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即使是經濟條件相對較好,與集資犯罪全案犯罪數額相比也是杯水車薪。這容易造成“司法打白條”的現象,致使程序空轉,對司法權威有害無益。在王某一案中,王某本人根本無法承但連帶賠償責任,還導致了長期多次信訪,不利于維護審判權威。
實踐中,集資類犯罪數額往往特別巨大,而從犯罪獲利角度而言,事務型幫助犯僅領取正常、固定工資,二者相差極其懸殊,從行為人對資金的控制程度而言,事務型幫助犯對集資財物也不能起到支配的作用。在主犯不到案或實際損失巨大的情況下,讓每月僅領取幾千元固定工資的事務型幫助犯對全案犯罪數額承擔連帶退賠責任,即使連帶責任并非獨立責任,人民群眾也往往難以接受。當然,普通群眾的樸素正義觀對于司法辦案并不具有決定意義,從法律引導或教導意義而言,被所謂民意驅從的法律也是不可取的,如對于偷換二維碼取財行為的定性,即使在群眾中也存在一般盜竊說、盜竊罪間接正犯說、一般詐騙說、詐騙罪間接正犯說、三角詐騙說、雙向詐騙說等多種觀點[5],這就需要法律給予專業上的結論。但無論如何,作為人民司法,民意和普通民眾的法感情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實踐中,針對王某一案中連帶退賠的做法,部分人大代表也提出了質疑,遠非“此乃司法實踐的慣例”所能遮蔽的,需要引起重視。
三、與犯罪地位作用相適應的違法所得退賠責任之提倡
實踐中,有觀點認為違法所得退賠本質系由犯罪人承擔的民事責任。對此,我們不能贊同,違法所得退賠是保護集資參與人財產權利的方式,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保護財產權利的法律途徑,既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刑事的,而違法所得退賠就是保護財產權利的刑事手段之一。從立法角度看,違法所得退賠規定在刑法之中,從實踐角度看,違法所得退賠客觀上也無法通過民事訴訟獲得救濟。因此,違法所得退賠就是承擔刑事責任的內容之一。至于退賠數額的界限,建議遵循罪責刑相一致原則,明確集資犯罪中事務型幫助犯違法所得退賠數額,應當與其自身犯罪行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匹配,具體可考慮以實際獲得的傭金為基數,再乘以適當倍數的方式確定最終退賠數額。需要說明的是,交由法官具體裁量并非意味著允許法官恣意,法官確定具體倍數時,既要考慮被害人損失的數額,也要考慮犯罪人作用的大小,還要考慮犯罪人退賠的實際可行性等多種因素綜合確定。
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應按照事務型幫助犯實際所得傭金退賠,而不必再乘以相應倍數。對此,我們認為,上述觀點實質上是從單個共犯實際獲得少量傭金的視角出發,將其違法所得僅限于傭金,從而認為追繳與退賠的對象只能是實際獲得的傭金,如此追繳與退賠總額將遠遠小于集資參與人損失額,其結果必將損害集資參與人的利益。事實上,這是對刑法中“違法所得”這一概念的誤讀。刑法用語的解釋,不僅要采用文義解釋方法,還應采用體系解釋、目的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從而找到刑法用語的合理界限,明確刑法適用邊界。[6]即使在特殊情況下,司法在合理解釋范圍之內適當偏離了刑法用語最常用的意義,但只要具有實質正當根據,也可以視為一種僅僅屬于形式偏離的趨向正義,仍然可以被接納。[7]
通常認為刑法中違法所得系指犯罪分子通過犯罪行為的得利;根據刑事訴訟法有關司法解釋,系指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獲得的任何財產。可見,違法所得即從犯罪人角度出發,以“所得”為標準計算的數額。與之不同,“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條規定,向社會公眾非法吸收的資金屬于違法所得。這就意味著集資犯罪中違法所得是以集資參與人為視角,以“所失”為標準計算數額。兩相對比來看,無論是從“犯罪人所得”角度出發,還是從“集資參與人所失”角度出發,只要將共同犯罪人視為一個整體,從全案來看,二者數額都應當是一致的,即集資參與人集資損失就是所有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站在這一立場上,事務型幫助犯退賠范圍就并非個人實際違法所得,而是全案違法所得中與其犯罪地位作用相適應的那部分違法所得,由于犯罪過程中以及犯罪后犯罪分子往往存在處置、揮霍財物的行為,因此,與犯罪地位作用相適應的那部分違法所得數額往往大于犯罪分子個人實際違法所得數額,至于二者具體的差額,應交由法官在具體案件中根據事實、證據的不同情況加以確定。可見,考慮以實際獲得傭金為基數,再乘以適當倍數的方式確定最終退賠數額,不僅有利于填平補齊被害人損失,保護被害人利益,而且有利于維護罪責刑相一致原則,給予事務型幫助犯改過自新的機會,這不僅是合適的,而且值得被借鑒推廣。對于前述案例中的王某,考慮到其在共同犯罪中具體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從犯地位作用也存在差別)等全案事實和情節,可在追繳傭金的前提下,責令其按照1倍標準繼續退賠違法所得,從而既有利于實現刑罰目的,也有利于維護司法權威,還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利益。
*本文為2022年度上海市檢察官協會重點課題“檢察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的探索與創新”(SH2022309)、2022年度國家信訪局信訪理論研究課題“檢察機關防范和化解信訪矛盾風險研究”(202207001)的階段性成果。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華東政法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201620]
[1] 參見柏浪濤:《刑法攻略》,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頁。
[2] 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頁。
[3] 馬克昌:《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頁。
[4] 參見李冠煜:《從絕對到相對:晚近德日報應刑論中量刑基準的變遷及其啟示》,《東方法學》2016年第1期。
[5] 參見張慶立:《偷換二維碼取財的行為宜認定為詐騙罪》,《東方法學》2017年第2期。
[6] 參見張慶立:《“情節嚴重(惡劣)”的法律解釋》,《法律方法(第33卷)》,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32-335頁。
[7] 參見孫海波:《超越裁判的可能、形式與根據》,《東方法學》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