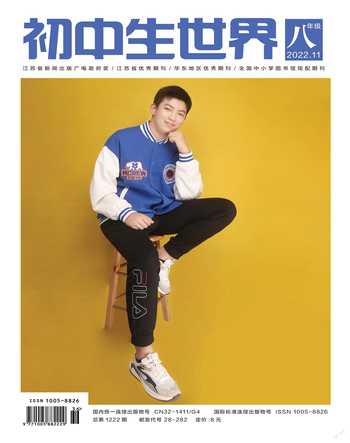向風暴中心駛去
鄭夢雨

“從背后吹來的風有七級,夾雜著水汽,由暖變冷。雷聲不斷在耳邊響起,連帶著地面輕微震動……”
這樣的場景,“00后”追風者蘇鏑坷和搭檔們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上百次。2019年開始,他們追逐并記錄風暴,行程超2萬公里,足跡踏過浙江、內(nèi)蒙古、江蘇、山東等地。
蘇鏑坷目前就讀于中國傳媒大學攝影專業(yè),同時是一名氣象科普博主。在學生身份的另一面,自由與勇氣的呼喚,讓追風少年們一次次迫近“危險”,向風暴中心駛去,與天之神跡打交道,直面大自然的“呼吸”和“脾氣”。
等風來
“風是什么?”對于蘇鏑坷和他的伙伴們而言,它可以是一場風暴,一朵奇妙的云,還可以是一場晚霞,一道彩虹,一次天氣事件。除了臺風,他們也追初雪、寒潮、洪水、沙塵暴。
每次出發(fā),他們都帶著一臺電影攝影機,一臺照相機,一臺運動相機,一架無人機,一部電腦,還有一個用模塊搭建的小盒子——被取名為“MENMOI”的簡易傳感器。
每一次成功追擊都是準確把握時間和地點的結果,需要在分析預報資料后立即作出決策,迅速前往登陸地,隨時調(diào)整。同樣,氣象攝影不僅要求拍攝者對天氣有精準把握,還要具備完備的拍攝策略和預案,預制參數(shù),快速應變。
最現(xiàn)實的考量是城市等級,以確保出現(xiàn)問題時能就近尋求支援。醞釀在山地的風暴比較危險,追風少年們長距離追擊時吃喝經(jīng)常在移動中解決,有時日行千里,路途中只能吃泡面、火腿腸。
更多準備從出發(fā)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事實上,追風者比大眾更明白如何在激烈天氣中保護自己,每一次出發(fā),都是綜合研判地形、城市等級和道路分布等實地情況后的決定。
與風暴正式“交手”前,往往是漫長的旅途。駕車途中,時間和空間感仿佛被弱化,追風者擁有自己特殊的時空衡量尺度。
風暴之下
他們的速度比風更快。
2019年8月,超強臺風“利奇馬”襲擊東南沿海,蘇鏑坷有了第一次直面風暴的機會。在父親的支持下,他開車穿行在臺風登陸區(qū),直面這場“危險的美麗”。這次成功追擊證明了實地追風的可行性,也帶給他強烈的震撼。
對追風者而言,每次追擊風暴都混雜著多重情緒:僥幸、刺激、疲憊、心有余悸。
2021年夏天,臺風“煙花”生成前一周,蘇鏑坷和搭檔注意到了處于襁褓之中的云系。彼時,他們正在山東濰坊追擊強對流,返程的高鐵上,他們觀測了數(shù)據(jù),判斷這個云系很有追擊價值,決定立即前往。
舟山大橋上空空蕩蕩,上島次日凌晨4點,他們就“吃”到了最為猛烈的一次風雨——臺風西北眼墻正在上岸,蘇鏑坷扎起馬步,迎風蹲下,握緊風速計,以防被吹倒。
稍稍打開車門,狂風便瞬間將車門拽開,“差點被‘吸出去”;密集的雨滴伴著狂風砸在身上,有如針扎般的痛感;打開車窗幾秒鐘,狂風灌入車內(nèi),把車里噴上一層薄薄的沙子。
清晨6點,風勢減弱,整個世界風平浪靜。測站大氣壓傳感器清晰地記錄下登陸地的氣壓變化過程。追風小隊驗證了自己正處于臺風眼中心,對他們而言,這是很大的鼓舞,也是一次精準的攔截。
給自然以秩序
追風的過程,對追風者而言是求知和證明的過程。蘇鏑坷感到最有快感的就是自己的預判得到驗證時“整個人會麻”。
許多個追擊現(xiàn)場,他們在車里,和閃電、暴雨一起度過夜晚。
2021年5月的一天,蘇鏑坷收到朋友發(fā)來的雷達圖,顯示武漢西側有一個大紅色的“鉤子”——這是發(fā)生龍卷風的預兆。幾乎同一時刻,蘇州市雷達資料也顯示出現(xiàn)了龍卷風征兆。半個小時后新聞彈窗彈出,蘇鏑坷立即買票直奔蘇州,驅(qū)車趕往盛澤龍卷風災害現(xiàn)場。
“在地面上,什么也看不出來,還以為生活已經(jīng)恢復了。”蘇鏑坷說,“但當我把航拍飛機弄上天后,我驚呆了,畫面中清晰可見綿延3公里的破壞帶,能明確地看到龍卷風的路徑。”
這場強龍卷風破壞了整個盛澤鎮(zhèn)的電力系統(tǒng)。坍塌的房屋和墻體堆在路邊,樹木被連根拔起,甚至樹皮都被剝開,“景象非常慘烈,我拍攝時整個手都忍不住顫抖”。
蘇鏑坷把這次拍攝的畫面提供給了佛山龍卷風研究中心,以供對龍卷風及其影響的后續(xù)研究;隨身攜帶的小型測站記錄數(shù)據(jù)也能夠與國家站數(shù)據(jù)并用互補,用來完善天氣事件的模擬和預警,降低災害損失。
風暴過境
風暴過境后,有時還能在另一側看到彩虹,那是大自然給予追風者的回饋。
臺風愛好者們傾向于賦予其人類般的神態(tài)與情感——它的疾風驟雨好似行走和喘息;它的風雨來自熱帶海洋,有溫暖的氣質(zhì);它在云圖上生成、發(fā)展、增強、到達巔峰、減弱、消亡,也耦合著人類的生命史。
“天氣其實就是一種情緒,而我們?nèi)祟惖男袨椋矔绊懙教鞖獾那榫w。”蘇鏑坷說,“人類的情緒和生活,可能被天氣的陰、晴、雨影響,而人類自身,也正在與一個氣候變化的大時代共存。”
近兩年,他們多次見證這種相互關系。全球變暖的背景下,極端天氣頻發(fā),近海海溫快速升高,登陸臺風數(shù)量多、強度大、影響地域廣。
“云壓過來,農(nóng)田、樹木不怕風暴和閃電,因為風暴會帶來降水和生機,‘災害是之于人的概念,是人類害怕災害,有了人類才有了‘災害。”
“我們不能克制災害,只能順應它,但也正是災害,讓文明得以推進和延續(xù)……”
追風過程中,他們不僅記錄影像,也想把對于人與天地關系的探討和背后的“風暴哲學”做成一部追風紀錄片。
整個夏天,蘇鏑坷和伙伴們一同輾轉(zhuǎn)于全國各地,以身體經(jīng)驗進入天氣事件核心區(qū)域,追逐弧狀云,深入臺風眼,目睹枝狀閃電,暴露于冰雹和雨幕……
2022年9月,副熱帶高壓北抬,云團再次在華東沿海生成。
宇宙天地照常運轉(zhuǎn)。幾個少年又一次出發(fā),向風暴中心駛去。
(選自2022年9月15日《新華每日電訊》,本刊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