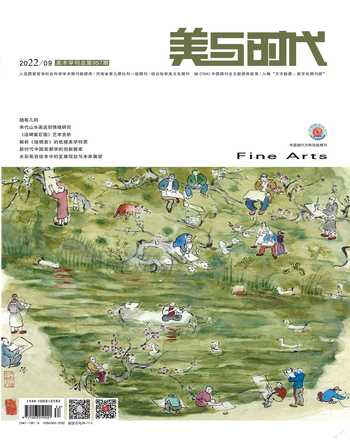元明捉勒題材的技法差異探析
摘 要:元明兩代捉勒題材繪畫作品不在少數,主要以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捉勒花鳥作品《鷹軸》《鷹擊天鵝圖》為例,對元明兩代院體捉勒題材畫作技法風格進行具體分析。梳理了元明兩代院體花鳥畫的風格流變,以及歷史環境、文化因素等影響下的捉勒題材作品,并且運用圖像對比研究法從技法風格特點、構圖形式和內容意義幾個方面進行論述,探討了兩幅畫作之間的異同,對于畫論的分析補充與創新等方面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元明花鳥畫;捉勒題材;技法風格;《鷹軸》;《鷹擊天鵝圖》
從歷代史論著述中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興廢》中,將中國畫分成人物、屋宇、山水、鞍馬、鬼神、花鳥六科,這代表著花鳥畫開始獨立成科。捉勒題材的繪畫作品屬花鳥范疇,即以鷹、隼等猛禽追捕野禽野雉為主題的繪畫作品,在北宋滅亡后,宋人心理發生了激變,因此在南宋時出現了非常多猛禽題材作品,這抒發著國家動蕩時期人們的激憤之情和積郁心態。在蒙元統治時期,治國政策雖較為寬松,但漢民族地位的突降使元人萌生出內斂靜觀的心境[1],出現了許多捉勒題材的繪畫作品。如元代雪界翁和張舜咨合作繪制的《鷹檜圖》,畫中鷹的形象肅穆莊重、威嚴冷峻。佚名作品《鷹軸》是這一時期捉勒題材花鳥畫的典型代表,其畫風淡雅幽柔,用筆骨力強勁,異于南宋技法而自成一格。明代宮廷院體花鳥畫面目一新,在復興唐宋院體工筆風格的基礎上探索出了一條新路。捉勒題材作品相較于元代時隱逸心態之下創作的作品更加奔放,明代畫家殷偕所畫《鷹擊天鵝圖》極具代表性。
一、元明兩代院體花鳥畫風格概況
元代古樸淡雅氣象之風靡。元代花鳥畫主要以水墨寫意形態為主,用簡單清純的墨色代替了以往隋唐五代兩宋時期色彩富麗、異彩紛呈的視覺主流,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受到了南宋的影響。蒙古統治下的元代時期,江浙一帶的畫家心理發生了激變,消極的思想與藝術表現上的水墨審美,正主導著他們的創作格調,如王淵的《桃竹錦雞圖》《竹石集禽圖》和邊魯的《起居平安圖》等這類“墨花墨禽”的水墨風格作品陸續出現。好在此時蒙元統治者對于文人思想及畫法持有包容態度,因此元代宮廷中熱愛書畫的風氣相對來說比較活躍,傳統設色妍麗的院體花鳥畫也逐漸受到元代風格的影響,開始向設色清雅轉變,如錢選的《八花圖卷》、任仁發《秋水鳧鹥圖》等。元代院體工筆形態下的花鳥作品體現著對唐畫神韻的所得,所謂唐畫神韻指的是唐人筆力深厚的細筆畫法和“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繪畫精神相輔相成。趙孟頫曾言:“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2]他認為“古意”是中國畫的內在精神,若失去了這種精神,畫得再工整也無用。
明代宮廷繪畫中,唐宋妍麗富貴之風風靡一時。明代宮廷繪畫呈現出唐宋氣象,源于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制度,廢元蒙興唐宋之舉,以及其獨特的審美思想——喜好雄勇兼具力量的猛禽、“斯理成義”的雁和許多有祥瑞詩情含義的禽鳥。可見在這一時期,捉勒題材花鳥作品成為畫家創作的主流,捉勒題材作品層出不窮,如殷偕的《鷹擊天鵝圖》,林良的《古木蒼鷹圖軸》《秋鷹圖》,呂紀的《殘荷鷹鷺圖》《鷹鵲圖》,蕭海山的《雙鷹老松圖》等。同時,宮廷工筆花鳥畫更加富貴雄邁,樣貌多元。永樂年間,被稱作“當代邊鸞”的武英殿待詔邊景昭復興并發揚了唐宋工筆形態,其技法繼承“黃家富貴”的同時,又具有氣勢磅礴的時代新貌,設色雍容富麗,給人以視覺震懾。同時,孫隆發揚了徐崇嗣的沒骨法,林良開創了水墨花鳥畫的先河,明代宮廷院體花鳥畫再度走向高潮。
二、《 鷹軸 》:古雅風颯
元代的《鷹軸》是一幅主要以細筆筆法表現的工筆花鳥作品,其藝術風格和技法所體現出的繪畫精神與趙孟頫的“古意”思想相近。
作品風格特點方面,一是格調素雅古樸,極具元代氣象。《鷹軸》的設色去除了唐宋時期濃麗的色彩而主要表現為淡雅,整體畫面以大色塊淡墨和白粉為基調,或勾,或皴,或染,或點,節奏時疏時密,筆力時緊時松,層次極為豐富。畫中對鷹的眼、喙、爪的刻畫極其深入。鷹眼以赭墨色為主,層層分染,瞳孔勾點有力,看起來炯炯有神;鷹喙、鷹爪主以墨色和白粉色繪之,使得鷹的形象惟妙惟肖。這種白粉色與赭墨色的結合是冷與暖的交相配合,讓鷹的形象更加生動。二是對唐宋傳統技法的繼承,和對“黃家”觀物之精、布局有序、筆意精妙的風格特點的延續。其中主體物象海東青和白鵝的造型特征刻畫自然生動,線條輪廓微妙精致,墨線與絲毛的用筆有虛實輕重的節奏變化,墨色有干濕濃淡的質感差別,鵝掌與鵝喙主以墨色平涂和分染相結合,分別刻畫出完全不同的質感表現。再如畫中背景顯現梅花、竹葉與坡地的畫法,與蘇軾所贊的“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3]之作《寫生蛺蝶圖》中相對勾染的技法形式相近,相較于“黃家”工筆精謹工細的線條表現來說,加強了收放自如、隨物而化的力度表現。至于雜草的筆法特點,則類似于徐崇嗣沒骨技法的表現形式,直接以色畫之。三是受到元代水墨寫意的影響,粗筆、細筆相結合。水墨寫意體現在配景蘆葦叢和皴染的背景空間。畫家用鏗鏘有力、斷斷連連的線條變化將斜倚倒狀的干枯蘆葦自身的特征和質感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定程度上散發出徐熙那種寓興閑放的意味。“祖宗以來,圖畫院之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4]“白”即崔白,崔白的《雙喜圖》中臨風吹折的雜草用筆文氣靈動,《鷹軸》中蘆葦的畫法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雙喜圖》中粗筆側皴淡染的背景加之細筆精謹渲染的主體,一種秋風蕭瑟之感浸滿整幅畫面,呈現出不失工整的水墨氣象,蘆葉清晰的葉脈和其上斑駁的蟲蛀被真實刻畫出來,相差甚大的濃、淡墨勾畫蘆葦的葉與筋,體現畫家對畫面整體全局的自如把控,用筆骨力強勁,生動瀟灑的寫意精神從畫中涌現而出。
作品內容構圖方面,《鷹軸》圖中左上空有一只仰天疾飛頓翅的海東青,其眼神明亮犀利,身姿矯健雄壯,利爪微握,其匯聚全神正在追捕一只向畫面右下方倉皇逃竄、張翅抻頸長鳴的白鵝。這種利用白鵝負鷹的下墜感,將所擊之鵝排布在畫面右底部,鵝首的延伸線接連微弓姿態的蘆葦叢向左上倚斜,給人一種向上升騰的感覺。這種構圖與南宋李迪之作《楓鷹雉雞圖》和佚名作品《鷹鳧圖》等構圖形式相同,被稱作“對角線”構圖。正如黃賓虹所言:“鷹隼之擊搏,南渡畫家所喜畫。”歷史上捉勒題材的作品內容不外乎兩種情形,一種是正在追逐,另一種是已經捉到。這幅作品中的海東青顯然還在奮力追逐獵物,正如元代王淵《鷹逐畫眉圖》中的情形一樣,且兩幅畫中的鷹除了品種不同,姿態有一種對稱的鏡像相似。
三、《 鷹擊天鵝圖 》:明麗莊典
《鷹擊天鵝圖》是明代畫家殷偕的作品,在《明畫錄》卷六中曾有記載:“殷善,字從善,江寧人。花木翎毛從林良、呂紀兩派中來,渲染有致而神采獨異。”
在技法風格特點方面,首先“治隆唐宋”思想之下宋人院體畫風強烈,造型具有裝飾感。畫中采用傳統工筆勾線技法,以淡墨勾之,后設色渲染。圖中海東青和天鵝的羽毛畫法與南宋李迪《楓鷹雉雞圖》中鷹羽的畫法相似。李迪所畫鷹羽以沒骨的手法用淡墨點厾而成,用筆較寫意畫法更工細嚴謹。另外,與元代邊魯所作《起居平安圖》中錦雞背羽的表現手法也比較相近,只是殷偕用白粉代替墨繪之。對于鷹、天鵝的造型,一是殷偕精心設計,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主體物身體的各個部位的羽毛排布,用厚重的白粉將輪廓表現得清晰分明。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鷹、天鵝的眼都分別用白粉點厾了高光,在當時這種畫法并不多見。這兩種獨特的畫法一定程度上為畫面增添了裝飾效果。其次沿襲元代水墨野逸之風,設色對比鮮明,別具一格。對于畫面的選擇,賓主有序、層次分明,除去主體物的鷹與天鵝,襯景以坡地和蘆葦營造一種置身荒野之感,設色淡雅至極,這是元代特有的清雅質樸的遺風。畫中主體鷹與天鵝以白粉用色厚重呈現,繪制在仿古底色的紙本上,視覺沖擊力極強。這種白粉層加積厚的效果類似于邊景昭《竹鶴圖軸》的畫面效果,但與之不同的是,殷偕不是大面積平涂白粉,而是片片分明。設色鮮明除了上述所討論的主體物和底色的對比強烈外,還體現在畫面中的重色都是主體物的關鍵部位,如鷹、天鵝的眼、喙,還有天鵝的腳掌部分,都使用濃墨畫之,使之更加醒目,增添了畫面的節奏感與豐富度。
《鷹擊天鵝圖》畫面中主體幾乎占據畫中三分之二的部分,體量最大的是被一只背部花白的海東青奮力攥住頭顱,并懸在空中,仰面朝天,面露恐懼與哀愁的悲鳴的天鵝。海東青用比天鵝小好幾倍的身體壓制在其上,眼神明亮,氣勢逼人,海東青與天鵝的位置以反“S”型的構圖呈現在畫面之中,有強烈的動態特征。以天鵝的身頸為主線,后到海東青的喙處,構圖趨勢往反向回旋,承接底部淡染的坡地石頭、勾畫的蘆葦野草,體現出一片風疾吹拂的野外之景。這種類別的構圖形式在中國畫中屢見不鮮,明代林良的《秋鷹圖》也是如此。
四、《 鷹軸 》與《 鷹擊天鵝圖 》技法風格差異
兩幅作品的用筆技法與風格不盡相同,雖都有唐宋遺風,但《鷹軸》圖是細筆、粗筆相結合的表現形式,主體物采取工筆勾勒分染的方式,如根根羽毛的絲毛、白粉分染出深淺濃淡的羽色變化、鷹爪清晰的紋路鱗片,還有鵝掌粗糙的紋理質感,盡顯生動,鷹與背景之間淡墨分染過渡得十分自然。這些特定的處理技法和繪畫方式是宋元工筆花鳥畫最為常見的手法。《鷹軸》的襯景以粗筆勾畫或直接以色涂之,畫中粗筆線條斷連有力,勾勒出干枯挺立的蘆葦枝葉,信筆點厾出隨風靈動的蘆葦穗,側鋒勾皴出的蒼勁梅枝和翠潤竹葉,還有以淡墨花青色直接勾畫的纖細雜草等,表現技法豐富。而《鷹擊天鵝圖》主體部分的技法表現看似與傳統工筆技法雷同,但細細觀察實則不同。首先比較兩幅作品中的海東青脖頸和胸腹羽毛的刻畫。殷偕所畫的羽毛是用筆直接點畫出羽毛的形狀,羽毛外輪廓是否用淡墨勾勒已經看不清,或許全部以白粉覆之也未可知,其絲毛融在羽色中,與《鷹軸》羽毛的白粉絲毛相比不夠清晰。從脖頸的羽毛到胸腹的羽毛來看,《鷹軸》圖能夠看到清晰的淡墨勾勒出的羽毛的外輪廓,設色淡雅,單根羽毛的深淺變化相差較大,絲毛也清晰顯現出來。《鷹擊天鵝圖》中的襯景用筆隨意率性,略顯刻板與拘謹,明顯遜于《鷹軸》。比較蘆葦穗的用筆,《鷹軸》蘆葦穗能看出用筆的輕重和穗的疏密變化,而《鷹擊天鵝圖》整體蘆葦穗的用筆較為中庸,沒有明顯的輕重節奏變化,用筆較含蓄內斂。二者對于坡地的染色表現也十分不同,《鷹軸》采用山水畫中皴染的用筆技法,以大筆側鋒皴出背景層次豐富的空間,《鷹擊天鵝圖》則較為保守和謹慎,用分染的形式渲染背景和坡地,幾乎不顯筆觸。
兩圖氣質風貌迥異。《鷹擊天鵝圖》主要是一幅工筆花鳥作品,但主體物描繪方式上有裝飾性效果,如對主體物象鷹與天鵝的羽毛結構、身形輪廓、羽上花紋等細節處理較為簡單,整體排布組合都較為簡略,顯現一種規矩且程式化的畫面效果。但《鷹軸》的作者用筆變化十分微妙豐富,主體物的羽毛都以淡墨勾勒輪廓,后用白粉多遍分染出虛實效果,對整體物象結構變化由內而外的細節變化刻畫精細,不僅區分出了整潔的羽毛、掉落的羽毛和折損的羽毛等,還區別了物象身體各個部位的羽毛特點,乃傳承了“黃家”精妙的傳統技法用筆,細微精妙,虛實相襯,生動形象。另外,《鷹軸》設色更為古樸自然,顯然作者受到元代水墨花鳥畫的影響。而《鷹擊天鵝圖》的設色并不妍麗,以墨色、白粉、花青為基調,整體雖淡雅,但在設色對比度上更為突出。
兩圖的內容與構圖形式不同。雖然同樣以鵝負海東青為主題,但《鷹軸》圖是海東青追捕中的場景,《鷹擊天鵝圖》是追捕到獵物之場景,為兩種捉勒題材類型。構圖分別以“對角線”和“S型”的形式出現,表現出的情境與畫面事態的發展十分相配。
五、《 鷹軸 》與《 鷹擊天鵝圖 》之間的偶然關聯
筆者在對兩圖進行分析,探尋兩幅畫作之間的聯系時,發現明代畫家殷偕所畫的《鷹擊天鵝圖》的靈感與啟發或許是來自元代的《鷹軸》。殷偕發散思維,聯想到時間瞬變之后的畫面。從《鷹軸》的畫面可知,一只眼神犀利、身姿雄健的海東青正在追逐一只倉皇飛逃的大白鵝,背景中的蘆葦叢和土坡在畫面的右側,展示出周遭一片荒野之景。而明代殷偕的《鷹擊天鵝圖》中,海東青張開利爪,緊攥白鵝的頭部,此時白鵝已經肚腹朝天,失去了博弈之力。背景的蘆葦叢與土坡則畫在了畫面的左側,仿佛是海冬青飛跨過蘆葦蕩的場景挪移。兩幅作品基調驚人地相似,又巧合地跨越時空產生了因果聯系,這使筆者不得不由此猜想推測殷偕作品的源頭。
參考文獻:
[1]孔六慶.中國畫藝術專史:花鳥卷[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252.
[2]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中國書畫全書:第6冊[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394.
[3]陳高華.宋遼金畫家史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7.
[4]宣和畫譜:卷十八[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18.
作者簡介:
卓拉,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花鳥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