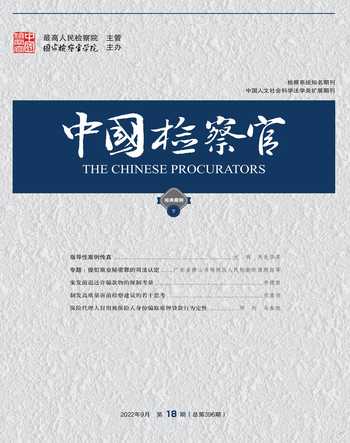依法懲治新型毒品犯罪 推進毒品問題綜合治理
元明 肖先華
編者按:2022年6月24日,最高檢發布了第三十七批指導性案例(檢例第150—153號)。該批案例以懲治新型毒品犯罪為主題,主要涉及介入偵查,引導偵查機關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證據,依法準確認定涉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等新型毒品犯罪的性質,推進新型毒品問題治理等內容。為充分發揮該批案例示范、引領和指導作用,本刊特約請最高檢第二檢察廳就該批案例進行整體解讀,辦案檢察院圍繞所辦案件重點、難點、亮點等問題撰文。為方便讀者閱讀,每篇案例解讀文章均附案情相關二維碼,掃碼即可閱讀。
摘 要:2022年6月24日,最高檢公開發布了以懲治新型毒品犯罪為主題的第三十七批指導性案例。該批案例主要涉及介入偵查,引導偵查機關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強化證據審查,依法準確認定涉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等新型毒品犯罪的性質,延伸司法辦案效果,推進新型毒品問題治理等內容。該批指導性案例對于檢察機關辦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起到示范、引領和指導作用。下一步,檢察機關將在保持高壓態勢、增強工作合力、確保辦案質量、提升履職能力、推進綜合治理方面持續發力,進一步提升毒品問題治理效能。
關鍵詞: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 欺騙他人吸毒罪 麻醉藥品、精神藥品 證據審查 法律適用
一、新型毒品犯罪指導性案例編發的背景情況
禁毒工作事關國家安危、民族興衰、人民福祉,厲行禁毒是黨和國家的一貫主張。近年來,毒品犯罪案件數量呈現逐年下降態勢,禁毒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同時,受國內外各種因素影響,新型毒品層出不窮,禁毒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據統計,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涉新型毒品犯罪16萬多人,其中,起訴涉甲基苯丙胺(冰毒)等毒品犯罪15萬余人,起訴涉新精神活性物質犯罪1.8萬人。從辦案情況看,當前新型毒品犯罪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案件總體呈上升態勢。近年來檢察機關起訴毒品犯罪案件總數逐年下降,由2019年的10.9萬人下降至2021年的7.5萬人。但起訴的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在毒品案件中的占比由2019年的53%上升至2021年的57%。其中,近3年起訴涉新精神活性物質犯罪分別為5183人、5549人、5561人,分別占當年新型毒品犯罪起訴數的8.8%、11%、12.7%,增長較快。二是合成大麻素類毒品犯罪增長迅速。涉新精神活性物質犯罪案件中,氯胺酮及苯環利啶類為主流,占起訴數的46%。2021年7月,國家將合成大麻素類物質列管后,全年起訴相關犯罪1078人,同比增幅257%;2022年1至3月已起訴相關犯罪464人。此外,三唑侖、阿普唑侖、γ-羥丁酸、芬太尼等新型毒品犯罪也多發。三是犯罪手段網絡化明顯,查辦難度大。犯罪分子普遍利用互聯網進行毒品交易,采用電子支付等非接觸方式完成,交易流程的“人、毒、財”分離。在交付環節,多采用寄遞方式,使用虛假寄件人、收件人身份和地址,利用“跑腿”“同城直送”等方式寄遞的案件增長較快。“網絡+寄遞”的形式,已成為販運毒品的重要方式。在聯系交易環節,犯罪分子除使用大眾化的即時通訊社交軟件外,還使用閱后即焚等新型通訊軟件,采用代號、術語進行聯系,犯罪手段隱蔽,證據收集、審查難度大。四是涉案人員累犯、再犯多,呈現年輕化趨勢。大部分販毒人員同時也是吸毒人員,“以販養吸”較為普遍。為尋求刺激,青少年容易成為新型毒品濫用的高危人群,吸食的同時也參與販賣。一些慣犯利用部分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分辨能力弱的特點,引誘青少年實施新型毒品犯罪。
針對新型毒品犯罪,近年來檢察機關一手抓打擊,一手抓治理,不斷提升懲治效果。最高檢指導辦理了河南趙某販賣、制造毒品案等一批重大犯罪案件,與公安部掛牌督辦了“2021-96”等多起重大新型毒品案件;推動有關部門對芬太尼類物質整類列管;發函國家禁毒辦,推動相關部門對氟胺酮等18種物質進行列管;組織“防范新型毒品,呵護無悔青春”為主題的第40次檢察開放日活動,指導各地檢察機關廣泛開展防范新型毒品的宣傳教育活動。為進一步加強辦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業務指導,解決重點難點問題,提高辦案質量,推動各地檢察機關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最高檢第二檢察廳根據《2022年指導性案例工作計劃》,著手編寫新型毒品犯罪指導性案例。第二檢察廳從各地報送的181件備選案例中篩選、編寫了備選案例,分別征求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最高法刑五庭、國家禁毒辦、海關總署緝私局、國家藥監局綜合司等部門、部分省級檢察院重罪檢察部門以及最高檢專家咨詢委員、重罪檢察專家庫成員的意見。2022年6月16日,最高檢第十三屆檢察委員會第一百零一次會議審議決定,將王某販賣、制造毒品案等四件案例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這批指導性案例罪名主要包括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罪、欺騙他人吸毒罪等,涉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特別是如何準確區分毒品犯罪與食品、藥品犯罪等疑難復雜問題,為各地開展引導偵查取證、證據審查、庭審指控、法律適用等工作提供指引。案例展示了檢察機關主動參與禁毒治理工作成效,同時對社會公眾起到法治宣傳、警示教育作用,提升全社會的法治意識和識毒、防毒、拒毒意識。
二、新型毒品犯罪指導性案例的主要內容
(一)王某販賣、制造毒品案(檢例第150號)
2016年,被告人王某明知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γ-羥丁酸可以由當時尚未被國家列管的化學品γ-丁內酯(2021年被列管為易制毒化學品)通過特定方法生成,為謀取非法利益,多次購進γ-丁內酯,添加香精制成混合液體,委托廣東某公司(另案處理)為混合液體粘貼“果味香精CD123”的商品標簽,交由廣東另一公司(另案處理)按其配方和加工方法制成“咔哇氿”飲料。王某通過四川某公司將飲料銷往多地娛樂場所。至案發,共銷售“咔哇氿”飲料52355件(24瓶/件,275ml/瓶),銷售金額人民幣1158萬余元。經鑒定,“果味香精CD123”“咔哇氿”飲料中均檢出γ-羥丁酸成分,含量分別為2000-44000?g/ml、80.3-7358?g/ml。
辦理該案過程中,公安機關以王某涉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圍繞王某涉嫌犯罪主觀故意、案件定性等方面積極引導偵查,審查認為王某具有制造、販賣毒品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符合販賣、制造毒品罪的構成要件,以王某犯販賣、制造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以販賣、制造毒品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15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427萬元。該案提煉的要旨是,行為人利用未列入國家管制的化學品為原料,生產、銷售含有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成分的食品,明知該成分毒品屬性的,應當認定為販賣、制造毒品罪。檢察機關辦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應當審查毒品含量,依法準確適用刑罰。對于毒品犯罪所得的財物及其孳息、收益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沒收。
(二)馬某某走私、販賣毒品案(檢例第151號)
2020年8月16日,馬某某在網絡上發布信息,稱有三唑侖及其他違禁品出售。2021年4月16日,馬某某通過網絡向境外賣家求購咪達唑侖,并支付人民幣1100元。后境外賣家通過快遞將一盒咪達唑侖從德國郵寄至馬某某的住處,馬某某以虛構的“李某英”作為收件人領取包裹。后馬某某以名為“李醫生”的QQ賬號,與“陽光男孩”等多名QQ用戶商議出售三唑侖、咪達唑侖等精神藥品,馬某某尚未賣出即于同年7月15日被民警抓獲。民警在其住處查獲咪達唑侖36ml、三唑侖3.25mg、阿普唑侖28.8mg。
辦理該案過程中,檢察機關引導偵查機關調取馬某某任職情況、學歷證書、發布信息網頁截圖、網絡聊天記錄等證據,并查清涉案精神藥品的來源和用途。公安機關以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審查認為馬某某除構成走私毒品罪外,還涉嫌販賣毒品罪,以走私、販賣毒品罪對其依法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以走私、販賣毒品罪判處馬某某有期徒刑8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千元。該案提煉的要旨是,行為人明知系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出于非法用途走私、販賣的,應當以走私、販賣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行為人出于非法用途,以販賣為目的非法購買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應當認定為販賣毒品罪既遂。檢察機關應當綜合評價新型毒品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依法提出量刑建議。
(三)郭某某欺騙他人吸毒案(檢例第152號)
2015年,郭某某為尋求刺激,產生給其女友張某甲下“迷藥”的想法。此后,郭某某通過網絡了解藥物屬性后多次購買三唑侖、γ-羥丁酸。2015年至2020年間,郭某某趁張某甲不知情,多次將購買的“迷藥”放入張某甲的酒水飲料中,致其出現頭暈、惡心、嘔吐、昏睡等癥狀。其中,2017年1月,郭某某將三唑侖片偷偷放入張某甲酒中讓其飲下,致其昏迷兩天。2020年10月5日,郭某某邀請某養生館工作人員張某乙及其同事王某某(均為女性)到火鍋店吃飯。郭某某趁兩人離開座位之際,將含有γ-羥丁酸成分的藥水倒入兩人啤酒杯中。后張某乙將啤酒喝下,王某某察覺味道不對將啤酒吐出。不久,張某乙出現頭暈、嘔吐、昏迷等癥狀,被送醫救治。張某乙的同事懷疑郭某某下藥,遂向公安機關報案。
辦理該案過程中,檢察機關根據郭某某給人下“迷藥”的事實和證據,引導偵查機關從欺騙他人吸毒罪的角度取證,重點調取涉案電子數據以及郭某某身份、工作職責等方面的證據,且以查證毒品來源為主線自行補充偵查,以郭某某犯欺騙他人吸毒罪依法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以欺騙他人吸毒罪判處郭某某有期徒刑3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千元。該案提煉的要旨是,行為人明知系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而向他人的飲料、食物中投放,欺騙他人吸食的,應當以欺騙他人吸毒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為實施強奸、搶劫等犯罪而欺騙他人吸食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應當按照處罰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責任。檢察機關應當加強自行補充偵查,強化電子數據等客觀性證據審查,準確認定犯罪事實。
(四)何某販賣、制造毒品案(檢例第153號)
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間,被告人何某明知某類樹皮含有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成分,為謀取非法利益,通過網絡購買某類樹皮,磨成粉末后按特定方法熬制成水溶液“死藤水”,先后三次販賣給袁某某、傅某某、汪某吸食,非法獲利人民幣1800元。2019年9月23日,何某被公安機關抓獲,在其住處查獲某類樹皮粉末,凈重256.55g。歸案后,被告人何某檢舉揭發他人犯罪并查證屬實。
辦理該案過程中,針對未能扣押毒品“死藤水”實物的情況,檢察機關建議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實驗,并列明實驗要求和注意事項,后成功獲取“死藤水”樣本一份。公安機關以何某涉嫌販賣毒品罪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審查認為,何某除涉嫌販賣毒品罪外,還涉嫌制造毒品罪,以販賣、制造毒品罪對其依法提起公訴。法院經審理,以販賣、制造毒品罪判處何某有期徒刑1年9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千元。該案提煉的要旨是,行為人以原生植物為原料,通過提煉等方法制成含有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物質,并予以販賣的,應當認定為販賣、制造毒品罪。辦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實驗,查明案件事實。
三、新型毒品犯罪指導性案例的相關問題
(一)關于新型毒品的概念和危害
“新型毒品”是相對于傳統毒品而言的,一般是指通過化學方法進行合成的毒品,即除傳統的阿片類、大麻類、可卡因類以外的其他毒品,包括甲基苯丙胺(冰毒)和其他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等。其中,新精神活性物質(未被聯合國1961年《麻醉品單一公約》和1971年《精神藥物公約》列管的物質)作為近年來出現的新型毒品,其濫用逐漸增多。近年來,新型毒品翻新變化快,檢察機關辦案中已涉及“咔哇氿(含γ-羥丁酸成分)”“死藤水(含二甲基色胺成分)”“神仙水(含氯胺酮等成分)”“開心水(含冰毒等成分)”“浴鹽(含卡西酮成分)”“阿拉伯茶(含恰特草成分)”“郵票(含LSD成分)”“聰明藥(含莫達非尼成分)”“小樹枝(含合成大麻素成分)”“藍精靈(含氟硝西泮成分)”等諸多新型毒品。
當前,社會上一些人對新型毒品的危害認識不足,重視不夠,認為新型毒品吸食后雖然使人興奮、刺激,但不上癮、危害小,后果不嚴重。實際上,這些都是對新型毒品危害性的誤解,值得高度警惕。一是新型毒品對身體機能損害大。吸食新型毒品可以在短時間內使人精神興奮、產生幻覺,同時對人的記憶力和思維能力造成損害,連續使用會造成大腦神經細胞嚴重損傷甚至退變,導致機體的其他系統功能受到嚴重損傷。二是新型毒品有很強的成癮性。許多吸毒者為了尋求刺激而把吸食新型毒品當成一種時尚行為,一些新型毒品,如苯丙胺類毒品,比傳統毒品的毒害性和成癮性更強,不易戒除,即使戒除復吸率也更高。三是新型毒品衍生犯罪危害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新型毒品麻醉的功效,進行強奸、猥褻、搶劫等犯罪活動;還有的人吸食毒品后自控力下降,出現幻覺,實施毒駕、傷害,甚至殺人犯罪,危害極大。四是新型毒品迷惑性強。新型毒品花樣繁多,有的被偽裝成餅干、巧克力、飲料、“電子煙”等,具有隱蔽性和迷惑性,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以迎合青少年群體好奇心強等特點,引誘青少年吸食服用。這批指導性案例涉及的γ-羥丁酸、三唑侖、咪達唑侖、阿普唑侖和二甲基色胺均屬于新型毒品范疇,案例發布有利于指導辦案、警示教育社會公眾。
(二)關于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法律適用問題很多,其中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等問題是當前辦案的難點。這批指導性案例主要聚焦以下法律適用問題:一是毒品犯罪與涉食品犯罪的區分。對于行為人以化學品為原料,生產、銷售含有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成分的食品,明知該成分毒品屬性的,應當認定為販賣、制造毒品罪。行為人對化學品可生成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特性并不明知,對于制出的成分物質系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毒品亦不知情的情形下,如果化學品屬于食品原料,超限量、超范圍添加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應當按照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定罪處罰;如果化學品系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應當按照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行為人犯販賣、制造毒品罪,同時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或者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應當按照處罰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責任。二是毒品犯罪與涉藥品犯罪的區分。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有雙重屬性,可用于醫療、教學、科研等合法使用,也可作為毒品濫用。對于麻醉、精神藥品的用途,可以從行為人買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是否有合法目的予以認定,除醫療、教學、科研等合法目的以外的用途,原則上均應當認定為非法用途。對于向販毒、吸毒人員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應當按照販賣毒品罪進行追訴。對于非醫療、教學、科研等合法用途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以及出于放任的故意,向不特定的人非法販賣的,均應當按照販賣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三是下“迷藥”行為的認定。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為實施強奸、搶劫等犯罪,給人投放“迷藥”(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應當按照強奸、搶劫等嚴重犯罪處理。特別是要充分考慮犯罪行為的時空等具體情形,對于以發生性關系為目的投放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符合強奸罪等嚴重犯罪構成要件的,要以強奸罪等犯罪進行追訴。行為人明知系國家列管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而采取隱蔽手段讓他人吸食,對強奸等行為不足以認定的,可以按照欺騙他人吸毒罪定罪處罰。四是利用原生植物制成毒品和未管制原生植物的區分。以國家未管制但含有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成分的原生植物為原料,通過特定方法,將植物中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成分提煉制成相關物質,改變了原生植物的物理形態,該物質具有使人形成癮癖的毒品特征,應當認定為毒品,行為人依法構成制造毒品罪。對于未被國家管制的原生植物,以及通過研磨等方式簡單改變外在形態的植物載體,雖含有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成分,不認定為毒品。五是新型毒品犯罪的量刑。新型毒品混于飲料、食品中,往往含有大量水分或者其他物質,涉案毒品含量應當酌情予以考慮。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時,應當考慮毒品數量、折算比例、效能及濃度、交易價格、犯罪次數、犯罪既未遂、違法所得、危害后果、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等各種因素。對于將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用于實施其他犯罪的,還應當考量其用途、可能作用的人數及后果、其他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等,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三)關于新型毒品犯罪的證據審查問題
新型毒品犯罪手段隱蔽,收集、固定證據難度大,檢察機關應當強化證據審查,完善證據體系,為準確定罪量刑打下堅實基礎,確保案件質量。這批指導性案例主要聚焦以下證據審查問題:一是強化引導偵查取證。檢察機關應當引導偵查機關采取各項偵查措施,全面收集、固定新型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特別是要著重加大對關鍵客觀性證據的收集,尤其要重視手機、電腦中電子數據的勘驗、提取和恢復、檢索,準確認定犯罪事實。要做好補充偵查工作,及時對新型毒品成分、來源和用途等事實進行補充偵查,制作具體可行的補充偵查提綱,跟蹤落實補充偵查情況。必要時,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履行自行補充偵查職能,全面、公正評價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及后果。在制造毒品方法存疑等情形下,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實驗,列明實驗要求和注意事項,依法及時固定證據,以查明案件事實。二是加強涉毒資產的審查。追繳涉毒資產是懲治毒品犯罪的重要內容,對于提升懲治毒品犯罪質效具有重要意義。檢察機關應當依法引導偵查機關及時對涉案資產進行查封、扣押,全面收集、固定證據。對于偵查機關移送的涉案資產,要著重審查性質、權屬及流轉,嚴格區分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本人財產與其家庭成員的財產,并在提起公訴時提出明確的處置意見。對于毒品犯罪所得的財物及其孳息、收益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沒收。三是強化新型毒品用途和主觀明知的審查。行為人對于毒品主觀上是否明知,是認定新型毒品犯罪的關鍵問題。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鎮靜、安眠等藥用功效,往往成為行為人抗辯其毒品屬性的借口。檢察機關不能僅憑行為人口供,還應當根據其對相關物質屬性認識能力、認知能力、學歷、從業背景、是否曾有同類藥物服用史、是否使用虛假身份交易、生產制作工藝等證據進行綜合認定。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是否用于非法用途也關系到毒品犯罪是否成立。對于“非法用途”的審查,檢察機關可以從行為人買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是否用于醫療等合法目的予以認定。對于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系國家管制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仍利用其毒品屬性和用途的,應當依法認定相關物品為毒品。
四、下一步工作考慮
檢察機關將以此批指導性案例發布為契機,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依法懲治和預防新型毒品犯罪,進一步提升毒品問題治理效能。
一是保持高壓態勢。強化大局意識和擔當意識,充分認清新型毒品犯罪的危害,堅持對這類犯罪“零容忍”。依法嚴懲走私、制造毒品、大宗運輸販賣毒品和非法生產、買賣制毒物品等源頭性新型毒品犯罪,堅決從嚴懲處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累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新型毒品犯罪分子。
二是形成工作合力。加強與郵政、醫藥衛生、網信、市場監管等部門聯系和溝通,健全協作機制,加大信息共享,著重加強新型毒品問題巡查和預警監測。落實“七號檢察建議”,加強寄遞行業監管,堵塞新型毒品流通渠道。深化打擊涉毒洗錢犯罪,建立司法機關、金融、海關等部門共同參與的涉毒資產查繳協調機制。加強司法機關之間的溝通協調,統一執法司法標準。
三是確保辦案質量。建立辦理重大毒品案件介入偵查機制,引導偵查機關完善證據體系和證據鏈條。積極開展自行補充偵查,加強對電子證據的審查力度,積極邀請檢察技術部門參與電子數據勘查、修復和審查,獲取關鍵的客觀性證據。辦案中聘請有醫藥學知識的專業人員對新型毒品進行分析研究,準確認定毒品危害,確保案件質量。
四是提升履職能力。加強指導性案例的解讀和培訓,針對實踐中新型毒品犯罪證據審查和法律適用難點問題,如入罪標準、主觀明知、毒品含量、危害性認定等,通過制發規范性文件,強化案例指導等方式予以解決。健全公檢法聯合培訓機制,統一司法理念,提高辦案能力和專業化、職業化水平。
五是推進綜合治理。針對辦案中發現的未被列管但存在濫用情形的新精神活性物質,及時向有關部門提出列管的意見。落實普法責任制,通過案例宣傳、模擬法庭、新聞發布、檢察開放日等形式,提高人民群眾對新型毒品的認知和防范能力。尤其針對青少年等重點人群,通過法治副校長宣講等形式,筑牢青少年拒毒防毒思想防線。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社會管理漏洞,特別是對易制毒物品、制毒工具、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的銷售監管環節,通過制發檢察建議等方式促進有效監管,堵塞監管漏洞,推動禁毒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廳長、一級高級檢察官,全國檢察業務專家[100040]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干部[10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