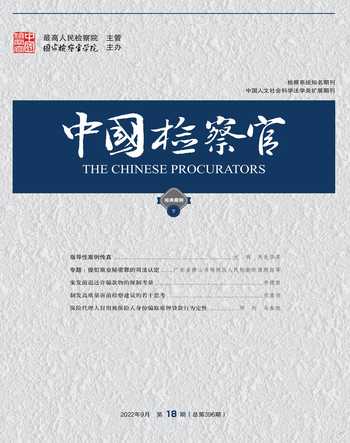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行為構造與罪量標準
編者按:商業秘密作為企業重要的知識產權,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對企業的生存和創新發展至關重要。為進一步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侵犯商業秘密罪作出了較大修改,降低本罪入罪門檻,加強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懲處力度,以強化對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在司法實踐中,對“商業秘密”的審查認定是辦理此類案件的重點和難點,本刊特聚焦實踐中侵犯商業秘密相關案例,請作者分別圍繞案例,對“商業秘密”的核心特征及其審查認定進行探討。同時,特別邀請本刊實務咨詢專家——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朱剛同志作為點評嘉賓,對兩篇文章的主要內容進行評析,并提煉實踐中辦理侵犯商業秘密類案件對行為對象的審查認定標準,為進一步統一司法適用提供借鑒。
摘 要: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作出了較大的修改,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刑事制裁范圍出現了新問題。在實質的、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出臺之前,商業秘密“同一性”和“秘密性”的判斷仍是司法實踐中判斷侵權行為是否成立的重要基準;應將“非法獲取行為”作為本罪的構成要件行為類型,技術員工離職后,對原公司的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是一種法定義務;即使“重大損失”要件被刪除,其依然是判斷“情節嚴重”的重要因素,凡是可以衡量企業競爭性利益減損程度的指標均可作為評價對象。
關鍵詞:侵犯商業秘密罪 同一性 秘密性 重大損失
一、侵犯商業秘密罪認定中的爭議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作出了較大的修改[1],首先,將“情節嚴重”作為入罪的衡量標準,破除了司法實踐長期唯“損失數額論”的現象。然而,在新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以“情節嚴重”作為入罪標準,由于各種考量因素的范圍和程度具有不確定性,在適用中司法機關可能無所適從。其次,刪除了商業秘密的定義,對于“密點”[2]的認定亟需實質的、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最后,用“違反保密義務”取代“違反約定”,由此產生保密義務主體的界定問題。廣東格蘭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格蘭仕公司”)被侵犯商業秘密案幾乎覆蓋了以上所有問題的處理。
[基本案情]劉某原系格蘭仕公司磁控管部門的核心技術人員,熟悉生產設備、工藝流程等一系列配套工作。中山市A公司為生產磁控管便找到劉某。劉某辭職后到中山市A公司實際出資且新成立的中山市B公司任職磁控管研發負責人。劉某在獨立研發B公司的磁控管過程中,使用了其在格蘭仕公司工作期間復制的部分磁控管的產品設計圖紙、部分工裝夾具圖紙,按照與格蘭仕公司大致的工藝流程進行多次試驗,生產出磁控管并出售給A公司。截至劉某投案,B公司共生產磁控管400多萬只,獲得的利潤超2000萬元。
盡管該案發生在《修正案(十一)》頒布實施以前,但是就本案有關構成要件的諸種爭議而言,不僅涉及到何為“商業秘密”這一基礎問題,而且涉及公司前員工離職后是否存在保密義務、沒有簽署保密協議是否降低了行為人的保密義務等問題,其在法律適用上具有典型性。
二、基準:商業秘密“同一性”和“秘密性”的判斷
盡管《修正案(十一)》刪除了商業秘密的定義,但在實質的、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出臺之前,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商業秘密“同一性”和“秘密性”的判斷仍是判斷侵權行為是否成立的重要基準。“同一性”問題涉及到使用者權限的劃定,應在界定技術信息種類的基礎上,判斷是否具有實質的同一性,必要時進行利益衡量。例如,行為人憑借在先前公司所獲得能力的一部分在后來的公司中參與相同或類似技術的研發工作,在什么范圍之內,可以認為其在后來的公司所產生的智力成果與前公司的技術信息具有同一性。有些技術信息很難被固定,除了生產研發過程中嚴格控制的零部件圖紙之外,還包括對某種重要設備的生產制作方法。如果這種制作方法被公司技術人員掌握、熟知,經過改造,運用到后公司的生產作業中,優化了生產制作的方法,此時則需要衡量,這一行為應歸屬于行為人自身的特殊技能所延續的成果還是一種竊取商業秘密的行為,這就需要依技術信息的特質作具體判斷。
商業秘密所要求的“不為公眾所知悉”,是指“該信息不能從公開渠道直接獲取”[3]。“不為公眾所知悉”又被稱為“秘密性”,這是商業秘密屬性的核心要素。首先,應經過專門機構鑒定,認為被指控的圖紙等技術信息與權利人所擁有的技術信息具有“同一性”。其次,“秘密性”的認定受商業秘密權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的程度影響。“秘密性”要綜合考量客觀條件,審查該商業秘密的保密狀態。如果該技術信息缺乏保密性措施,應當審慎認定“秘密性”。最后,“秘密性”無需員工與權利人之間簽訂專屬的保密協議。根據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1998年修訂)和有關法律規定,權利人就商業秘密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的要求是“適當的”“合理的”,該合理和適當是指權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能夠使義務人明確知悉其有保密的義務,并不要求簽訂專屬的保密協議。
格蘭仕公司被侵犯商業秘密案中,被告人劉某作為格蘭仕公司磁控管部門的核心技術工作人員,利用工作便利,向外發送磁控管的相關生產可行性報告、成本分析等資料。經鑒定,在中山市B公司扣押的磁控管相關技術圖紙、實物和格蘭仕公司的不為公眾知悉的磁控管產品設計圖紙技術信息具有同一性。盡管被告人劉某和格蘭仕公司沒有簽訂保密協議,但是格蘭仕公司發布了《員工手冊》等一系列公司規章制度,要求全體員工對公司的技術等保密,可以認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三、定性: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認定
(一)非法獲取行為
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本質上侵犯了商業秘密的保密性,因此無論是行為人在獲取之后是否實際對其加以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保密性都受到了侵害,單純的非法獲取行為可以獨立成為一類侵權行為。[4]首先,應在有限范圍內承認非法獲取行為是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行為類型。例如,員工出于個人恩怨,竊取公司正在研發的資料并將其毀損,對公司未來的經營和發展可能造成實質的破壞。其次,非法獲取他人商業秘密進而毀損的行為,相比于泄露作為技術信息的商業秘密而言,對人類智力成果的毀損是終局性的,損失難以挽回。最后,對于嚴重侵害特定權利人的商業秘密,使其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明顯喪失,但是卻難以說明具有嚴重擾亂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的情節,可以以侵犯商業秘密罪未遂予以處罰,使得罪責刑相適應。
(二)合法獲取后的利用行為
行為人合法獲取商業秘密,之后加以利用的情形較為復雜,包括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等。對于合法獲取商業秘密者,其保密義務是法定義務,而非約定義務。在格蘭仕公司被侵犯商業秘密案中,前員工劉某雖未與格蘭仕公司簽訂保密協議,但不能認為員工離職后因不受公司規章制度制約而不具有保密義務,也不能因雙方沒有簽訂保密協議因而不屬于違約行為而否定行為人的保密義務。員工離職后,對原公司的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是一種法定義務,即便是合法獲取的商業秘密,對其非法使用的行為也完全符合本罪構成要件。
非法泄露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不限于為自己謀利的情形。單純的使用情形是指前員工沒有履行保密義務,使用行為導致其現公司生產經營利潤增加,但是尚未導致該商業秘密向其他市場競爭主體擴散。這種行為只是在同行競爭中,不當抬高了現公司的競爭優勢,同時使得前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競爭優勢。而合法獲取后的披露行為則不同,其本身可能并不是為了謀取利益,但卻是一種破壞性行為。例如,行為人將正在研發的作為技術信息的商業秘密,發布到網絡平臺使得商業秘密的研發價值落空,即便客觀上難以評估損失大小,也可以認為這種披露行為足以構成“情節嚴重”。
(三)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
刑法第219條第2款規定:“明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該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學界將此類行為稱為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在格蘭仕公司被侵犯商業秘密案中,中山市A公司的行為是否可被評價為間接侵犯商業秘密值得探討。對于間接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認定,主要在于確定明知的程度。《修正案(十一)》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應知”刪去,僅保留“明知”,說明對于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提高了主觀要素的標準。哪怕在“應知”保留之際也并不能將“應知”理解為應當知道。“應知”應屬于“實知”的范疇,不屬于刑事推定的問題。因此,即便不援用“從舊兼從輕原則”,適用《修正案(十一)》之前的條文,對于格蘭仕公司被侵犯商業秘密案,在沒有證據證明中山市B公司實際知道劉某違反了保密義務的要求,使用他人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不能認為B公司的投資者A公司符合“應知”的標準。
四、定量:侵犯商業秘密案件“情節嚴重”的認定
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保護法益是競爭性利益,而競爭優勢的直接效果就是帶來更多的財產性收益,因此,即使《修正案(十一)》刪除侵犯商業秘密罪中“重大損失”這一構成要件,即侵犯商業秘密罪由原來的結果犯修改為行為犯[5],“重大損失”依然是重要的判斷因素,對于“重大損失”的判斷依然是司法實務中不可避免的環節。根據2020年最高檢、公安部《關于修改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決定》(以下簡稱《立案標準決定》)中,仍然是將“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損失數額”作為重要標準。侵犯商業秘密罪以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作為背景,這決定了無法實施精確的損失數額計算。實際上,司法實踐早已突破“確定發生的實際損失”的限制,將各種推定的損失作為計算方法。[6]刑法不是民法,數額的計算是為了反映法益侵害程度,而不是為了合理地給予被害人損失賠償。因此,當犯罪行為使得被害企業完全喪失了對商業秘密的支配時,可以將商業秘密本身的價值作為損失數額。此外,商業秘密的權利人為減輕對商業運營、商業計劃的損失或者重新恢復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其他系統安全而支出的補救費用,應當計入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的損失。在認定補救成本時,要注意比例原則的適用。
除損失標準外,《立案標準決定》還將違法所得數額作為重要標準。但是,違法所得數額的計算也要考慮與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發揮主要作用時,可以將全部利潤數額認定為損失;起次要作用時,不宜將全部利潤計入重大損失”[7]。此外,《立案標準決定》規定,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不論是否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損失數額都可以根據該項商業秘密的合理許可使用費確定。
劉某作為格蘭仕公司的前員工,其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不屬于不正當手段獲取,由于行為人占有是合法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故造成的損失不以商業秘密的合理許可使用費或者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作為損失認定的依據。同時,權利人的產品非市場唯一廠家且不對外銷售,日本東芝、松下、韓國LG以及中國的美的等公司也占有微波爐磁控管的部分市場份額,因此在既無充分證據證明權利人產品的合理利潤,也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新東家產品的合理利潤的復雜情況下,屬于合理利潤無法確定的特殊情況,應結合在案的相關證據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選擇依據侵權人生產的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和實際數量,根據被害人產品的相對生產成本,得出侵權產品的相對合理利潤來推算本案格蘭仕公司因被侵權造成的經濟損失。司法機關根據格蘭仕外購磁控管的合理利潤和自制磁控管的成本、B公司從2018年到2020年被告人劉某投案自首期間具體銷售磁控管的情況,認定格蘭仕公司因被侵權造成銷售利潤的損失為2022.56145萬元,并據此認定被告人的行為已達“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情節。
在判斷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秩序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問題上,刑法當然應當基于自身承載的任務和條文的規范目的獨立判斷違法性的有無和大小,不完全受制于前置法的規定。但同時也要盡可能清晰地、類型化地把握“情節嚴重”的入罪門檻。格蘭仕公司被侵犯商業秘密案的理論研究價值更典型地體現在其反映了市場經濟時代,勞動者生存與發展的權利與企業市場公平競爭的權利之間的博弈。刑法既應當重視在市場秩序穩定和安全方面的刑事保護任務,又應當審慎地介入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內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合理范圍。
*本文為2021年度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侵犯商業秘密罪幾個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課題組負責人:徐彪,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三級高級檢察官[528000];課題組成員:李靜芝,湖南師范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碩士研究生[410006];李榮楠,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檢察院北滘檢察室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舒新軍,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檢察院北滘檢察室一級檢察官[528300];程伊喬,清華大學刑法學博士研究生[100084]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將侵犯商業秘密罪原規定中的“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特別嚴重后果”修改為“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刪除了拘役刑以及原第2款商業秘密的定義,將第1款第3項中的“違反約定”改為“違反保密義務”,并刪除了行為人“應知”他人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構成犯罪的規定,僅以“明知”這一主觀要素來限定入罪范圍。
[2] “密點”是指權利人主張的不同于公知技術或公知信息的,為本企業所獨有的,能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由企業采取了保護措施的技術信息或經營信息。
[3] 參見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1998年修訂)第2條規定。
[4] 參見李蘭英、高揚捷等著:《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08頁。
[5] 參見翁安娜:《侵犯商業秘密罪中“重大損失”的認定研究》,《 山東青年》2021年第5期。
[6] 參見劉科:《侵犯商業秘密罪刑事門檻的修改問題》,《法學雜志》2021年第6期。
[7] 王文靜:《論侵犯商業秘密罪中“重大損失”的認定原則》,《法學評論》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