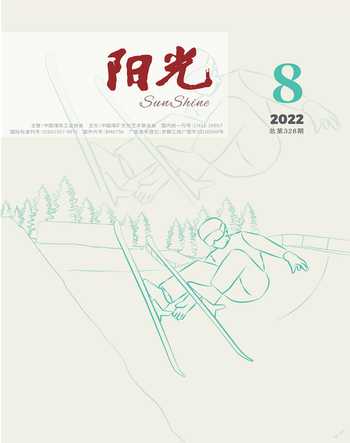母親的鄉愁
五月盛開的鮮花姹紫嫣紅,和風細雨伴著花香令人沉醉。母親對家鄉的無比思念陪伴我的童年、少年、青春,直至我長大成人。母親絮叨故鄉四季的山山水水,對故鄉的回憶令她眼中放出奇異的光芒,每一段、每一個人仿佛就是一部電影,循環往復地在她腦海里播放,兒女們聽倦了、聽膩了,可是母親依舊千萬遍地重復著,她對故鄉的思念永不褪色,日日夜夜地眷戀著故鄉。整日里圍著灶臺的母親現在連飯碗也端不起來了,兒女們在床前盡孝,一口飯一口湯地喂。人老了,不能動了,可她的思維還是清晰的,她仍然做著回歸故鄉的夢。
母親節來臨之際,為感念母親辛勤勞作大半輩子,兒女們孝心滿滿地“回家看看”:包攬家務活兒,讓母親捧一杯熱茶安心歇一會兒,讓母親吃上一頓熱騰騰滾鍋三鮮餡水餃,為母親置辦一件紅艷艷的毛衣,溫暖慈母心。這些事對兒女來說是再平常不過的,只要帶著一顆“孝順”之心即可滿足母親,令她有滿滿的幸福感。母親的偉大都是一樣的,平凡的母親千千萬萬。我的母親就是千萬平凡母親中最普通的一個,區別于溫婉的、賢靜的、知性的女子,我母親是尋常百姓中的農家女。她自小身體孱弱,嫁為軍嫂是她此生最驕傲的事。她大字不識,針線活兒不精,粗茶淡飯操持一大家子的家務,養育四個兒女,實屬不易。母親的幼年是在北京順義的兵荒馬亂中度過的。一次日本鬼子深夜掃蕩,周莊的男女老少紛紛逃出避禍。趕巧姥爺做木匠活兒在外地,小腳的姥姥懷抱著才兩個月的舅舅,四歲多點兒的母親緊緊地拽著姥姥的衣角,深更半夜往哪兒跑啊?跑不動了,實在沒法子,她們就躲藏進村口的棒子秸里,居然躲過了日本兵的刺刀!刺刀幾次穿過棒子秸在頭頂劃過,明晃晃的刺刀“唰唰”作響,幸而兩個孩子沒哭沒鬧躲過一劫,姥姥過后嚇出一場大病。這場驚嚇,令姥姥至死難忘。幸好那夜日本兵沒放火,不然即便躲過了日本兵的刺刀,也會被燒死在棒子秸里。真是撿回三條命啊!多年后,當母親捂住胸口說出當時的情景時仍令人感到頭皮發麻、驚恐不已。類似的苦難經歷多了,養成了母親時常坐在凳子上呆呆愣神的習慣。
一九六三年六月,父親抗美援朝歸國后,任濟南軍區第十一分部器材管理科科長?,母親遠離故鄉到山東成了隨軍家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成為她每日的全部。那時候,除了父親有成套的軍服,全家老小一年四季的衣、帽、鞋、褲,全靠母親一針一線縫制。難為母親在昏暗的燈光下手指戴頂針箍趕制衣服,為了逢年過節孩子們能喜氣洋洋、整整齊齊地穿上新衣服,她求人用報紙剪裁下衣樣、鞋樣,比葫蘆畫瓢地在布料上裁剪。夏做冬裝秋紡麻線,春天里坐在白楊樹下拿起錐子納鞋底,白雪茫茫的冬季正是熬糨糊做袼褙的好時節。衣服新舊好說,大的孩子穿小了小的孩子接著穿,無非補丁多了點兒。吃飯卻是頭等大事,半大小子能吃窮老子,況且還是一群孩子!一家人全靠父親一個人的收入養活,常常入不敷出,壓得雙親喘不過氣來。好在母親做飯是把好手,煎炒烹炸樣樣精,四季里瓜果蔬菜皆能腌制成可口的咸菜,熬出油渣包餃子,粗糧細做花卷烙餅蒸發糕,別人家扔了不要的菜葉子,洗干凈剁碎烙菜合子吃,冬季儲存蘿卜丟棄的蘿卜纓,成了她包大包子最好的食材。在母親的辛勞呵護下,我們這些孩子早已成家立業并成了有了孫子輩的人了,更懂得了“養兒方知父母恩”的道理。眼瞅著母親滿頭白發一天天老去,人不能自由行動了,躺在病床上還嚷嚷著:“開春了,咸菜該出缸晾曬了……”握住老人家的手,兒女們感慨母親一生操勞,臨老還在操心,惦記兒孫,惦記她的咸菜缸,惦記著故鄉。我們也在心頭流淚,父親的離世不敢告訴她,或許她是知道的,可母親就是不說,也不問。她常常陷入沉默,雙眼空空地直視著屋頂。
我們什么時候對母親的依戀轉變成了責任?是母親望著兒女們長大成人后的背影嗎?我們什么時候對故鄉的熟知轉變成了回歸的向往?是母親思鄉的淚水流入了兒女們的心田之后嗎?魂牽夢縈的故鄉是生我養我、給我血肉的母親一生的牽掛!五月是普天下母親的節日,故鄉梨花正放,眼前依稀似見花瓣雨染白了山崗,染白了我們的小村莊。母親坐在梨樹下,手搖紡車嗡嗡作響。梨花雨簌簌而下,隨風飛舞,落在母親的發間和衣服上,飄在紡車上,落在母親的腳下。
當我們經歷了春夏秋冬酷暑嚴寒的歷練之后,方懂得“寸草之心”。大地滋養萬物似母親用乳汁哺育著兒女,讓兒女無憂無慮地成長。我在感念母親的恩情之時,也感恩祖國的繁榮富強。在這美好的五月,愿普天下的母親健康幸福!
殷振鋒:中國煤礦作家協會理事,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薛城區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創作長篇小說《回程票》等。作品被清華大學、山東師范大學等大學圖書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