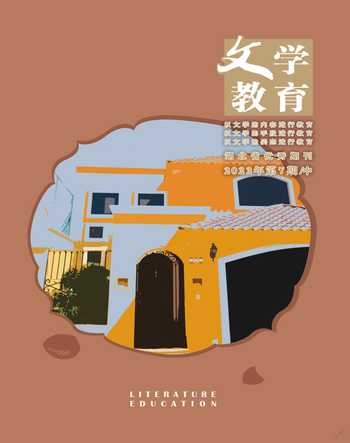試析馮夢(mèng)龍對(duì)“沈煉父子”故事的改寫
莊澤鑫 莊澤遠(yuǎn)
內(nèi)容摘要:馮夢(mèng)龍將《贈(zèng)光祿少卿沈公傳》和《沈小霞妾》兩個(gè)歷史文本匯編、改寫為歷史小說《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并收入《喻世明言》中。馮夢(mèng)龍的改寫體現(xiàn)了他重視文學(xué)的社會(huì)教化作用的文學(xué)觀與倡導(dǎo)男女真情的“情教”觀。從前文本到“三言”,“沈氏父子”故事經(jīng)由歷史敘事轉(zhuǎn)向文學(xué)敘事,故事人物不再是類型化的符號(hào),開始變得有血有肉,情節(jié)更具有曲折性、可讀性。考察這一轉(zhuǎn)變過程,可以分析出馮夢(mèng)龍對(duì)于歷史和歷史改寫的態(tài)度,以及分析他在寫作中如何平衡真實(shí)和虛構(gòu)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 馮夢(mèng)龍 歷史小說 改寫
《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是《喻世明言》中的一篇?dú)v史小說。它由兩個(gè)歷史故事匯編而成,一為沈煉的故事,一為沈煉之子沈小霞及沈小霞妾的故事,這兩個(gè)故事的前文本分別是徐渭的《贈(zèng)光祿少卿沈公傳》和江盈科在《皇明十六種小傳》中所編的《沈小霞妾》。
目前學(xué)界對(duì)于《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的研究相對(duì)較單一,大致可分為情節(jié)研究、人物形象研究和讀者期待研究。韓南的《中國白話小說史》和胡士瑩的《話本小說概論》在論及本篇時(shí)均認(rèn)為就情節(jié)而言,《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是“三言”中藝術(shù)成就較高的文本;[1]繆詠禾的《馮夢(mèng)龍和三言》聚焦于文本中的官吏形象,提出了應(yīng)將文本中的官吏分為上中下三級(jí);[2]郝煥東:《〈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與沈煉忠義形象的生成》則從讀者期待的角度分析了沈煉的形象在文本中如何建構(gòu)與生成。[3]總之,學(xué)界目前較少探析小說與前文本的關(guān)系,譚正璧的《三言二拍源流考》雖從源流學(xué)的角度討論了《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如何從不同的前文本演變而來,但沒有進(jìn)一步的分析。[4]因此,本文從“改寫”入手,探析馮夢(mèng)龍的改寫策略和改寫的意義。
一.沈煉故事:有意識(shí)地強(qiáng)化忠奸對(duì)立
比之徐渭《贈(zèng)光祿少卿沈公傳》平實(shí)的敘事,《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蘊(yùn)含了馮夢(mèng)龍揚(yáng)忠貶奸的價(jià)值判斷——入話、背景、故事細(xì)節(jié)均強(qiáng)化了忠奸對(duì)立的故事格局。
《贈(zèng)光祿少卿沈公傳》從沈煉考中進(jìn)士時(shí)講起,他歷任知縣、錦衣衛(wèi)經(jīng)歷,而后因嚴(yán)黨打壓而被流放邊疆,最終蒙冤而死。這是一篇標(biāo)準(zhǔn)的、較少摻雜作者主觀情感的傳記。在《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中,作者的主體意識(shí)則較為明顯地干預(yù)了敘述。比如入話詩“閑向書齋閱古今,偶逢奇事感人心。忠臣反受奸臣制,骯臟英雄淚滿襟。”[5]就直接點(diǎn)明了忠與奸的主題。在入話之后,馮夢(mèng)龍?jiān)鲅a(bǔ)了一段時(shí)事背景描寫,細(xì)致地指摘了嚴(yán)嵩和嚴(yán)世蕃的種種惡跡,令讀者側(cè)目。緊隨背景之后,又筆鋒一轉(zhuǎn),“只為嚴(yán)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gè)忠臣來”帶出故事主人公沈煉。接著又不厭其煩地描寫沈煉的日常生活,講述沈煉敬慕諸葛亮,常手抄《出師表》,“每逢酒后,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往往長(zhǎng)嘆數(shù)聲,大哭而罷。”[6]忠臣形象躍然紙上。沈煉還將嚴(yán)家比作曹操父子,諸葛亮與曹操父子的并置再一次強(qiáng)化了忠奸對(duì)立。在事件結(jié)尾,馮夢(mèng)龍一方面遵循事實(shí),寫了嚴(yán)黨倒臺(tái),嚴(yán)世蕃問斬,另一方面也增補(bǔ)了沈煉以及馮主事的結(jié)局,讓他們羽化登仙,與奸臣的結(jié)局形成對(duì)比,“忽一日,夢(mèng)見沈青霞來拜候道:‘上帝憐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為南京城隍,明日午時(shí)上任。”[7]
馮夢(mèng)龍的改編策略,應(yīng)置于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觀中來討論。馮夢(mèng)龍?jiān)凇缎咽篮阊詳ⅰ分姓劶埃按恕缎咽篮阊浴匪氖N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dǎo)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xí)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8]也即是說,馮夢(mèng)龍重視文學(xué)的社會(huì)教化作用,這一文學(xué)觀念上承儒家“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大夫文人希冀借文學(xué)“足以佐經(jīng)書史傳之窮”[9]。忠與奸的對(duì)立能教化讀者,令讀者知曉哪些人物、行為是可借鑒的,哪些應(yīng)持批判態(tài)度,以此達(dá)到《喻世明言》所謂“明者,取其可以導(dǎo)愚也”的目的。沈煉和馮主事的結(jié)局安排,也實(shí)現(xiàn)了因果皆有報(bào)應(yīng),行善立德的勸諭作用。
二.沈小霞故事:書寫男女之真情
在江盈科的《沈小霞妾》中,故事情節(jié)為沈煉三子皆被逮捕入獄,其中二兒子、三兒子被活活打死,只留沈小霞一人發(fā)配保安,其時(shí)嚴(yán)世蕃交代差役在路上結(jié)果沈小霞性命,而沈小霞亦知此事。令人訝異的是,沈小霞在情知此去危急的情況下,仍要求其妾同行,似又要白白搭上一人性命。在路途中,沈小霞自作主張安排了逃跑策略,卻棄其妾于不顧。總之,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沈小霞妾雖為題旨人物,但始終處于失語的狀態(tài),任由沈小霞安排自己的生死。這種敘述不僅無法體現(xiàn)“情俠”[10]的機(jī)智勇敢,更造成人物行為邏輯的混亂。
《沈小霞妾》固然只是野史,但面對(duì)這樣“失序”的前文本,馮夢(mèng)龍的改編勢(shì)在必行。從史學(xué)走向文學(xué),改編問題所觸及的是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問題。任何歷史都嵌套在一定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條件中,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歷史的發(fā)生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因此,把握歷史人物,突顯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合理性對(duì)于作者來說成為了一項(xiàng)重要的任務(wù)。“合理性”是指在歷史小說中,作者應(yīng)把握歷史事件內(nèi)在的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和歷史人物行為的內(nèi)在邏輯性。在中國傳統(tǒng)文論里,也有“事體情理”的說法,曹雪芹曾說:“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事體情理罷了……至若離合悲歡與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zhèn)髡摺!盵11]由此可見,古典文學(xué)亦遵從“事體情理”“追蹤躡跡”,注重把握住描寫對(duì)象的活動(dòng)軌跡、生命際遇和命運(yùn)的必然。
在《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中,馮夢(mèng)龍將沈小霞的故事修改為住在家鄉(xiāng)紹興的沈小霞接到官府通告,要押解他發(fā)配保安,一家老小頓時(shí)哀嚎不已,其妾挺身而出,要與沈小霞同行。路上,沈小霞妾發(fā)現(xiàn)差役有所企圖,她私下安排沈小霞逃跑,自己則留下來與差役周旋,最終上演了大鬧公堂的劇情。
這幾處改動(dòng)豐富了情節(jié),完善了人物的行為邏輯,在敘述上比之《沈小霞妾》易于讀者接受許多,成功勾勒出一位有勇有謀的“情俠”形象。
馮夢(mèng)龍對(duì)于沈小霞故事的改編策略與其文學(xué)觀、思想觀密不可分。馮夢(mèng)龍對(duì)于“情”推崇備至,甚至主張建立“情教”與佛教對(duì)抗,呼喚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同時(shí),馮夢(mèng)龍也強(qiáng)調(diào)故事的真實(shí)性,這里的“真實(shí)”不是指歷史真實(shí),而是如同他在《警世通言敘》中所論述的“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真者可以補(bǔ)金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yáng)勸誘、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贗,即事真而理亦真。”[12]換言之,馮夢(mèng)龍強(qiáng)調(diào)的“真”是讀來似真,即不摻雜虛浮之言與矯飾之情。“情”與“真”高度統(tǒng)一,“情”聯(lián)系萬物與人際關(guān)系,[13]而“真”又是“情”的第一要旨,因此唯有文章用情真方能讀來似真。在沈小霞的故事里,讀者可以讀到人物的無奈與不舍,讀到沈小霞妾挺身而出的勇氣,她不再是為沈小霞任意使用的工具,而具有了自主性,因而沈小霞妾的行為才能更好地打動(dòng)讀者,做到“情真”“理真”“事真”。
三.歷史小說的改寫:從歷史敘事到文學(xué)敘事
徐渭是明代的重要朝臣,由他所寫的《贈(zèng)光祿少卿沈公傳》被視為客觀的歷史敘述,而江盈科的《沈小霞妾》則被《四庫全書》歸入奇聞野史一類。從前文本到“三言”,馮夢(mèng)龍的改寫本質(zhì)上使“沈氏父子”故事由歷史敘事轉(zhuǎn)向文學(xué)敘事,故事不僅具有史學(xué)意義,還有了審美意義。因此,考察歷史小說的改寫意義,就是在追問采用具有藝術(shù)審美性的文學(xué)敘事之于歷史敘事的不同。
自19世紀(jì)末以來,實(shí)證主義不斷發(fā)展,西方史學(xué)科學(xué)化的傾向越發(fā)明顯,人們?cè)桨l(fā)嚴(yán)格地要求歷史編纂,幾乎將其視為科學(xué)。由此,真實(shí)成為歷史敘事的第一要義,這就是所謂“實(shí)證性歷史編纂”,它重視敘述的平實(shí),講數(shù)據(jù),要出處。實(shí)證性歷史編纂往往只關(guān)注事件的起因、經(jīng)過、結(jié)果,鮮少關(guān)注事件過程中的人物的心聲,其根本原因是記錄歷史的人無從知道他人內(nèi)心的真實(shí)想法,僅能揣摩當(dāng)事人的心理活動(dòng),但一旦介入記錄人主觀的揣測(cè)則必然影響歷史敘事的可靠程度,因此不關(guān)注或少關(guān)注人物的精神、心理狀態(tài)在實(shí)證派看來是記錄歷史的必要之義。
然而,歷史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并非真與不真這樣單向度。在實(shí)證性歷史編纂之前,西方傳統(tǒng)的歷史編纂是敘事性的,即“敘事性歷史編纂”,這種歷史敘事認(rèn)為修辭性乃敘事的根本,沒有任何形式的敘事可以完全擺脫文學(xué)性。關(guān)于歷史敘述的修辭性特征,海登·懷特認(rèn)為“即使是實(shí)證性的歷史編纂,也無法掩蓋其修辭性和文學(xué)性,盡管千余年以來它一直在極力擺脫自己與修辭性和文學(xué)性的干系。別的且不說,它是以日常經(jīng)驗(yàn)為基礎(chǔ)的書面話語,僅僅這一點(diǎn)就足以決定其特性——具有修辭性和文學(xué)性。”[14]
厘清歷史真實(shí)與文學(xué)敘事之間的關(guān)系,一方面是為了澄清歷史小說的尷尬,另一方面是借此看到馮夢(mèng)龍為原本枯燥粗糙的故事賦予了怎樣富有生命力的描述和代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物質(zhì)水平與精神風(fēng)貌的書寫——這些是歷史敘事難以惠及讀者的,也是“沈氏父子”故事被改寫的意義所在。
但反過來說,歷史小說畢竟受“歷史”二字的約束,這規(guī)定了作者在歷史小說中的虛構(gòu)的權(quán)力邊界以及承認(rèn)歷史優(yōu)先性的義務(wù)。恩格斯在《致費(fèi)迪南·拉薩爾》中曾討論過歷史劇的創(chuàng)作問題,恩格斯認(rèn)為拉薩爾有權(quán)將歷史上未曾發(fā)生過的事情按需要寫入文本中,但在揭示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因時(shí)則不可以主觀臆斷。套用回《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沈小霞及其妾一路上所發(fā)生的事情無第三者證明,歷史真實(shí)永遠(yuǎn)不可追溯了,此時(shí)作者有權(quán)通過想象、虛構(gòu)豐富他們一路上的故事,突顯出二人智謀與真情。但是,諸如嚴(yán)嵩陷害沈煉、嚴(yán)黨倒臺(tái)、嚴(yán)世蕃問斬等影響事件整體走向的重大歷史節(jié)點(diǎn)則不容虛構(gòu),要符合實(shí)際。從小說文本可以看出,馮夢(mèng)龍的改寫策略與恩格斯對(duì)于歷史劇、歷史小說的改寫的看法是不謀而合的。
但從另一個(gè)方面來說,歷史小說的本質(zhì)是小說,它是屬于文學(xué)藝術(shù)范疇而不是歷史范疇的、是需要提供給讀者以審美享受的存在,因此歷史小說要遵守“美學(xué)本位原則”。也就是說,歷史小說中的人物應(yīng)被賦予豐富的性格,舒展出人性的不同面向,人物不能只是冷冰冰的符號(hào),情節(jié)應(yīng)具有曲折性、可讀性。《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在遵循實(shí)有其人其事的前提下,不斷剖析人物性格,展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心獨(dú)白,增加忠邪之間你來我往的激烈斗爭(zhēng),使文本更具美學(xué)張力。
從《贈(zèng)光祿少卿沈公傳》和《沈小霞妾》到《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是歷史文本向文學(xué)文本的轉(zhuǎn)型。馮夢(mèng)龍的改寫一方面體現(xiàn)出他重視文學(xué)的社會(huì)教化作用與“情真”“理真”“事真”的文學(xué)觀、思想觀,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他對(duì)歷史小說的改寫態(tài)度,即兼顧歷史真實(shí)與文學(xué)審美性,而不是偏至任何一方。改寫歷史小說的意義則體現(xiàn)在文學(xué)對(duì)于史學(xué)的補(bǔ)充,文學(xué)敘事雖然受到基本歷史框架、重要?dú)v史節(jié)點(diǎn)的約束,但作家填補(bǔ)的細(xì)節(jié)使得人物變得有血有肉,情節(jié)曉暢可讀,更易于普通讀者接受。
參考文獻(xiàn)
[1][明]馮夢(mèng)龍.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7.
[2][明]馮夢(mèng)龍.情史類略[M].湖北:岳麓書社,1984.
[3][美]韓南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4]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
[5]繆詠禾.馮夢(mèng)龍和三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譚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譚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美]海登·懷特.元史學(xué):19世紀(jì)歐洲的歷史想象.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10]朱光潛.美學(xué)問題討論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注 釋
[1]韓南認(rèn)為“馮夢(mèng)龍的歷史小說中最好的是《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和《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兩篇。”見[美]韓南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頁。胡士瑩認(rèn)為“與話本相比,《三言》一部分的作品及其他專集中的少數(shù)或個(gè)別作品,繼承并發(fā)展了話本的好的傳統(tǒng),有的反映了市民的追求自由的意識(shí)和斗爭(zhēng)的精神,如《杜十娘》《沈小霞》等。”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463.
[2]繆詠禾認(rèn)為“這個(gè)故事刻劃了一群從上到下的反動(dòng)統(tǒng)治階級(jí)成員。上層的有嚴(yán)嵩父子這些當(dāng)朝權(quán)貴;中層的有路楷、楊順這批親信官吏;最下面一層則有張千、李萬這伙爪牙走卒。”見繆詠禾:《馮夢(mèng)龍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頁。
[3]郝煥東認(rèn)為“中國百姓歷來渴望有沈煉式的人物橫空出世,就如同他們渴望包拯,渴望海瑞。這些‘超人式的英雄嫉惡如仇,本領(lǐng)強(qiáng)大,更重要的是他們始終如一,毫不動(dòng)搖,以至于達(dá)到‘非人的狀態(tài)。”見郝煥東:《<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與沈煉忠義形象的生成》,《文學(xué)教育》,2018年第3期.
[4]譚正璧對(duì)《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與前文本的關(guān)系做了考察,“《沈小霞相會(huì)出師表》,演明嘉靖時(shí)沈煉父子事,出《古今小說》卷四十。文中所言皆實(shí)錄。煉性伉直,嘗于席上折嚴(yán)世蕃,因劾嚴(yán)嵩謫佃保安,縛草為人,像李林甫、秦檜、嚴(yán)嵩,令子弟射之。俺答入寇,破應(yīng)州四十余堡。嵩黨楊順反上首功。煉遺書切責(zé)之,且為文祭死事者。順與路楷因陷煉至死。并見《明史》煉傳(卷二百九)。錦衣衛(wèi)陸炳,驕貴而喜接士大夫,又素善煉。小說謂煉謫保安,由炳周全之力,殆亦事實(shí)。至沈襄妾聞氏,明江進(jìn)之曾為作傳,馮夢(mèng)龍《情史》四,《智囊補(bǔ)》閨智部,具載其事。唯煉友賈石,及濟(jì)寧馮主事事今無考。”見譚正璧:《三言二拍源流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218.
[5][6][7][明]馮夢(mèng)龍編,許政揚(yáng)校注:《喻世明言》,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605,606,634.
[8][明]馮夢(mèng)龍編,顧學(xué)頡校注:《醒世恒言》,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895.
[9][明]馮夢(mèng)龍:《古今小說序》,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c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27.
[10]江盈科將《沈小霞妾》收入《皇明十六種小傳》的“情俠類”.
[11][清]曹雪芹:《紅樓夢(mèng)》,華文出版社2019年版,3.
[12]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cè),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年版,231.
[13]馮夢(mèng)龍?jiān)凇肚槭沸颉分姓f“萬物如散線,一情為線索。散線就索穿,天涯成眷屬。”見[明]馮夢(mèng)龍:《情史類略》,岳麓書社1984年版,1.
[14][美]海登·懷特:《敘事與詩性的歷史》,《中國學(xué)術(shù)》,第17期。又見《元史學(xué):19世紀(jì)歐洲的歷史想象》,譯林出版社,2004年.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xué)中國語言文學(xué)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