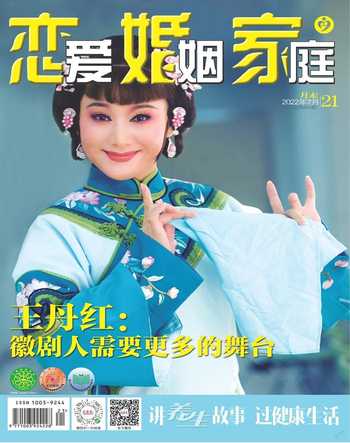愛到深處是簡單
潘彩霞
1930年,陳省身考入清華大學數學系攻讀研究生,數學系教授鄭桐蓀對他格外關注,他希望陳省身能做自己的乘龍快婿。鄭教授的女兒鄭士寧在東吳大學生物系就讀。好友楊武之(楊振寧之父)教授看出鄭桐蓀的心思,于是和夫人一起當起了媒人。其時,陳省身正準備出國留學,他承諾回國后再談終身大事。1937年,陳省身學成歸國,來到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建的長沙臨時大學任教。那一年,鄭士寧從東吳大學畢業,由師長們穿針引線,兩個年輕人訂婚了。
雖是父母之命,可對于愛情,鄭士寧一點也不盲目。亂世之下,陳省身一邊執教一邊宣傳抗日救國,這一腔愛國情、報國志對鄭士寧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西南聯大成立后,陳省身擔任理學院教授。1939年7月,兩人結為伉儷。這樣的情感,談不上浪漫,卻樸實真摯。許多年后,陳省身回憶說:“我們其實沒有談過戀愛,因為她父親要招女婿,覺得我不錯,可以做他女兒的丈夫。她也很聽父親的話,所以我們就結婚了。”
在西南聯大,因日寇不斷轟炸,經常居無定所。鄭士寧懷孕后,父親帶她回上海待產。那是1940年,夫婦倆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這一分別,就是6年。兒子出生后,鄭士寧準備返回昆明,不料,太平洋戰爭爆發,交通一度中斷,她被迫滯留上海。在西南聯大,陳省身無奈,只好過起單身生活。幸好,他的導師從國外寄來大量資料,他一面閉門研究,發表了大量論文,一面培養了眾多英才,其中就包括楊振寧。
因研究成果引起國際數學界矚目,1943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邀請陳省身去做訪問學者。世界陷入大戰,他無法去上海與妻兒告別。懷著內疚,以及對數學研究的癡迷和渴望,幾經輾轉,他終于到達美國。在大洋彼岸,陳省身潛心研究微分幾何,而鄭士寧在漫長艱辛的日子里,一邊在中學任教,一邊撫育幼子,望眼欲穿。


抗戰勝利后,陳省身回國效力。1946年,他終于和鄭士寧團聚。而此時,從未見過面的兒子,已經6歲了。委屈和艱難,她沒有訴說,對他只有理解和支持。擁著賢妻愛子,陳省身含淚許諾:“從今以后,一家人永不分離!”他沒有食言。1948年年底,普林斯頓大學再次發出邀請,本來只邀請陳省身一人,但他堅持全家一起去。直到對方解決了全家人的機票,他這才踏上赴美之路。
到美國后,陳省身先后在幾所大學任教。為了讓他安心研究,鄭士寧承擔了全部生活瑣事,小家庭寧靜而幸福。因為癡迷數學,陳省身腦子里時時都會迸發出新鮮奇妙的想法,每次開車外出,鄭士寧都會非常緊張,再三叮囑他注意安全。后來,她干脆親自接送他,這一接送就是幾十年。身為數學天才,對行政瑣事,陳省身沒有絲毫興趣。而鄭士寧,就是他的全權代表,應邀參加學術會議時,他只有一個要求,帶夫人同行。
身在他鄉,心系故土。每遇海外游子,鄭士寧都會熱情地邀請他們來家里做客。她善良又好客,還有一手好廚藝,舌尖上的溫暖慰藉了年輕學子思鄉的心。她的盛情,提升了陳省身的人品威望。陳省身邀請國內數學家到美國進修,為了省錢,就讓他們住在自己家里。鄭士寧仍是一貫的熱情,很多年后,華羅庚、丘成桐都對她的款待念念不忘。家庭瑣事,人際交往,她一一解決。沒有了后顧之憂,陳省身才能全身心投入研究,才有了“獨上高樓”的輝煌。
愛情,其實是一件簡單的事,無非琴瑟和諧甘苦與共,無非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就像一個好習慣,讓人愿意日日夜夜去重復它。鄭士寧60歲生日時,陳省身特地為她作詩一首:“三十六年共歡愁,無情光陰逼人來。摩天蹈海豈素志,養兒育女賴汝才。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遺井臼倍勞辛。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覺壺中日月長。”她數十年的默默奉獻,他都記在心里。1978年,在《我的科學生涯與著作梗概》中,陳省身深情寫道:“在結束本文前,我必須提及我的夫人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近40年來,無論是戰爭年代抑或和平時期,無論在順境抑或逆境中,我們相濡以沫,過著樸素而充實的生活,我在數學研究中取得之成就,實乃我倆共同努力之結晶。”他們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他們的人生契合無間。
1985年,南開數學所成立,這是為陳省身量身打造的,他捐錢捐書,精心撫育著這個“新生兒”。他決定回國定居,鄭士寧不顧自己患有心臟病,毫不猶豫陪伴身側。那時,她已是古稀之年。知道他淡泊名利,對官場的事最是頭疼,舉辦宴會怎么安排席位都是個難題。于是,她參加他的學術會,為他出謀劃策,先在紙條上編好號,然后親自站在門口發紙條,讓大家對號入座。
數學成就舉世聞名,一雙兒女事業有成,因為有鄭士寧,陳省身擁有了完美的人生。1999年,他們迎來結婚60周年紀念日。那天,他無比自豪地對朋友們說:“我們60年來沒吵過架,她管家,我不管,我就做我的數學,所以我們家里生活很簡單!”牽手一個甲子,他不能沒有她。在南開的居所,陳省身為其取名“寧園”。其一,他認為,做學問就應該有寧靜的心態;其二,“寧”字,飽含了他對她的綿綿深情。習慣了她的陪伴,他從來沒有想過她會先他而去,可噩耗還是來了。2000年,一次睡夢中,鄭士寧因心臟病發作悄然離世。陳省身悲痛萬分。幾經思考,他將她的骨灰安葬在南開數學所,其側留了一個空墓穴,那是他為自己準備的,生而同衾,死亦同穴。
鄭士寧去了,但她的大幅照片就掛在墻壁上,工作累了,陳省身就會抬頭看看她。他曾傷感地說:“很容易就想起了她。以前有什么東西找不到,我就對她說,你幫我找找,她很快就給找出來了。現在,找不著就是找不著啦!”為了緩解痛苦,陳省身投入緊張的研究中,以九旬高齡,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沒有了鄭士寧的監督,他忘我地研究“屬于年輕人的難題”,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他的衰老。
2004年12月,93歲壽辰剛過,他走了,神情安詳。遵他的遺愿,他與鄭士寧合葬南開園。他們的墓園設計成了露天教室,墓碑是黑板,碑前擺放著圓形石凳。一代代莘莘學子,跟隨他走進美妙的數學花園,也深深感受著他和她的簡單愛情。
摘自《做人與處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