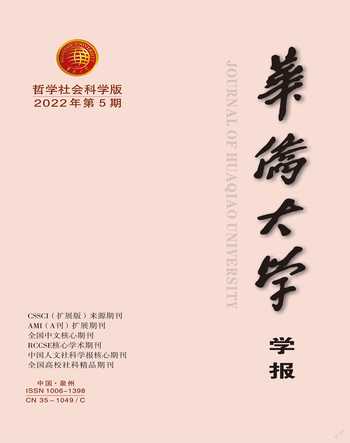沈從文新詩創作流變論
田文兵 張俊琦
摘要:20世紀20年代,沈從文自覺融入中國現代詩潮,從民間歌謠的搜集和整理開始現代新詩試驗,多維度地探索詩歌創作,為其文學創作走向成熟奠定基礎。沈從文與新月派詩人交往甚密,理論與創作上受新月派詩學影響頗深,沈從文的新詩創作具有較為明顯的新月派風格。20世紀30—40年代,沈從文詩歌創作藝術的積淀、文字運用能力的提升、詩學觀的成型,以及所處現實境遇的變化等,其詩風從具象抒情轉向抽象哲思;最終因沈從文對詩歌、小說的不同功能定位,及個人諸多因素的影響,其現代詩創作漸趨沉寂。盡管沈從文的現代詩歌的數量不及小說和散文,但其詩歌的獨特審美及其現實價值仍具有較重要的文學史價值。
關鍵詞:中國現代詩潮;沈從文;新體詩;新月派
作者簡介:田文兵,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E-mail:twenbing@ 126.com;福建泉州362021)。張俊琦,華僑大學文學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1207.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398(2022)05—0141—11
沈從文的小說、散文成就已然得到學界公認,但對其詩歌創作卻關注較少。實際上,沈從文的文學生涯始于詩歌創作:“四十年前,最初用筆寫作,表示個人情感和愿望,也是從作詩啟始的”①。盡管沈從文起初創作的是舊體詩,但他在五四思潮的感召下來到北平后開始白話新詩創作,在《京報·國語周刊》《晨報副刊·詩鐫》《新月》《現代評論》《大公報·文藝副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詩歌和詩論文章,在從事編輯工作時也身體力行地扶持和鼓勵青年詩人。即便沈從文后期從作家轉而專事文物研究,也從未放棄詩歌創作。為何在沈從文創作生涯中極其富有特色的詩歌沒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在詩歌創作和實踐上頗有心得的沈從文為何將文學創作重心轉向小說和散文?沈從文三四十年代發表的詩歌一反前期明白曉暢風格,詩風漸趨隱晦,是什么原因導致沈從文在詩歌創作的數量和風格上發生如此突兀的變化?如何準確評價沈從文現代時期的詩歌創作?本文將從沈從文詩歌與中國現代詩潮的交互、沈從文與新月派的關系,及其詩風轉變等方面考察和探討沈從文的新詩創作。
一呼應與探索:新文學語境與沈從文現代詩試驗
1920年代初,沈從文離開家鄉湘西,只身來到北平。這個時期正值現代新詩從“嘗試時期”進入“創作時期”,也是沈從文認為中國新詩成績最好的時期。②出于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向往以及現代新詩成就的認可,沈從文自覺地跟隨現代新詩潮流,在內容與形式上多維度地探索詩歌創作。
1926—1927年,沈從文陸續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筸人謠曲》和《筸人謠曲選》,這是他托家鄉表弟代為搜集的鎮算歌謠,經其整理并作了較詳盡的考證和注釋。為何沈從文的新詩創作會起始于民間歌謠?時代轉折期,新舊文化驟然斷裂,各文類均面臨破舊立新的問題。中國詩歌的發展道路該將如何?白話口語如何入詩?為打破舊體詩的語言束縛,探索新詩的表達方式,五四知識分子向民間尋求最樸質的情感表達,積極探索現代新詩的民族化路徑。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向全國征集歌謠,蔡元培發出《校長啟示》,邀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積極參與歌謠搜集運動,這一天成為“‘中國歌謠學運動的緣起日。”
①1920年10月26日《晨報副刊》開辟“歌謠”專欄刊載民間歌謠,“不但有詳細的注釋,還對一些方言詞匯進行注音、解釋,甚至進行了一些民俗學的考證。”②沈從文搜集整理湘西民間歌謠的同時,還創作一系列的民歌體詩,這源于他對當時歐化語充斥詩壇現狀的不滿:“至于最新的什么白話詩呢,那中間似乎又必須要加上‘云雀,夜鶯,安琪兒,接吻,摟抱才行。”③面對新詩創作因襲、虛浮的僵化風氣,沈從文決定要做一種新嘗試,“若是這嘗試還有一條小道可走,大家都來開拓一下,也許寂寞無味的文壇要熱鬧一點呢。”④沈從文之所以對歐化語持如此拒斥態度,一方面固然來自于五四新詩自身的缺陷,然從其心理層面考察,這源于詩人來到都市以后對“鄉下人”身份的強烈認同。
沈從文初到北京時,生活窮困潦倒,得到郁達夫、徐志摩等人的幫助,后來經林宰平托梁啟超致書熊希齡,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得到圖書管理員的職位。在《筸人謠曲》的“前文”中,作者從個人視角敘述了他搜集家鄉歌謠的起因。沈從文在香山感到寂寞、無聊,“長住下來,清閑得正如同做和尚模樣”⑤,故鄉的民間歌謠時時對他進行聲音招魂,沈從文不無眷戀地回望故鄉,又對此刻所處的都市發出暗諷:“我想起在我鄉下,這樣天氣,適當挖蕨折包谷的時節,工作的休息里正不知是給了若干年青男女們的娛樂的方便!在這里卻連借此來表示兩者希望的山歌也不能聞,很是可怪的事。要說這類人是沒有這種需要呢?我可不敢相信。”“也許是近于都市的人,都學到了在‘溫的接吻中應守著死樣的沉默吧,那可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⑥此外,他還諷刺都市教授對民間藝術認識的淺薄,與只會吹噓、喝彩的虛偽。沈從文將自己對都市與鄉村的態度寫入《算人謠曲》的“前文”中以作說明,足可見其介紹鎮算歌謠的另一重用心,那便是把這些真誠而不矯飾的歌謠介紹到都市中來。沈從文以歌謠作為媒介,目的在于呈現并向都市中人傳播湘西這種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男女大膽真誠的熱烈情意,以作為對都市虛偽風氣的抵拒,引起都市文化場域內讀者的關注與反思。
《鄉間的夏》是沈從文所作的第一首民歌體詩,是他對新詩創作方向的一次開拓性嘗試。詩歌首節便以都市的夏與鄉村的夏作對比開頭,彰顯他對鄉村的懷戀與親近,這可側面窺探其創作的心理動機,詩中對鄉間自然風景與人事場景的描摹多運用方言詞句,《鎮筸的歌》更進一步展示出民間語言的譏誚幽默,成為沈從文民歌體詩的鮮明特征。根據作者于詩后所附的“話后之話”中,可以得知這種“新鮮、俏皮、真實”的語言風格與貼近生活、自然樸質的詩意傳達在當時詩壇別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又如沈從文以鎮筸土音改寫《詩經》中的《伐檀》而成的《伐檀章今譯》,《伐檀》中勞動者對剝削者的諷刺和對現實不公的控訴,在沈從文的改寫下顯得更加真實平易,增添了一分幽默感:“秧不插,田不耕,哪那撿得這禾線三百根?”詩人以通俗樸實的農家口語諷刺剝削者好吃懶做的習性和生活方式,重章疊句的句式加強了諷刺效果。沈從文親身證明了那些為舊文人鄙夷的民歌俗語一樣可以表達嚴肅主題,甚至效果可以更生動、更有力。詩人不只是單就語言進行創新,還在形式方面尋求變革,在《還愿—擬楚辭之一》中描繪出家鄉酬儺神時的祭祀場面,是騷體與格律體形式的結合體,各節對稱,每句由11音節5音步組成,句末押韻,各節換韻,形式嚴謹,句式均齊,沈從文將騷體與格律體融合為一,體現其在新詩領域的開拓創新精神。沈從文的民歌體詩中,愛情題材最為豐富動人,包括其搜集整理的《算人謠曲》和《筸人謠曲選》也多屬情歌,主題涉及男女對唱歌、誘戰歌、單歌、自詠歌、男女分手時節唱的歌等多個方面,呈現出豐富的湘西情歌地理圖景。《春》是沈從文自己創作的一首男女對歌長詩。詩中既有沈從文對湘西原始歌謠的直接引用,又有他在原始歌謠基礎上融入白話的分解改造,同時又在唱詞中運用比喻的修辭手法,體現出詩人豐富的藝術創造。
如果說最初沈從文積極響應歌謠運動是為了掌握并運用白話文來表情達意,那么經由時間沉淀,其白話語言功底已比之前大有進步,他不再依賴方言土語彰顯地方特色,而是把民間元素自然融入現代語言文字的使用中,進而連綴詩篇。《黃昏》作為沈從文1932年創作的一首苗族男女分手時對唱的民歌體詩,已無生僻字眼,整體詩風更加清新自然。沈從文對于民間歌謠的搜集整理與創作是其自覺融入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一種方式。初入文壇的民歌經驗對沈從文個人也影響深遠,鍛煉了其對白話工具的熟練運用,為其文學創作確立自身特色、走向成熟奠定基礎。沈從文借民間歌謠書寫湘西優美、健康、自然、真誠的生命形式,一定程度上對都市男女異化的情感和虛偽的社會風氣起反撥作用。
民間歌謠為沈從文進入新詩創作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體式,而五四時期的現實主義詩潮是其創作大量現實題材詩作的思想資源。1922年,文學研究會創立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新詩專刊《詩》,將胡適等五四新詩開拓者所提倡的“寫實主義”①創作方法進一步深化,形成詩歌中的為“人生派”,直面現實的黑暗與殘酷,他們同情底層人民被壓迫與剝削的處境,以詩鼓動人民奮起反抗。沈從文仍在家鄉之際,便想要以詩來表達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在《我怎么就寫起小說來》中表示他厭惡部隊吸食鴉片、秩序混亂的環境,但是由于“年齡又還不成熟到能夠顯明諷刺詛咒所處社會環境中,十分可惡可怕的殘忍、腐敗、墮落、愚蠢的人和事,生活情況更不能正面觸及眼面前一堆實際問題。”“寫詩主要可說,只是處理個人一種青年朦朧期待發展的混亂感情。常覺得大家這么過日子下去,究竟為的是什么?實在難于理解。難道辛亥革命就是這么的革下去?”②沈從文自身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慮,與五四時期的現實主義詩潮遙相呼應,創作出眾多現實題材詩作,如《舊約集句—引經據典談時事》由《圣經》中的章句組合而成,目的在于抨擊北京女師大風潮中的教育界人士,抨擊教育制度的腐朽,贊揚學生的愛國行為;《失路的小羔羊》以兒童視角、獨白體形式,對人與人之間隔膜、虛偽的交往關系發出質疑與反思;《到墳墓去》中,詩人把假革命者和湊熱鬧的看客比作“蛆蟲”加以諷刺,表達他對五卅慘案的悲憤之情;《到墳墓的路》《余燼》則以“小詩體”形式,諷刺人性的虛偽、諂媚、與趨炎附勢等問題,希望生命可以回歸自然、真實與純粹。
與此同時,順應了五四狂飆突進時代精神的浪漫主義詩風,尤其是注重個性解放與表現自我,與沈從文的內傾型性格產生化合反應,激勵著他勇敢向內挖掘、表達自我,如《希望》《悔》《愛》等對情愛的向往與對自我個性的歌頌,“我將用詛咒代替了我的謙卑,詛咒中世界一切皆成丑老!我將披發赤足而狂歌,放棹乎沅湘覓紉佩之香草”。五四時期破舊立新、向往自由與光明的情感呼之欲出,不乏郭沫若《女神》般大膽而狂放的色彩。然而,“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如一對孿生姐妹,相親相近,尤其在‘五四落潮以后更為明顯”①。沈從文出于對國家前途命運的迷惘與自身的情感壓抑,也難免陷入到這種感傷主義的窠臼當中,如《春月》既未脫舊體詩詞的痕跡,情感上又帶有一種無名的悲哀;《痕跡》反復重復“石上的淡淡悲哀痕跡泯滅了”一句,使得全詩呈現出一股濃烈的感傷色彩;《其人其夜》更是陷入一種顧影自憐、自哀自嘆的消極情緒之中,似為情而傷,情感較無節制。除此之外,沈從文還受到1920年代中期的象征主義詩潮影響,如《囚人》:“報時大鐘,染遍了朋友之痛苦與哀愁,/使心戰栗,如寒夜之荒雞,/捉回既忘之夢。”詩歌在歐化句式、節奏韻律上與李金發《棄婦》有相似之處,模仿跡象明顯。
然而,沈從文與中國現代詩潮的呼應并非是其隨波逐流的表現,而是“情緒的體操”,是一種“扭曲文字試驗它的韌性,重摔文字試驗它的硬性”②的體操,最終目標指向于學習借鑒,在大量試筆的基礎上不斷提升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與文學創作水平,以更好地表情達意,形成獨具特色的詩學理念與新詩作品。
二詩藝與詩意的交融:沈從文新月派詩人身份的探討
沈從文的京派文人身份成為學界共識,但其與新月派的關系存在較大的爭議。劃分作家的派別歸屬,主要由其創作所展示出來的特點來判斷,作家的交往以及接受的影響也是重要依據。“盡管作家寫作時并不想到他要當什么派,但他的審美趣味、他的文藝觀點、他過去接觸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影響,無形中還是會支配著他,使他寫出可能接近于這派或那派的作品。”③沈從文新詩創作(包括民歌體詩)大致有50余首,近半數都發表在新月派刊物《晨報副刊》或《新月》上。詩論方面,沈從文在《職業與事業》《致灼人先生二函》等文中均鼓勵青年多向徐志摩、聞一多、朱湘、陳夢家等新月派詩人學習,可見沈從文與新月派關系之密切。
1925年,沈從文與林宰平等新月派詩人相識,在《談朗誦詩》中,作者自述林宰平介紹他認識徐志摩的場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天真純厚才氣橫溢作家時,是在北平松樹胡同新月社的院子里,他就很有興致當著客人面前讀他的新作。”④沈從文于《回憶徐志摩先生》中更表示“和他第一次見面,就聽到他天真爛漫自得其樂,為我朗誦他在夜里寫的兩首新詩開始,就同一個多年熟人一樣”⑤,直陳“年紀最輕,幫助最多,理解最深,應數徐志摩先生。”⑥徐志摩在主編《晨報副刊》期間,大量刊載沈從文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使得初登文壇的沈從文能夠以寫作賺取稿費、維持生計。此外,沈從文于1930年相繼在中國公學與武漢大學任教,主要講授以新詩發展為內容的新文學課程,其講義中多數是對徐志摩、聞一多、朱湘這些新月派詩人詩歌的講述與贊賞。可見,作者從初入文壇,到1930年代成名之期,都與新月社緊密聯系在一起。
徐志摩對沈從文的發現與提攜可謂影響了其一生的命運軌跡,在《習作選集代序》中,他對胡適、林宰平、郁達夫等人對他的鼓勵與幫助表示感謝,尤為感激徐志摩,表示“沒有他,我這時節也許照《自傳》上說到的那兩條路選了較方便的一條。”①沈從文從徐志摩那里“接了一個火”,告訴讀者“你得到的溫暖原是他的”②,認為紀念徐志摩唯一的方法,便是“應當擴大我們個人的人格,對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③沈從文何來如此感受?首先,徐志摩對世界“寬容”與“愛”的品質影響著沈從文的行為方式,沈從文對后輩多有提攜,力所能及地幫助、扶持青年的文學事業,并為他們提供創作指導與發表渠道。其次,徐志摩的文章對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理念影響頗深,“第一次見到徐志摩先生,是我讀過他不少散文,覺得給我嶄新深刻動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開始學習用筆時。就不知道不覺受到一種鼓舞,以為文章必須這么寫。”④徐志摩執著地追尋“從性靈深處來的詩句”⑤,“在詩里真誠地表現內心深處真實的情感與獨特的個性,并外射于客觀物象,追求主、客體內在神韻及外在形態之間的契合”⑥,而這也正是沈從文于詩歌中所要追尋的藝術境界。如《頌》以一系列客觀物象表達詩人內心對愛的贊頌與渴求,在視覺與嗅覺上將情人之于他的感覺以自然意象化之,尤其是最后一節:“你是一株柳;有風時是動,無風時是動:但在大風搖你撼你一陣過后,你再也不能動了。我思量永遠是風,是你的風。”其中疊詞疊句的運用,使音節自然和諧,將情人比作“柳”,將“我”比作“風”,風與柳永遠相知相伴,表達出詩人對愛人的脈脈情意,整首詩歌與徐志摩的詩風極為相似。
沈從文在西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教授“各體文習作”課程時,作《從徐志摩的作品學習“抒情”》一文,認為“徐志摩作品給我們感覺是‘動,文字的動,情感的動,活潑而輕盈”⑦,他的文字“清而新,能凝眸動靜光色,寫下來即令人得到一種柔美印象。”⑧沈從文的不少詩歌受到了徐志摩“飛動飄逸”“自然清新”詩風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愛情詩《悔》:生著氣樣匆匆的走了,這是我的過錯吧。旗桿上的旗幟,為風激動;飏于天空,那是風的過錯。只請你原諒這風并不是有意!文字輕巧靈動,天真活潑,自然清新,具有青春的活力。徐志摩認為,“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⑨徐志摩的詩歌總是在自由的形式中尋求內在的法度,而綜觀沈從文的新詩,大多也都是不受嚴謹格律所縛,自由中帶有法度、自然流淌詩意的詩作。于是,陳夢家在《新月詩選·序言》中這樣評論沈從文的新詩:“我希望讀者看過了格律謹嚴的詩以后,對此另具一風格近于散文句法的詩,細細賞玩它精巧的想象。”⑩顯然,在詩歌形式方面,沈從文更認可徐志摩的觀點,雖講求格律但卻少刻意雕琢的痕跡,而是致力于追求詩藝與詩意的自然渾融。
新月詩派主張“本質的醇正”與“格律的謹嚴”的詩風,而最能直觀反映沈從文受其新詩格律化理論影響的詩作是《夢》,這是他對聞一多所提出的詩歌“三美”理論的直接實踐:
我夢到手足殘缺是具尸骸,
不知是何人將我如此謀害!
人把我用粗麻繩子吊著頂,
掛到株老桑樹上搖搖蕩蕩。
仰面向天我臉是藍灰顏色,
口鼻流白汁又流紫黑污血;
巖鷹啄我的背膊見了筋骨,
垂涎的野狗向我假裝啼哭。
全詩共分為兩節,每節四行,形式嚴整,句式整齊,具有建筑美;每句由11音節5音步組成,句末押韻,2句一換韻,具有音樂美;“藍灰顏色”“紫黑污血”,具有繪畫美。詩作以“夢”為題,夢中是一個頹廢腐敗的世界,這個灰暗的夢象征著沈從文對現實的認知,人與人之間相互殘殺、利用,“我”備受黑暗現實的摧殘,小人橫行于世,整個世界呈現出一片絕望、頹敗、殘酷的畫面。這首詩創作于1926年4月8日,也可以理解為沈從文對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慘案”的憤懣回應,滿含作者的愛國主義之情。受新月派影響,沈從文開始在詩歌創作中有意識地講求韻律形式規范,尋求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詩藝與詩意的融合,進而生發出自我特色,形成其個性詩風—“象征性”“泥土氣息”與“湘楚風味”。
《“狒狒”的悲哀》全詩共8節,每節4行,形式嚴整均齊,句末押韻,兩句一換韻,作者以狒狒的經歷象征詩人對民族健壯的渴望,富有新意。《云曲》全詩共2節,各節對稱,化用楚詞體,形式上具有湘楚地域特色,詩中通過對“云”自然形態的書寫,象征詩人心中的理想生命狀態,“愛月而不遮月,近山而不倚山”有與舒婷《致橡樹》相似的情感價值導向,即對自由獨立之人格的倡導,沈從文在古典與現代雙重形式的化用中,運用自然意象,賦予其現代象征義,極具創新性。此外,沈從文善于以平白樸實的語言意象表情達意,在《一首詩的討論》中,認為現代抒情詩應當“充滿土氣息,泥滋味”,“對農村原有的素樸和平具有深刻誠摯的愛”①,這種詩觀可謂貫穿其創作始終,是其新詩最鮮明的特征。如《月光下》全詩共8節,每節4行,各節基本對稱,句末押韻,兩句一換韻,以“水車”“豬”“老梟”“田坎”“蛙”“村砦”“狗”“蚱蜢”“鸕鶿”等田園意象連綴詩篇,引用原始歌謠,具有鄉間泥土氣息。月光象征希望,“我”追逐月光便象征詩人對希望和理想之境的追求與對心中理想信念的堅守。《薄暮》分兩節,各節對稱,句末基本押韻,以自然意象書寫苗鄉薄暮場景。詩人將薄暮的天空比作農家“綢子”,將月亮比作農家剪紙剪成的“亮圓”(苗語月),蘊含地方色彩。《覷一瞟》具有湘楚大地孕育下的浪漫主義氣息,詩分4節,各節基本對稱,交錯押韻,各節換韻,形式嚴整而富于變化。詩人對情人的眼睛進行特寫,“莫讓星兒獨擅其狡猾,汝亦有此閃忽不定之聰明。荷面上水珠不可捉拿,你眼睛比那事物更活更靈!”詩歌同樣以以自然意象作比,表現情人雙眼的光亮、潤澤與神氣,詩人淪陷在情人的眼神當中,在對視中二人兩心相知。最后一節,沈從文運用通感手法,將這“覷一瞟”的眼神魅力比作“音樂魔力”和“檸檬汁鮮味”,化虛為實,富有新意與感染力。
新月派“戴著鐐銬跳舞”的格律倡導不只影響著沈從文同時期的詩歌創作,甚至影響了他20世紀30—40年代的詩學觀,其詩論文章多次強調語言形式與韻律節奏的重要性,如沈從文在《新詩的舊賬—并介紹詩刊》強調“新詩在辭藻形式上不可偏廢”①,詩歌韻律、辭藻、形式有其存在價值;在《談朗誦詩》中認為,即便是朗誦詩,其文字處理也不可極端自由,否則將會無從朗誦,認為真正便于朗誦的,是詩形“‘帶了些腳鐐手梏的。如徐志摩、聞一多、朱湘”②等人的作品;在《致今是先生》中強調“詩應當是一種比較精選的語言文字,在有限制的方式上加以處理的藝術”③;在《談現代詩》中更是直接夸贊新月派詩人“把格律提出作為欣賞的尺標”④可以作為一個共通標準,以建立起讀者與詩人之間有效聯結。
從詩歌本體觀出發,新月派除了對新詩格律化運動的倡導,還提倡“理性節制情感”的詩學主張,反對情感的無節制流露,這一觀點也影響了沈從文的詩歌創作理念,他在《給一個寫詩的》中強調寫詩“應當極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熱情”⑤,不能把寫詩當成一種“感情排泄的痛快。”⑥新月派對此的實踐方式之一便是進行新詩的小說化、戲劇化,沈從文《叛兵》《“狒狒”的悲哀》《曙》《絮絮》等詩作是他學習新月派新詩戲劇化理論的自覺嘗試。
新詩戲劇旁白體,如《叛兵》描繪出一幅行刑場面,人物涉及法官、被行刑的少年、觀眾、劊子手;同時融入場面描寫,黃土坡的凄涼、悲壯的歌聲、群眾的和鳴、病葉的零落;再加上戲劇表演中的唱和詞,營造出一派悲壯的行刑畫面,表現出沈從文對蕓蕓眾生的悲憫;又如《“狒狒”的悲哀》將戲劇化與格律化融為一體,全詩共分8節,每節4句,句末基本押韻,兩句一換韻。這首詩透過對狒狒心理的描寫,表達詩人對民族擺脫贏弱、重新健壯起來的渴望。新詩戲劇獨白體,如《曙》運用男子第一人稱的獨白形式,諷刺都市現代紳士小姐因金錢利益的需要而結合的虛偽,贊美妓女的純粹與真誠;又如《瘋婦之歌》,以第一人稱“我”諷刺“小姐、奶奶和太太”等貴族家庭天生就擁有特權,對社會的不平等現狀發出強烈控訴,在“我”的反諷中彰顯作者的情感傾向;《絮絮》則運用女子第一人稱獨白體的形式,“我”是妓女身份,對男子吐露自己身不由己的娼妓生涯、生不如死的生命狀態,和對真誠愛戀的渴望,極力表現妓女的善良。正是因為對上海文人“寫‘性史、無病呻吟、槍炮加女人之類作品的不屑”⑦,沈從文以一位渴望愛情的妓女入詩,用詩歌來諷刺都市上層社會的不平等以及都市男女虛偽情愛,開啟其以自然生命狀態審視現代都市病的鄉土敘事先聲。
沈從文的新詩創作得到徐志摩、陳夢家等新月派詩人的肯定,陳夢家于1931年出版的《新月詩選》中收錄沈從文新詩多達7首,數量上僅次于徐志摩,排名第二,超越聞一多、朱湘等被歷史所公認的新月派詩人。陳夢家評論沈從文詩歌“極近于法蘭西的風趣,樸質無華的辭藻寫出最動人的情調。”“所惜他許多寫苗人的情歌,一時無法盡量搜尋,是我最大的遺憾。”⑧由此可見,即便沈從文的新月派詩人身份頗有爭議,但毫無疑義的是,沈從文的詩歌創作藝術已具有較高水平,在1930年代的中國詩壇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位置。
三歷史振蕩與心靈沉潛:沈從文詩歌沉寂與詩風轉變
1930年代以后,沈從文僅有十余首新詩發表,數量與20年代相比大幅減少。其由何自?其一,沈從文的詩歌創作理念無法滿足中國當時的抗日救亡需求。隨著抗日戰爭的打響,民族救亡運動高漲,詩歌的政治宣傳功用被無限放大,新詩標語化盛行。然而,沈從文卻對詩歌的這一發展趨向持警醒態度,在《談朗誦詩》中否定了當前多是以革命為題材的口號詩做法。其二,1920年代的中國正處于白話新詩的探索階段,五四先驅者們積極探尋新詩的表達與形式規范,詩學理論層出不窮,加之沈從文自身對詩歌的興趣,共同推動著作者學習與創作的欲望。1930年代后,新詩創作規范漸趨成熟,但沈從文卻對自己的詩歌寫作并無信心,內含一種自卑心理,他在1931年11月13日致徐志摩的信中說:“你怎么告陳夢家去選我那些詩?我不想作詩人,也不能作詩人,如今一來,倒有點難為情。一看到《詩選》我十分害羞。”①沈從文大多只是將詩歌作為個人的興趣愛好,并非是其文學事業的重心所在。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沈從文的小說、散文創作也進入成熟期,《邊城》《湘行散記》《從文自傳》等作品的成功給他的文學之路帶來信心,作家成名后大多也會將重心放在帶給他聲名的體裁上,因此詩歌創作漸趨沉寂。另外,沈從文既擔任大學老師,又主編《益世報·文學周刊》《大公報·星期文藝》等刊物,忙碌蕪雜的事務也是其詩歌創作數量驟減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沈從文對于詩歌與小說的不同功能定位,成為他這一時期將精力放在小說而非詩歌的主要因素。沈從文于1931年發表的《窄而霉閑話》反映了作者這一時期的文學觀念。沈從文反對當時文壇迎合商業的做法,指責那些“玩”文學,將文學當作“玩具”的人,反對“白相文學的態度”②。因此,他提倡“文學的功利主義”,“這功利指的是可以使我們軟弱的變成健康,壞的變好,不美的變美”③,即著眼于文學對民族品德建設的有益方面,認為這較之那些“在朦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還有些功利的好處。”④同時作者表示,這種“注重文學的功利主義,卻并不混合到商人市儈賺錢蝕本的糾紛里去”⑤的希望,應由“創作小說來實現”⑥,“事實上這里的責任,詩人原是不大適宜于擔任的。一個唯美詩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個進步的詩人,能使用簡單的字,畫出一些欲望的輪廓,也就很費事了。”⑦詩歌難以有效地表達出自己的“事功”想法,小說才可以擔任這個角色。聯系1930年代沈從文的個人活動,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不再僅僅局限于埋頭創作,而是發表大量議論文章,如1932年在《上海作家》一文中提倡一種新的人生觀,“力避衰弱無力的牢騷,小巧無聊的雜感,以及那種上海趣味最壞的一種造謠風氣。”“應當獎勵征求能使國民性增加強悍結實的一切文學作品。”⑧1933年發表《文學者的態度》告誡作者要“誠實”的去做,不造謠、不說謊,不投機取巧。1934年憑《論海派》一文更是挑起了“京派”與“海派”的論爭,痛斥海派文學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的結合,是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代表。較之1920年代,沈從文對文壇局勢關心更甚,隨著作者社會責任感日益趨重,詩歌這種更著重于抒發心靈之聲的體裁便被沈從文置于邊緣位置。
然而,創作數量的降低并不代表詩人創作才氣的枯竭,經過沉淀,沈從文的詩藝更趨圓熟,詩風經歷了由明白曉暢的具象抒情到形而上的抽象哲思的變化,其背后有多重因素影響。首先,沈從文1920年代的詩歌創作便已初具象征意味,1930年代,他對象征手法的應用更加嫻熟,意象與象征義之間的聯系不再明晰,意義趨于抽象。其次,沈從文語言文字運用能力的提升與詩學觀的成型影響著其詩風變化。1929年沈從文在中國公學的教書經歷成為其語言文字進步的重要階段,“學習過程中有個比較成熟期,也是這個時候。寫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識有計劃結合,從這時方啟始。”①整體而言,沈從文20世紀30—40年代的詩歌語言更趨精煉雋永。另一方面,沈從文在中國公學教授新文學課程的經歷,促進了他對新詩理論的總結與認識,獨立詩學觀的成型是影響他詩風變遷的重要一環。1930年代初,沈從文在《給一個寫詩的》中,提醒詩人在語言上要組織,勸誡他莫要“隨便”寫詩,“應當節制精力,蓄養銳氣,謹慎認真的寫”②,1940年代在《談現代詩》《致今是先生》等文章中更是反復強調同一觀點,“詩其所以成為詩,必出于精選的語言,作經濟有效的處理”③,要“以約見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釋并表現發生較深較持久的效果”④,由此反觀其1920年代的部分詩歌創作,便會發現其用詞用語的野性和自由無拘,與詩歌感情的坦白、直露。如果說,沈從文1920年代的詩歌創作,其試驗與探索的成分更多,那么1930年代以后,他便是在其已然成熟的詩學觀指引下進行的藝術創造。
沈從文所處的現實境遇與歷史環境也是影響其詩風變遷的重要因素。1930年代,國家局勢動蕩,戰爭的殘酷與現實的挫折把他引向對人類命運、生命意義等問題的形而上思索。如《北京》,詩人對人類的生存狀態作形而上思考。恢弘壯闊的北京城背后,是千萬勞動人民“血與淚”般的生存。詩人對上層階級與底層人民的生活作對比,關心平民的生存狀態,“誰派王回回作羊屠戶,/居庸關每年跑進五十萬肥羊,/給市民添一分暖和,添一分腥?”這份思索貫穿古今,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甫隔空對話,體現出沈從文的現實關懷。但這首詩已與其1920年代創作的現實諷刺詩不同,時空意識更為博大,抽象意味初顯。《時與空》中,詩人借愛在四季的孕育、滋長、成熟與枯萎,表達美不可追逝的迷惘,正如詩題:“—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時間自然流逝,不受人為控制,詩人表露出一種虛無主義心境:“思量從虛無證實自己生命存在”,題目中的“空”不是指代“空間”,而是意為“虛空”“虛無”,時間的虛無意味著人存在的無意義,人的存在就是虛無的,而與此詩僅相隔12天所作的《憂郁的欣賞》更可見詩人的消極情緒,海鷗雖最終總是面臨被海水吞噬的結局,但它卻永遠會不離開大海,“憂郁和它一樣/從不會由我心上挪開。/一千個日子里,/憂郁的殘骸沉積在我的心上”,正如海鷗與海的永恒相伴,憂郁與詩人也是連體共生。
進入1940年代,沈從文詩歌的抽象性更進一步,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當時身處西南聯大,受校園內現代主義詩風環境的熏染,然內在因素是,這一時期,沈從文屢屢受到文壇攻擊,作者時常陷入自我懷疑與自我解剖之中。幾乎從1935年前后,沈從文的“關注中心從個人的文學事業擴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學的命運和前途,更推至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和前途。”⑤幾年間,沈從文大量抒發自己對文學、文壇、政治的看法,如《論讀經》反對國家倒退的愚行;《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反對文學趨從于政治的文學創作傾向;在《一般或特殊》中提出自己的文藝觀,卻被文壇評為“與抗戰無關論”。沈從文越挫越勇,繼續發表《文運的重建》和《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等文,反對文學的商品化和政治化。沈從文盡管屢屢被攻擊、污蔑、批判所包圍,但他對文學獨立性的堅持卻未曾改變,固執抒發著他的文藝見解。盡管沈從文深知自己的文藝觀在舉國抗戰的背景中大都無法被認可,但他為何仍要固執發聲?從其《蓮花》中可窺見一二,沈從文不愿像豬耳蓮一般沉默,“我也應當沉默?/不,我想呼喊,想大聲呼號。我在愛中,我需要愛。”他想要大聲呼號,希望自己的呼號可以得到時人的認可。然而,詩人也知這只是妄念而已,“火熄了,剩一堆灰。/妄念和幻想消失時/并灰燼也無剩余。”詩人借蓮自剖心境后,又陷入絕望之中。《看虹》一詩有與之相似的意蘊傳達,思維的復雜化與線團化與中國新詩派的詩風趨近,這首詩運用對白體的形式,以“希望”的生成、破碎三重回旋結構組合詩篇。“希望”的象征物不斷變化,虹上有夢,然而夢掉落;“我”索要星子照亮荊棘的路,卻被對話者拒絕;“我”需要“一點孤單,一點靜,在靜中生長,一點狠”,然而“我”又自我否定,“又像什么都不需要,因為/有一片坪蕪在眼中青”,再次否定了希望存在的可能性。詩人在對希望的肯定/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之間糾結、徘徊,表現出沈從文對希望存在的渴望,與對希望只是一種幻夢的現實認知的絕望。
1940年代初,沈從文已漸漸墮入消沉與虛無,而經由周遭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精神危機在1949年達致頂點。1948年,馮乃超在《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中,將沈從文的文章視為“今天中國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也是最反動的文藝。”①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視為“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的“桃紅色”作家。”②北大校園甚至出現學生用大字報轉抄的《斥反動文藝》,教學樓掛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③的大幅標語,學生的背叛使沈從文的精神徹底陷入紊亂當中,“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④沈從文自覺不被新政權接納,作品也將被全部否定,這對其是致命打擊。《樂章》中的三首詩反映了沈從文這一時期的精神狀態:從《第二樂章—第三樂章》中“我在搜尋喪失了的我”的迷茫、孤獨與憤怒,到《從悲多汾樂曲所得》中,在音樂的幫助下正常理性得以回復,心“很真實貼近了地面”的個體,再到《黃昏與午夜》中經由生命回溯而生發積極生活渴望,作者終于確立了自己生命得以存在的支點,那便是在“融群”中為祖國散發生命的余熱。沈從文在對個體存在的反思中確立起未來的人生走向,“我”逐漸讓位于“群”,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在最后一首新詩《黃昏與午夜》后也進入停滯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研究工作當中。沈從文1930年代以后的詩歌創作可以看作其心靈之聲的私語,對于了解其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變化軌跡有無法替代的參考價值,是考察沈從文后半生事業轉向的重要研究材料。
四結語
當然,沈從文的新詩創作并非是對中國現代詩潮的亦步亦趨,也不僅僅只是一種“情緒的體操”而已,而是在于探索新詩表達方式,尋求形式與內容的融洽,以更好地表情達意。沈從文1920年代基于鄉土倫理背景的寫作方式,與五四時期基于人道主義和啟蒙姿態的現代詩人的美學觀點相比別具一格。在以啟蒙為創作旨歸的時代,詩人極力贊美鄉村的民風民俗,以妓女入詩描寫其內心獨白的新詩創作實踐獨具特色。沈從文與新月派中人交往甚密,在詩學觀與詩歌創作上受其影響頗深,在形式的規范中自然融有其個性特征,成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之一。20世紀30—40年代,在詩學觀的成熟、歷史環境的變遷、語言駕馭能力的提高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沈從文詩風轉向抽象,詩歌創作漸趨沉寂。但沈從文所發表的大量詩論文章,以歷史的、發展的、比較的眼光考察新詩發展演變,在評價詩人風格的同時表達自己的詩學理念,對中國新詩發展起到較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其主編《大公報·星期文藝》期間,發表了中國新詩派成員的作品多達40余篇,可見其獨具慧眼。正如沈從文對詩的理解“詩應當是一種情緒和思想的綜合,一種出于思想情緒重鑄重范原則的表現。容許大而對宇宙人生重作解釋,小而對個人哀樂留個記號,外物大小不一,價值不一,而于詩則為一。”①沈從文的詩歌及其詩學理論是研究其小說和散文的對舉互證、互為補充的材料,也為探討沈從文創作美學觀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種研究視角和重要參考,然而各類現代文學史論著卻忽視了沈從文的詩人身份,其詩歌成就也仍處于被遮蔽狀態,顯然難以全面認識和評價沈從文的文學史價值。
On the Shen Congwen's Poetry
TIAN Wen-bin,ZHANG Jun-qi
Abstract:In the 20s,Shen Congwen consciously integrated into the tid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started his poem writ- ing from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folk songs,explored poem creation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his literary creation going to mature. Shen Congwen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escent school poets,and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poetics of the Crescent school. So his poems were written with an obvious Crescent School styl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40s,ShenCongwen'spoetie style changed from conerete lyricism to abstract philosophy d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is poetic creation art, the improvement of his ability to use words,the formation of poetieview,and the changes in his realistie circumstances. Finally his modem poetry creation gradually became silent because of his different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poetry and novels and his own personal factors.Although the number of Shen Congwen's modem poems is less than that of novels and essays,the unique aesthet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his poems still have important liter- ary history value.
Keywords:modern Chinese poetry;ShenCongwen;new style poetry;Crescent School
【責任編輯:陳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