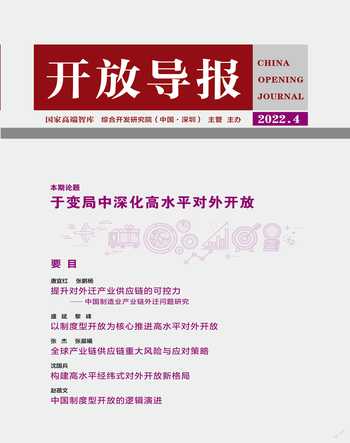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推進策略
[摘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追求以及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的,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階段性進展。然而,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高質量發展短板凸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較低、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居于高位、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有待完善,以及數字鴻溝和信息障礙帶來沖擊等方面。建議以“做大蛋糕”“做實蛋糕”“做優蛋糕”和“分好蛋糕”為主線,同時要特別關注農村低收入人口等重點群體和數字經濟等關鍵領域的共同富裕。
[關鍵詞] 共同富裕? ?分配制度? ?低收入人口? ?數字經濟
[中圖分類號] F124.7?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4-6623(2022)04-0069-08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歷史性跨越: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21FJYB053)。
[作者簡介] 高強,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村政策分析、土地制度等。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崇高社會理想,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我國如期完成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任務,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為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指出,“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標志著我們黨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2021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并將2035年遠景目標確定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和國家反復強調“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并做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邁入新時代,必須進一步深化對共同富裕核心要義的認識,夯實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分析把握面臨的主要挑戰,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義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馬克思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維度對共同富裕的本質特征進行了闡釋。一方面,發達的生產力和豐富的物質財富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馬克思指出,“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實際前提,是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作為“兩極分化”的對立面出現,具有歷史漸進性,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歷史發展規律。根據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科學構想,漸進性和階段性是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特征。“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商品經濟下的貧富日益懸殊,最終將導致整個社會陷入崩潰。作為“兩極分化”對立面的共同富裕成為未來社會最根本的發展目標,資本主義社會終將被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所替代。
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讓人人享有平等分配社會財富的權利,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毛澤東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脫貧致富問題,認為只有堅持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黨的十三大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現象日益突出。針對這一情況,江澤民強調,“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黨的十五大以后,我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胡錦濤基于當時的基本國情,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社會主義建設全局來認識共同富裕,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論水平,并將共同富裕思想和實踐融入國家建設和發展之中。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堅持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帶領全體人民向著美好幸福生活不斷奮進。
(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追求
共同富裕指向的是通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升全體人民福祉。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天然的內在聯系。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只是為了簡單地追求物的最大化,還要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只有人民的主體地位、主體意愿和主體利益都得到充分滿足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具有真實的進步意義。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堅持以人為先、以人為重的理念,明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兩個階段的奮斗目標,并旗幟鮮明地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
在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推進共同富裕面臨的一個緊迫且艱巨的任務就是實現現代化。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不僅包括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還包括人的思想觀念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多方面內容。理論和實踐也已證明,我國追求的現代化是造福人民的現代化,而且無論何種現代化,它的目標指向都是人民美好生活。黨和國家在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后,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將共同富裕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豐富了共同富裕思想,也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涵。
(三)共同富裕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目的
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也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高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首先表現在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高于資本主義社會”。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歷程中,毛澤東第一次將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聯系起來,指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具有極端重要性。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以農村作為突破口實行改革開放,推動農業農村經濟快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更堅定的決心、更有力的舉措,不斷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進展。
進入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內在要求與重點方向呈現出新的變化和特點。在向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70多年間,我國高度重視生產力發展,較好地扭轉了物質生產落后的局面,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得到較好的滿足。邁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生產力發展更加重視質量。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黨和國家將更加關注人民對高品質生活的期盼,以高質量發展破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以高水平生產力滿足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筑牢我國由富到強的生產力基礎。
二、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礎。中國共產黨是實現和維護人民利益的先進政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最根本保證。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著眼于國家發展與治理的宏觀視野,堅持把制度建設貫穿黨的各項建設之中,不斷完善黨內法規建設,全面提高管黨治黨能力。從《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到《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以及黨章的歷次修訂,無不體現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忘初心、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人民群眾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不畏艱難、歷經挫折,為國家和人民的事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贏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偉大勝利,開辟了一條能夠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勇于在實踐中革新自己,不斷增強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動蕩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突發事件,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從容應對。
(二)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實現共同富裕確立了基本路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經歷了從產生、發展到不斷完善的過程。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以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確立了將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新時代國情出發,將現階段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根本上保證了財富的社會性。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地兼顧了效率與公平,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如在農村領域,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家庭基本經營制度,順應了農業農村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是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性選擇,也是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遵循多勞多得的勞動邏輯,強調保護和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并高度重視再分配、三次分配的作用,從而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慈善事業等方式構筑起共同富裕的保障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政府作用與市場作用的有機結合,這將極大提高社會財富的創造能力,推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邁上新的臺階 。
(三)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
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繼承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也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重要體現,為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價值遵循。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契合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是財富創造的主體力量,以及創造財富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人的幸福”的財富觀,有利于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黨和國家始終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這一主線,堅持將增進人民福祉、提升人民幸福感作為執政使命,通過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在經濟社會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促進共同建設、共同勞動、共享成果,推動物質積累、精神創造和社會進步,堅定人民對于實現共同富裕的信心。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必須繼續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通過共建共治共享來實現和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四)堅持優化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社會保障作為長期性的制度安排,根植于經濟社會之中。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和維護社會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進入新時代,我國相繼出臺多項政策措施優化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人民的基本生活權利得到更加全面、更高質量的保障。《“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并對社會保險制度、社會救助體系、關愛服務體系等社會保障關鍵領域進行系統部署,彰顯了黨和國家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決心。從歷史經驗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其調解收入分配的效果將更加明顯,推進共同富裕的作用也更加顯著。邁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新征程,必須將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作為重要任務,優化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方式、價值功能和實施效益。總之,要把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切實發揮社會保障制度的再分配作用及其在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積極功能。
(五)堅持推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
生態文明作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態度和倫理追求,是實現人類共同富裕的價值旨歸。一方面,人類作為能動主體,在社會生產活動中認識和改造自然,以實現自身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人類是自然的產物,自然是人類肉體和“精神”的最終歸宿。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點領域,是推進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變革的重要著力點。黨和國家將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千方百計為廣大人民群眾創造優美的生態環境,充分體現了黨對人民福祉與民族未來的高度關切。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必須處理好與自然生態條件相關的人民發展權益問題,把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共同擁有、互惠共享與公平分配作為全社會的根本性原則,加快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推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
三、新時代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挑戰
(一)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
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和貿易復蘇乏力,國際治理體系和大國競爭格局調整加快,國際產業鏈、供應鏈脆弱性增加,我國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增多,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在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以及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全球經濟“低增長、高債務、不穩定”現象愈發明顯。近幾年來,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條件和供需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經濟潛在增速逐步回落,經濟運行面臨持續下行壓力。202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0976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約為12500美元,接近世界銀行2021年7月最新發布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95美元)。然而,即便我國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若要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目標,年均經濟增長必須保持在6%左右。從短期來看,我國經濟正面對多年未見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等多重壓力,維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短板凸顯
新發展階段,經濟高速增長下的供需平衡關系被打破,社會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傳統的數量型、粗放式發展已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根據“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應當是具備創新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開放性以及共享性的發展。雖然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質量水平總體呈上升態勢,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創新性仍顯不足,協調性仍是突出短板,共享性仍需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廣大中西部地區,協調性水平長期偏低,開放性水平提升緩慢,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雖然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推動下,我國科技創新生態正在逐漸形成,但仍然存在研發結構不合理,科研人員密度低且分配不均等問題,部分核心技術仍然被先進國家“卡脖子”,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中低端產業。同時,供給側質量和效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如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大氣、水、土壤污染和重要生態涵養區功能退化,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等問題突出。此外,我國要素市場化改革尚未全面完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運行機制不健全,資源配置效率偏低,這些均已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短板。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較低
著力解決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使所有居民能夠享受到充足的、在內容和質量上大體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目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還存在明顯差距。總體而言,地方政府財力不足是造成部分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公共服務低效或缺位的重要原因。中國式財政分權和政府職能異化,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發展經濟,弱化了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需求不斷增長,呈現出多層次、多樣化和高質量等特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面臨“新矛盾”“新結構”“新技術”和“新冠疫情”等諸多挑戰。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和農村空心化等問題,客觀上要求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數量、供給結構和供給質量作出調整;新興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觀念、行為模式和社會參與方式,對基本公共服務模式創新、業態創新和服務創新提出了新需求;新冠疫情等公共突發事件則進一步考驗了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和治理水平。
(四)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居于高位
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務。當前,我國部分地區和部分群體已經相當富裕,但先富帶動后富的機制不健全,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縮小比較緩慢,絕對差距仍在進一步擴大。首先是城鄉差距,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農村居民為18931元。從相對差距上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5倍,這一數值僅比2020年降低了0.06;從絕對差距上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高28481元,這一數值比2020年增加了1778元。其次是地區差距,主要表現為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收入差距明顯。如2021年上海和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78027元和75002元,而貴州和甘肅分別僅為23996元和22066元,后者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此外,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不容忽視。2020年數據顯示,前20%的高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8520元,而后20%的低收入農村居民僅為4681元,前者是后者的8.2倍。值得注意的是,我國90%的低收入人口分布在農村,因而農村低收入人口應當成為推進共同富裕的重點關注群體 。
(五)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有待完善
從現實情況看,我國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機制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初次分配的市場化機制不完善,再分配的稅收體系、轉移支付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對收入的調節能力不足,公益和慈善事業等三次分配能力還不夠高。初次分配方面,雖然我國市場化建設總體上已取得較大進展,但資源要素市場發育滯后,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以及財產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較低。勞動力市場嚴重分割,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也存在明顯的壟斷和扭曲。再分配制度方面,首先,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能力有限,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工薪稅”,對于不以工薪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高收入人群來說,該稅種顯得無關緊要。其次,間接稅占政府財政收入比重較高,但間接稅的性質決定了其具有擴大收入差距的功能。此外,盡管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低收入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但轉移支付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起到的作用較小,而社保繳費的累退性反而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擴大。三次分配機制方面,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等實施機制不健全,制約了社會力量在推進共同富裕中作用的充分發揮。
(六)數字鴻溝與信息障礙帶來沖擊
我國正處于數字化轉型不可逆轉的時代。作為一種新型社會不平等形式的數字鴻溝,對共同富裕的挑戰與沖擊需要引起重視。數字要素的獲取和使用具有一定的門檻,技術壁壘和市場壟斷可能對數字領域的共同富裕造成阻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若沒有政府的干預,數字經濟將造成“信息富人”和“信息窮人”的分化,并誘致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經步入快車道。數字經濟在政府治理、民生服務、生產技術等方面帶來數字紅利的同時,也在部分低技能、低收入和老年人等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形成一道數字鴻溝,這一鴻溝正成為擴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潛在因素。以數字普惠金融為例,已有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鎮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顯著大于農村居民,對東部地區居民的收入提升效果顯著大于中西部地區居民,這一現象值得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截至2021年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3%,但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僅為57.6%,比城鎮地區低23.7個百分點。同時,60歲以上網民群體占網民總體不到7%。數字鴻溝在老年人、農村居民、偏遠地區居民,以及低收入者等弱勢群體中廣泛存在,他們難以分享數字技術發展的紅利,成為數字時代新的貧困者,給實現共同富裕帶來了新的挑戰 。
四、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推進策略
(一)做大“蛋糕”:挖掘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無論是從大國博弈的角度看,還是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角度來看,增長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依托和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這個優勢條件,為“做大蛋糕”提供穩定、持續的內源性動力。從宏觀層面看,多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和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國內市場特別是消費需求持續擴大,為我國國民經濟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增長空間。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日益成為我國穩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因此,必須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實施有效的需求管理,提高供給側活力,增強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在增速換擋中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要加快培育完善內需體系,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環節的堵點,促進商品生產與國民需求有機銜接,促進國內大循環。特別地,要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持續深耕農村這一潛在市場,著力促進農村消費擴容提質。加強農村現代物流體系建設,完善現代倉儲設施布局,改善農村道路狀況,優化配送網絡,增加農村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以高水平供給滿足農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優化各類所有制企業投資環境,發掘農村投資需求,合理擴大農村有效投資。
(二)做實“蛋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過程,其內含“做實蛋糕”的發展要求。因此,必須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矛盾運動規律,適應需求結構變化新趨勢,促進高質量發展。要把新發展理念完整、準確、全面地貫穿到發展全過程,將“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消費拉動”、“加快速度”轉向“提高質量”,不斷推動發展的質量效率變革、目標動力變革和方式路徑變革。完善創新驅動的政策環境,支持協同創新,加強融資支持,降低創新成本,加快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和高質量發展中的核心地位,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因地制宜、分類別分層次突破發展瓶頸,前瞻布局把握未來主動權。要在發展中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在碳達峰、碳中和框架下引導新舊產業和新舊技術接續轉換,推進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空間格局。
(三)做優“蛋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要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讓人人都能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健全中央統籌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運行機制,構建責任清晰、各負其責、執行有力的領導體制,做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供給規劃、政策體系和考核機制的銜接。兼顧經濟發展趨勢和各級政府財政實力,深化基本公共服務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在厘清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權責范圍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央地財政共擔的資金籌措機制。改變自上而下的運動式治理策略,創新協同治理機制,更好地發揮政府、社會、市場、公民等多元主體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作用。優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加大農村教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健全鄉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統籌鄉村醫療衛生人才培養和縣域醫共體建設;健全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統籌城鄉公共文化設施布局、服務提供和隊伍建設。最后,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跟蹤問效,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供給內容、供給質量和實施成效進行全過程監督。
(四)分好“蛋糕”:改革創新收入分配制度
科學的收入分配機制不僅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還有利于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要依托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優勢地位,不斷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調節秩序。在初次分配領域,加快生產要素市場化步伐,讓生產要素市場不僅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決定性作用,而且在決定要素回報方面起到更多的作用。在再分配領域,改革的重點是加大稅收和轉移支付調節力度。在稅收結構方面,逐步提高直接稅在稅收中的比重,不斷降低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間接稅比重。同時,繼續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讓個人所得稅能夠覆蓋那些收入主要不是來自工薪的高收入人群,起到調節“過高收入”的作用。此外,改革社保繳費制度,促進社保繳費從累退性向累進性轉變,降低低收入人群繳納的社保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從而縮小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在三次分配方面,健全社會公益事業發展機制,出臺鼓勵性政策,創造有利于社會組織和慈善事業發展的政策環境,讓人人愿意做公益,富人樂意做慈善,從而提高三次分配的收入調節能力。
(五)重點群體:促進農村低收入人口增收
考慮到我國90%的低收入人口分布在農村的現實情況,促進農村低收入人口這一重點群體持續增收對于實現共同富裕至關重要。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抓手,補齊“三農”領域發展短板,建立穩定增收機制,挖掘農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潛力。首先,著眼于提高經營性收入,建立惠及低收入群體的鄉村產業體系。創新鄉村產業模式和業態,著力提高農業效益和附加值,健全低收入人口產業參與機制和利益聯結機制。其次,著眼于提高工資性收入,穩定低收入群體就業。強化就業幫扶和人力資本建設,建立覆蓋低收入人口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體系,通過發展富民產業,提高欠發達地區就業容量。再次,著眼于提高財產性收入,深化農村改革。統籌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和“三塊地”改革,探索盤活閑置宅基地的多種實現形式,鼓勵低收入人口以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林權等入股經營主體,加快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此外,要著眼于穩定轉移性收入,建立更有利于低收入人口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最低生活補助資金保障力度,提高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標準,健全分層分類的救助制度,盡量滿足差異化的救助需求,強化對困難群體的保障能力。
(六)關鍵領域:重視數字領域的共同富裕
加快推進數字經濟建設是順應全球發展變革的必然要求。隨著我國逐步進入數字時代,數字經濟必將成為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在實際操作中,應加快制定和出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實現數字普惠的政策。在政策設計上要盡可能揚長避短,規避數字鴻溝可能帶來的沖擊,努力放大數字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積極作用。推進數字教育平等化,縮小城鄉數字教育差距,促進人力資本公平發展。大力開展數字技能專業培訓,重點對農民開展信息技術專項輔導,增強勞動力稟賦結構與數字技術的匹配度。擴大數字基礎設施覆蓋面,特別是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完善農村信息基礎設施,消弭城鄉數據壁壘,提高農民數字素養,提高農村家庭數字工具的可及性。積極引導高新技術企業參與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民間商業資本,形成多元化的融資體系,減輕地方政府壓力。規范數字經濟監管,拓展數字產業鏈,以數字化改革提升公共服務質效,以數字賦能推動政策集成化、精準化。
[參考文獻]
[1] 陳新.馬克思主義財富觀下的共同富裕:現實圖景及實踐路徑——兼論對福利政治的超越[J].浙江社會科學,2021(8):4-10+156.
[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邱海平.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與實現途徑[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7(4):21-26.
[4] 范從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J].經濟研究,2017,52(5):23-25.
[5] 汪盛玉.公平正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12):48-51.
[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9] 劉欣,黃軻.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的科學指南——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2(1):32-40.
[10] 劉培林,錢滔,黃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內涵、實現路徑與測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11] 逄錦聚.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協同推進共同富裕[J].政治經濟學評論,2022,13(1):3-13.
[12] 張峰.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新的莊嚴承諾[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2):6-14.
[13] 逄錦聚.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為共同富裕百年奮斗的理論與實踐[J].經濟學動態,2021(5):8-16.
[14] 趙學清.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探討[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4):52-56.
[1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謝小飛,吳家華.中國共產黨追求共同富裕的百年歷程與啟示[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42(7):53-58.
[17] 范從來.益貧式增長與中國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J].經濟研究,2017,52(12):14-16.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22] 程恩富,劉偉.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論解讀與實踐剖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6):41-47+159.
[23] 王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的邏輯進路[J].經濟問題,2021(8):25-35.
[24] 何文炯,潘旭華.基于共同富裕的社會保障制度深化改革[J].江淮論壇,2021(3):133-140.
[25] 潘玲霞.“共同富裕”與“成果共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民生思想[J].社會主義研究,2009(1):40-43.
[26] 羅明忠.共同富裕:理論脈絡、主要難題及現實路徑[J].求索,2022(1):143-151.
[27] 李實.共同富裕的目標和實現路徑選擇[J].經濟研究,2021,56(11):4-13.
[28] 李舟,陳翊旻,劉渝琳.“中國之治”視角下高質量發展的多維表現[J].改革,2022(2):88-100.
[29] 李實,楊一心.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行動邏輯與路徑選擇[J].中國工業經濟,2022(2):27-41.
[30] 張帆,吳俊培,龔旻.財政不平衡與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0(12):28-42.
[31] 楊曉軍,陳浩.中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區域差異及收斂性[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37(12):127-145.
[32] 葉興慶,殷浩棟.促進農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政策取向[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3(1):1-8.
[33] 高強,曾恒源.中國農村低收入人口衡量標準、規模估算及思考建議[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2(4):92-102.
[34] 李實.以收入分配制度創新推進共同富裕[J].經濟評論,2022(1):3-12.
[35] 李實,朱夢冰.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進共同富裕實現[J].管理世界,2022,38(1):52-61+76+62.
[36] 王若磊.完整準確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內涵與要求[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6):88-93.
[37] 陳宗勝,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及其經濟學解釋[J].經濟研究,2001(4):14-23+94.
[38] 聶海峰,岳希明.間接稅歸宿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影響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3,12(1):287-312.
[39] 岳希明,張斌,徐靜.中國稅制的收入分配效應測度[J].中國社會科學,2014(6):96-117+208.
[40] 蔣永穆,何媛.扎實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時代要求、難點挑戰和路徑安排[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11):4-12.
[41] 張勛,萬廣華,吳海濤.縮小數字鴻溝:中國特色數字金融發展[J].中國社會科學,2021(8):35-51+205.
[42] 楊偉明,粟麟,王明偉.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居民收入——基于經濟增長與創業行為的中介效應分析[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0,22(4):83-94.
[43] 夏杰長,劉誠.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徑與政策設計[J].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42(9):3-13.
[44] 高強,曾恒源,殷婧鈺.新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動力機制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6):101-110.
The Promotion Strategy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Gao Q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the unswerving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d by Marxis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dhere to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to achieve staged progress. However,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greater pressure on economic growth, the prominent shortcoming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low level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high income gap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need to adjus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Improvement,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formation barri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while focusing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key groups such as the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 and key areas such as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istribution System; Low-income Popul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收稿日期:2022-06-30? 責任編輯:羅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