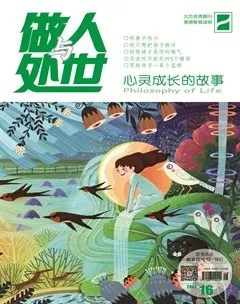靜味
劉萬祥
我學會了拒絕熱鬧
高僧佛印與蘇軾相交莫逆。一日,蘇軾要請佛印吃“半魯”,佛印不知道是何物,到了才知道“半魯”是魚,蘇軾得意地哈哈大笑。第二天,佛印也請蘇東坡享受“半魯”,蘇東坡高興地來到佛印處,卻被晾在院子里,曬半天太陽。蘇軾頗為生氣,看著靜坐的佛印,質問道:“魚在哪里?”佛印說:“‘半魯是日,就是請你來曬太陽的。”蘇軾聽完恍然大悟,才明白佛印的智慧。佛印與蘇軾像這樣的往復之語繁多,他之所以被蘇軾視為知己,不僅僅因為智慧高深,還因為其常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能于“鬧”中覓得趣味,得“靜”之真諦。蘇軾屢次被貶,早已被俗事傷得遍體鱗傷,正是佛印的平靜之心,撫慰了蘇軾的創傷,也讓蘇軾在動蕩中,明白清靜自然、曠達于世的道理。
其實,世間變化皆在于心,心若不靜,哪怕是身處空靈悠逸的環境,也難免浮躁。而真正的靜,從來不是要避開車馬喧囂,而是內心的靜水流深,波瀾不興。
莊子說:“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心若流水,雖波光瀲滟,追求奔騰,卻過于偏執,難以掌控,只有心如同靜水那樣波瀾不興,才能了悟世間種種變化。《蘭亭集序》集字聯有這么一句:“虛竹幽蘭生靜氣,和風朗月喻天懷。”清雅的竹子和幽靜的蘭花,可以滋生靜謐的心氣;和煦的清風與明朗的月亮,往往使人心懷坦蕩。處紅塵人且靜,落俗事心乃平。懂得鬧中覓靜,便可擁有美好的生活。
人生最寫意的活法,往往隱藏在花花草草之中。花草,看似尋常普通,可花落花開間,不僅能帶來天地自然的生機,也昭示著世間萬物的輪回。如果心塵遍布,不妨澆水剪枝,擺弄花枝,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老舍平時最愛養花,他自認是個“勞動者”,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市井煙火的人。花開得大小好壞,他都不計較,只要花開他就高興,花生病他就難過。趕上狂風暴雨,他就把幾百盆花都搬到屋里去,累得腰酸背疼,等天氣好轉了,他再將其一盆一盆搬出去,樂此不疲。他說:“養花與人生一樣,就是要有喜有憂,有笑有淚,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須勞動,又長見識,這就是養花的樂趣。”老舍經過生活的甜酸苦辣,也深知人性的冷暖炎涼,對于他來說,閑坐賞菊,品茗沐陽,醉心于草木之間,這樣的生活才人間值得。
“談笑從容無俗客,山花風竹皆吾友。”伴花而居的生活,幽靜而豐富,與花竹為友,愜意舒心,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一顆沉靜下來的心,是在獨處時光里最真實的自我。《道德經》里說:“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聒噪也好,燥熱也罷,只要一個人內心平靜,思緒清晰,便能立于世間。
有位哲人將人生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像是一口井,平靜而單調;第二層次像一湍急流,奔騰而不寧;而第三層次像是一片湖泊,湖面寂靜如鏡,湖底深邃未知。”人這一生,越走到最后,越能感覺到世事無常,唯有承受過失去的痛苦,經歷過夢想的抉擇,才會對人生有所明悟。生命的豐富,從不在于活了多久,而在于有多少次的怦然心動;生活的幸福,不在于你擁有多少,而在于有多少回的心靈安靜。
《菜根譚》中說:“鯨豚沉潛于大海,幽蘭沉湎于山谷,從容沉靜與紛擾,清明沉淀于心靈。”生活于世,唯有沉得住氣,穩得住心,才有時間和能力去成長。放平心態,在熱鬧與喧囂之中,尋得自在,清凈安寧。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