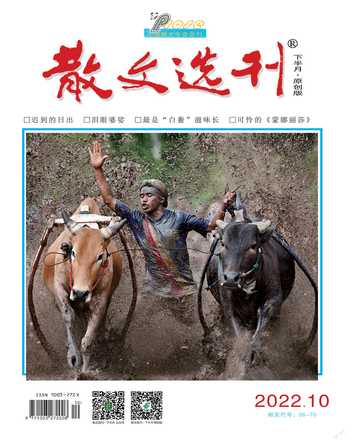夢見薄荷
2022-05-30 10:43:33徐江慶
散文選刊·下半月
2022年10期
徐江慶

河灘綠起來的時候,父親就坐不住了,他似乎聞到了空氣中隨風飄蕩的薄荷草的味道。
回到家里,父親摘下鐮頭嵌入院墻縫隙里的鐮刀,坐到院子的磨石邊,往栽在土里的磨石上反復澆些水,按上一鍋老旱煙,瞇眼吸著,等磨石慢慢吸透水,開始磨鐮。父親右手握住鐮頭處的木柄,左手食指和拇指捏緊鐮尖,將沾過水的鐮刀貼近磨石,一推一回,若即若離,如木匠用刨子打磨木頭,花樣滑冰擦著冰面小心滑行,沒多時,一把銹了的鐮刀磨得鋒亮。確保鐮刀鋒利,父親要感受下刀鋒,用大拇指肚在鐮刃上輕輕刮幾下,嚓,嚓,清脆如割麥的聲音,收獲的喜悅在心里蕩開。
不是只有父親關心著薄荷草,兒時的鄉下,好像每個人心里都記掛著薄荷草。薄荷草不同于一般的草,收割曬干后可以拿到鎮藥材收購站換錢。只要能換錢,就會從各種草中脫穎而出,受到關注。集體農耕時代,日子過得緊巴,閑時常到地里尋挖些半夏、桔梗、丹參、車前子等藥草,攢到夠斤兩了,趕鎮集時捎上,在收購站換幾個零碎錢。薄荷草不是專屬誰的薄荷草,如雨后樹底下生出的蘑菇,誰先發現誰先采。那些日子里,父親借著午睡的空閑發現了好幾片薄荷草。
父親去過的河灘我都去過,給父親當幫手,把割倒的薄荷草一把一把收起來,按順序歸成堆。有時一片薄荷草能割一大捆,有時幾處薄荷草也割不了多少,這兒割一把,那兒割一把,一個下午換好幾個地方。薄荷草的第一茬收割多在芒種前后,長到一尺高,莖葉齊壯,是收割的好時機。……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