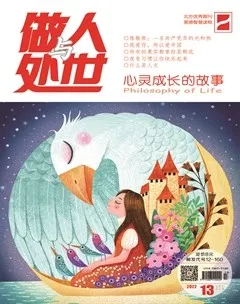什么是人文
唯有人文足千秋
人文是指人類文化中的先進部分和核心部分,其集中體現為: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
文化史不是文明史。在西方,文化史是從公元前3500年左右開始的,那時出現了楔形文字。到下一個1000年的時候,才出現了人物的傳說。大約公元前500年,出現了一個奴隸——伊索。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第一次人文主義的體現。為什么這樣說?相傳,《伊索寓言》的作者是一個被釋放的古希臘奴隸。伊索經常扮演的角色,是當主人請來客人時,由伊索為客人講故事。伊索知道,如果他講不好故事,他的自由就沒有希望了。最終,當伊索得到自由的時候,他已經46歲了,他的主人在臨死前給了伊索自由。當我們從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看《伊索寓言》時,就會對這件事情、這段歷史生出很多溫情和感動。
14世紀,西方文學史上出現了薄伽丘,再往后,又出現了莎士比亞、達·芬奇。按照我們今天的看法,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多數是帝王和貴族,即使出現仆人,也往往是可笑的配角。但我們為什么說莎士比亞的作品充滿了人文主義的氣息呢?這是因為,在莎士比亞之前,戲劇中演的都是神或是神的兒女們的故事。而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人開始站上舞臺。正因為這一點,所以它是人文的。
我非常感謝文學,是文學給了我善良和憐憫。托爾斯泰的《舞會之后》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舞會之后》講了這么一個故事:主人公伊萬是一名青年軍官,他愛上了要塞司令的女兒。這一天,要塞家舉行舞會,他和小姐在花園里散步,突然聽到令人恐怖的喊叫聲。原來,在花園的另一處,要塞司令在監督對一個士兵實行鞭刑。伊萬對小姐說:“你能跟你的父親去說說嗎?停止吧,懲罰一下就夠了。”小姐說:“不,我為什么要那樣做?我的父親在工作,他在履行他的責任……”年輕的伊萬請求了三次,小姐依然不答應。伊萬毅然告辭了,當他背過身走的時候,他說:“上帝啊,我怎么會做那樣一個女人的丈夫?不管她有多么漂亮。”
今天,我們為什么要紀念雨果?因為他高舉起了人文主義的旗幟。他的很多書都是在流亡的時候寫成的,連巴黎的洗衣女工也會用省下的錢買《悲慘世界》來讀。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一提。冉阿讓偷偷地把銀盤子、銀燭臺放進自己袋子里的時候,他手中拿著一根鋼釬,目光一直盯著睡在床上的米里埃教士。月光照在老人光禿的頭上、臉上,老人睡得那樣安詳。早上,米里埃教士醒來的時候,銀器都不見了,那是米里埃教士唯一的財產。管家說,那些銀器都被偷走了。但米里埃教士說,不是這樣的,那些東西原本就是屬于窮人的,窮人只不過是把原本屬于他們的東西又拿回去了。如果沒有這些窮人,根本就沒有這些銀盤子、銀燭臺,它們都是經過礦工、銀匠等窮人的手才生產出來的。這些振聾發聵的話,就是連洗衣女工也會讀《悲慘世界》的原因。
我們經常說,要補上科技這一課,要補上法律意識這一課。我認為,我們還需要補上人文這一課。
有一次在法國,我和兩位老作家一同坐車去郊區,車行駛在泥濘的小路上。那天飄著雨,在我們前邊有一輛旅行車,車上坐著兩個漂亮的法國女孩,不時從后窗看著我們。車輪滾起的泥土濺在我們的車窗上,加上雨滴,窗戶更臟了。我問司機:“能超車嗎?”司機說:“在這樣的路上超車是不禮貌的。”正說著,前面的車停了下來,下來一位先生,對我們司機嘀咕了幾句,然后回到車上,把車靠邊,讓我們先過。原來,那位先生對我們的司機說:“一路上,我們的車始終在前邊,這不公平。車上還有我的兩個女兒,我不能讓她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人文在哪里?從大的方面來說,它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但在我眼里,人文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人文就在我們的尋常生活里,就在我們人和人的關系中,就在我們人性的質地中,就在我們心靈的細胞中。
(根據梁曉聲在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大講堂”上的演講整理)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