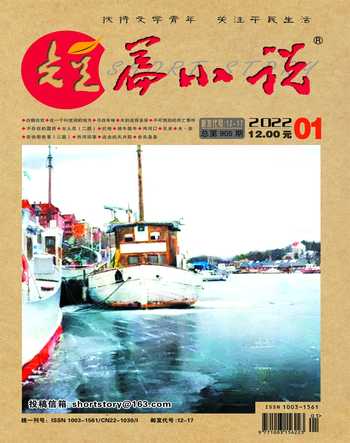在一個叫虎澗的地方
李加福
接到電話的時候王建國正在單位加班開會,母親熟悉的聲音里隱隱流露出一點異常的氣息,就是那一點異常讓他心里猛然一顫,他立即預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已經發生。這種直觸靈魂的感覺讓他沒有像往常那樣習慣性地匆匆掛斷電話,而是選擇了另一種不同以往的做法,他匆匆走出會議室去尋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那一刻他比誰都更想知道隱藏在母親帶給他的那種異常感覺之后的實質性的內容。果然,母親在電話那頭閃爍其詞地應付了幾句之后也就不再轉彎抹角了,她直奔主題告訴建國他父親失蹤了,她跟建國說,已經好幾天沒有回家了。
這把王建國嚇了一跳。
隨后他就一直心神不寧的,草草結束了會議后放下了手頭的工作準備回家。有幾位同事看出了他的異常,但沒人打擾他。
其實早早回家對王建國來說也沒什么意義,他夫人回娘家了,女兒在別的城市上大學,家里就剩下他一人,他回家又能做什么呢?只不過在現在這種焦慮的狀態下,他待在單位也同樣沒有意義。
獨自靜坐在書房里,王建國想起自己已經有很多年沒回老家了,他掐著手指算來算去不是十年就是十一年。以前他總是跟家里人說忙忙忙,不是說自己工作忙,就是說孩子學習忙,然而他心里比誰都清楚,這些都不過是他借來一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實情況是他跟家里鬧了點小矛盾。剛一開始,他憋著一口氣堅決不回去,他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有知識的人,明著跟家里鬧翻是不可能的,他只是借用這種方式以宣泄他內心深處無言的反抗。然而時間一長,他的想法變了,他覺得也沒有必要回家了,家里還有哥哥姐姐,他回不回去意義不大,他是無關緊要的人。不過逢年過節他總是往家里寄一些日常用品,從衣服、電器到酒水和糕點。另外,他每年還往家里匯幾萬塊錢。他想,只要給家里匯錢了,他也就算盡到義務了,還非要回去干什么呢?現在他對老家沒什么特別懷念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家仿佛已經不是以前的老家了,所以他再也不想回去。王建國回想自己心路歷程的變化,他從最初因為鬧別扭拒絕回家發展到后來成為習慣不想回家,前后只用了十年或者十一年。
以前可不是這樣的,他記得以前他是時常想家的,每逢長一點的節假日他就想往老家跑,每到年底他總想著回老家去過年,以前他對家鄉充滿了懷念。但是自從年齡過了四十以后,他對家鄉的懷念戛然而止。人到中年想法出現了變化,就像突然長大的孩子脫離了對母親的依戀,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想家了。
也并非一直都是無動于衷的,他也曾反思過,在一些天氣晴朗的日子里,他也曾想起過應該回去看看。特別是從前年開始,前年他接連不斷地接到母親和哥哥姐姐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他,父親患了阿爾茨海默病。在接到電話的那一刻,他一下子蒙了,整個人都不好了,在經過短暫的思維休克后,理性讓他重新振作起來。他在電話里安慰他們,先是母親,然后是姐姐和哥哥,他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解釋以緩解他們內心的焦慮,他說人老了生病是正常的,他說人就跟機器一樣,年紀大了身上的各種零部件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表現出各種各樣的病癥,他說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父親得那種病也是正常的,關鍵在于靜養,他囑咐他們在家多費點心多當心留意著一點兒,最后他說,他會在適當的時候回去看看。然而,當他心中的焦慮期一過,拖延的毛病又占據了主導,然后他就一直拖延到現在也沒回去。
究竟是什么原因淡漠了自己曾經對家的無比熱愛呢?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他也曾經仔細地琢磨過這個問題。他想,也許是因為老家曾經給他留下過魂牽夢繞過于美好的印象,所以他以前喜歡回家;而現在他不喜歡回家,也許是因為過去的每一次回家都令他失望。他每次回家都在尋找那種美好的印象,然而結局卻是一次次的失望,他再也找不到與他腦海深處的記憶相匹配的那些美好的場景了,這讓他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最后他得出結論,老家已經永久地失去了在他印象中的那種美好了。至于究竟有什么美好的印象,他也說不上來,如果非要讓他在記憶的廢墟中仔細搜尋,他想,也許是陽光。他記得那時候的陽光是美好的,盡管現在的陽光也不錯,但是那時候的陽光要比現在的美好十分。
在艷陽高照的日子里,王建國習慣于凝視窗外的陽光。陽光燦爛明媚,但他總是搖搖頭,好像是在說,陽光沒有以前的好了。他總是感覺以前的陽光比現在的美好,具體好在哪里他也說不清楚。就跟現在有很多人覺得以前的雞蛋比現在的雞蛋更好一樣,說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感覺就是不一樣,總是感覺以前的雞蛋更好。陽光亦是如此,珍藏在王建國心底的那一抹遙遠的陽光是最美好的。有時候他想,那時候的陽光照在干燥的土地上像是撒滿了黃金,那時候陽光的美好是可以觸摸到的,不像現在,看起來再燦爛的陽光也只是一種無法觸摸的虛無。
然而就在上個月,他的心里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上個月他剛滿48周歲,在大學念書的女兒特意坐飛機回來給他過生日,訂了很大的蛋糕。他喝了點酒,感到很幸福。就在這天晚上,他忽然發現自己還不知道父母的生日,這讓他心里倍感慚愧。生日那天酒后的回憶讓他深有感觸,他想是應該回家看看了。而今天母親的來電又喚醒了他內心深處的感覺,他在心里嘀咕,是應該回去看看了,父親已經老了。他心里想得更多的還是父親,很久以前那種溫馨的畫面再次涌向眼前。
王建國每次對老家的回憶最終總會收斂到對父親的回憶。父親是小學校長,在別人眼里他是一個嚴肅慎重、冷若冰霜、令人畏懼的人。但是在王建國的記憶里,父親也有溫柔的一面。在他的記憶深處珍藏著父親少有的溫柔時刻,當其他的記憶幾乎全都被遺忘消失殆盡時,這一抹記憶還在他的腦海深處永存。印象是那樣的深刻,以至于他常常會想起。王建國記得那時自己還沒上學,他后來一直想弄清自己那時的年齡,他想也許是四五歲,也許是六七歲,直到最后他發現糾結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時間不能倒回,他注定是永遠也無法搞清楚了,他唯一清楚的是那時自己還很小,有關那天發生的事也許是他能記起的最早的事情,所以整體的記憶是遙遠而又模糊的,只有一些片段還算清晰。
他記得那天陽光明媚,父親帶他去遠方的一所學校拜訪朋友。學校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一路都是山路,父親一路步行,他騎在父親的肩上,看到一條干白的土路曲折蜿蜒著向前無限延伸,身旁的樹木在不停地往后倒退。他們走過了一片又一片的稻田,又走過了一塊連著一塊的玉米地和紅薯地,然后穿過了大片大片的樹林,最后還翻越了一座高高的大山。一路上王建國聽到小鳥在路邊鳴唱,微風在耳邊呼呼地響,空氣里飄浮著花草的芬芳和木葉的清香。他記得有那么一個時刻,當他們穿過一片玉米地時,他還和父親面面相對蹲在路邊的玉米地里拉了一泡屎。每次想到這里王建國都忍不住笑起來,關于這一個鏡頭,他倒記得格外清楚。
他還記得他們在去的路上遇到一個谷場。谷場在山腰上,有幾個大人在谷場上干活,孩子們在谷場上玩跳房子的游戲。跳房子游戲那時在孩子們中間風靡一時,幾乎所有地方的小孩兒都在玩。也許是遇到了熟人,也許是要向人打聽什么,也許僅僅是因為太累了想要休息一下,他記得父親走向那個谷場,把他從肩上放下來。父親走過去跟谷場上的大人說話,而他則加入那群孩子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戲。他玩得很開心,及至后來父親要走時,他正玩在興頭上,不愿意離開。父親急著要趕路,而他則急得哭起來。結局是父親向他承諾,等回來時一定讓他和那些孩子們繼續玩,玩個夠。可是等到他們下午回來再路過那個谷場時,場上空無一人,孩子們都不見了蹤影。王建國幼小的心靈經受不住失望和委屈的雙重攻擊,忍不住又哭了。父親哄他說,沒人陪你玩,我陪你玩。王建國后來回憶起來一直都覺得不可思議,就在那天下午,父親帶著幼小的他在那個離家很遠大山深處的一個平整的谷場上玩跳房子的游戲。金色的陽光灑滿了谷場,他和父親跳了一回又一回,當太陽下山天邊掛滿彩霞時,他還不愿意走,一直玩到暮色四垂,他才不得不戀戀不舍地離開。他還記得當他們走到半路時周圍一片漆黑,父親向路過的一戶人家借了手電筒。而他一直騎在父親的肩上,父親一手扶著他,一手打著手電筒在夜間的山路上行走。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在父親的肩膀上睡著了,也不知道他們是什么時候回到家的。
在后來的回憶里,王建國記得那天的大部分時間他都騎在父親的肩上摟著父親的脖子,所以他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那個脖子,脖子強壯有力,上面有三顆黑痣。從他當時幼小的眼睛里看,那個脖子堪比老虎或者雄獅的脖子,因此他覺得父親像一頭老虎或者雄獅那樣無所畏懼無所不能,及至后來,在他心目中依然認為父親總是能搞定一切,而且永不衰老。直到三年前,當他接到電話得知父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時,他才驀然醒悟,原來父親也會走向蒼老。而在上月自己的生日聚會上,當他面對衛生間里的鏡子觀察自己花白的頭發時,他才意識到連自己都老了,更何況比自己還大三十多歲的父親呢。今天母親的電話讓他感到格外焦慮,也許比他三年前剛聽到父親患病時的那一刻更加擔心。他心里明白,若非情勢緊急,母親也不會特意給他打電話的。
父親究竟去哪兒了呢?他現在在哪里呢?王建國獨自一人思考著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在不知不覺間睡著了。他在短暫睡眠的期間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站在一個空曠圍場的中央,微風吹來花草的芳香,流鶯在場邊的樹蔭里鳴唱,白云在湛藍的天空里飄蕩,火紅的太陽掛在天上,地上灑滿了金色的陽光,他忍不住大聲歡呼,這就跟夢境一樣。然后他醒了,原來果真是一場夢,他感到有點失望。
王建國懂得夢由心生的道理,所以他明白夢見的也許正是他經常回憶的地方。夢境非常清晰,把他遠在幼兒時期的回憶一下子就拉近到眼前。只是那個地方的名字,他卻怎么也想不起來了。以前他是知道那個地方的名字的,他記得自己曾經還在一張紙上用毛筆寫下了那個地名,是兩個字,但是現在,他費盡心機卻一無所獲。
王建國后來打開電腦或許跟那個夢境有關,也許是夢境讓他興奮得難以入眠,也許是夢境喚醒了他對回家的渴望。他打開電腦后查看航班信息,剛好看到有一個早晨的航班,時間和價錢都從未有過的那么合適,他當即訂了一張票。他干脆覺也不睡了,忙著收拾了一些物品放在一個雙肩包里。要帶的物品并不多,反正他也不準備在老家多待,他估計也就待個兩三天然后就回來。
天亮之后王建國乘坐一輛出租車直奔機場。飛機準時把他運到省城,長途車把他送到縣城,隨后他坐上一輛攬活的私家車。一路上他都在想那個地方叫什么名字,可是,他一直想不起來,這讓他感到渾身很不舒服,如鯁在喉。他越是想不起來,就越是老往那上面想,也并非是他刻意要去想,實際上是不由自主地,王建國覺得自己鉆進了牛角尖里,他無法控制自己了。就連在私家車上他跟司機師傅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時,腦子里卻還在絞盡腦汁地苦思冥想。
突然,他眼前一亮,想起來了!虎澗,那個地方的名字叫虎澗。
虎澗,你知道嗎?想起那個名字后王建國感到渾身舒坦,他情不自禁地問司機師傅,你知不知道有一個叫虎澗的地方?
知道啊,司機說,我當然知道,虎澗林場嘛,我怎么會不知道呢?
在哪里?王建國又問。
還有五六公里吧,司機說,往前五六公里有一條岔路,從那里往右轉再開個七八公里就到了,一路往上,在大山里頭,以前車不通,只能步行,現在好了,公路通了。
王建國一直聽著,沒有說話,若有所思。
你想去嗎?司機見王建國一直沒反應,就無話找話地問他,他說,虎澗林場是值得一游的,經常有縣城的人去那里爬山。
那就在前方右轉吧,王建國說。他的回答幾乎沒有猶豫。
汽車在五六公里后駛離了正道,向右轉彎駛上了一條狹窄陡峭曲折顛簸的山路。一路都是上坡,兩邊長滿了茅草,里邊是懸崖,外邊是山澗,中間是一條狹窄的被陽光曬得泛白的土路,只能容一輛車通過,偶爾有摩托車迎面從上邊駛下來,騎車的人只好把摩托車歪向道路里邊貼在巖石上,才能讓汽車緩緩通過。
汽車沿著山路轉來轉去往上開了挺長一段路,直到前方出現一個較大的村莊,那個村莊掩映在竹林之中,仔細看有十幾戶人家。司機跟王建國說,只能到這里了,再往前的路只能步行,車不能開了,你自己走上去吧,已經不遠了。
王建國背上雙肩包下了車,接著往前走。沿途他看到了幾塊荒蕪的山間梯田,枯黑腐爛的稻茬顯示它們已經被遺忘良久。他還看到了幾處覆蓋著青瓦或者茅草的土房子,那些破舊的門窗、生銹的鐵鎖和泛白的春聯顯示它們早已被主人拋棄無人居住了。往前看是巍峨的高山和一望無際的林海。腳下的路越來越窄,也許因為行人稀少的緣故,有些地方茅草都長到了路中間。就是這一條狹窄的被陽光曬得干燥泛白的山路,它像一條曲折的羊腸向前蜿蜒前進,一直通向遠處巍峨的高山林海。一陣風吹過來,送來了多種山間木葉芳草混合在一起的芬芳,王建國頓時感到神清氣爽,遙遠而又模糊的記憶沉渣從腦海深處徐徐泛起,讓他覺得這眼前的一切似曾相識。他想,前方也許應該有一個平場。
當他轉過那個山嘴,一片寬闊的平場突然出現在眼前時,他既感到驚訝又覺得理所當然,一切似乎都落在他的意料之中。
這么一大塊平整空曠的場地在大山里顯得難能可貴,王建國猜測那是用來處理從山上運下來的毛竹和木材的,堆放在場邊的毛竹和杉樹也許正好給他的猜測提供了證據。向前方的大山看去,這時候能看得更清楚了,大片大片的毛竹林、杉樹林和板栗林匯成了綠色的海洋。毫無疑問,王建國在心里確信,眼前那些一眼看不到邊的林海肯定就是虎澗林場了。
在平場的邊緣,有一位老人坐在石凳上,眼神呆呆地盯著前方,他的表情看起來僵硬麻木,他好像已經坐了很長時間,他好像正在等待誰的到來。當他看到一個背著雙肩包的身影從山嘴那里慢慢出現走在通向平場的小路上時,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你是三娃子嗎?老人離得很遠就迫不及待地向來人問道。
王建國沒有說話,但他點了點頭。
我們快來跳房子吧!我等了你很久了。
老人說話時像個孩童,抑制不住的興奮和喜悅洋溢在他的臉上。
看著場地上畫得很整齊很整齊的房子,王建國就好像是跟老人約好了要來玩游戲似的,他急匆匆地卸下背包放在場邊的石凳上,脫下西裝掛在場邊的樹杈上,然后,他和老人玩起了跳房子的游戲。過了這么多年,游戲的規則他早已遺忘,但是沒關系,老人極具耐心一遍一遍地教他。
金色的陽光照耀著腳下平整的土地,看起來就像是撒滿了黃金,那種美好近在眼前,真的是觸手可及。不遠處的山腰上有兩三座白墻黑瓦的房子也沉浸在這無邊無垠的陽光里,門是關著的,不知道里面有沒有住人。王建國想那些房子也許已經被人拋棄了,也許里面還住著林場的守林人。
他們玩了一局又一局,身上流出了很多汗水。王建國貼身的襯衣早已被汗水浸透,臉上掛滿了汗珠。時間過得真快,他們似乎玩了很久,但實際上又好像并沒玩幾局。眼看夕陽親吻著遠方的山岡,王建國站在場邊點燃了一根香煙,他記得他剛踏進這個場地時,太陽還高高地掛在偏西的天空里。
王建國轉過頭時剛好看到有一座房子的門開了,有一個中年人從屋里走出來站在門口,他也看見了王建國。兩個人隔著老遠互相望著對方,彼此都表現出了應有的驚訝。
是王建國率先打破了這種僵持的局面,他一邊邁步向那個站在門口的中年人走去,一邊從兜里掏出香煙向他做出了一個遞煙的姿勢。那人立即做出了回應,他邁步向王建國走來,伸手接了王建國遞過去的香煙,嘴里問道,你是到林場來爬山的嗎?對于這個問題,王建國不知道怎么回答合適,所以他很僵硬地點了點頭。那人又問道,你是從哪里來的?王建國隨口回答道,從縣城來的。
你走了那么遠的路,肯定口渴了,進屋來喝口水吧。
不了不了,王建國連忙說,我不渴,謝謝!
那人返身走進屋里,不一會兒又出來了,一手提著一把老式的提梁壺,另一只手里攥著三個茶碗。他走過來把茶碗擺在場邊的石凳上,倒了三杯茶。王建國連忙道謝。站在一旁的那位老人嘴里哆嗦著也不停地說著謝謝。
這位老爺子,那人指了指自己的腦袋向王建國解釋說,他這里有毛病。他在這里待了好幾天了,他見到每一個人都問人是不是三娃子,要不要跟他一起玩跳房子的游戲。
他晚上是怎么過的?王建國問道。
第一天晚上他住在我的柴房里,我半夜起來上廁所,聽見柴房里有響動,我拿手電筒一照,把我嚇了一跳。隨后的晚上我都讓他睡在我們的空屋里,現在這里空房子多,都沒人住了,人都搬走了,我在一張舊床上給他鋪了一床破被褥,他一到晚上就睡在那張我為他特別安排的床上。
看到王建國對有關老人的話題興趣盎然,那個中年人便不厭其煩地跟他詳細敘述著老人的情況。
這老爺子,他接著說道,你可別看他現在有毛病,但是看起來很有氣質的樣子,以前也許是一位知識分子呢。而且他的精神好像是忽好忽壞的樣子,有時候說的話你都分辨不出來他是有病還是沒病,就比如說昨天晚上吧,我問他,你家在哪兒?要不要我送你回去?或者帶信讓你家里人來接你?他先是說他不記得了,后來他又說,他說——說到這里那個中年人停頓了一下,他用手指搔著臉龐仔細地想了想,然后接著說道,他說他害怕有那么一天,他真的永遠地走丟了或者他死了,他的家人會太過傷心,所以他要提前預演一下。你聽聽,能說出這話的人,腦子像是有病嗎?這像是腦子有病的人說的話嗎?
那個中年人絮絮叨叨地說著,沒有注意到王建國的反應。當他終于轉過頭來望向王建國時,他看到王建國呆呆地盯著天邊的夕陽;他看到夕陽正在慢慢沉下山岡,余暉映紅了半邊天空;他看到淚水從王建國的眼角涌出,順著臉頰慢慢地滑落,有一串淚珠在夕陽光輝的照耀下閃閃發光。眼前的情景讓他備感驚訝,他不過是隨口說說而已,讓他難以明白的是,他隨口說出的幾句話竟然讓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潸然淚下。
責任編輯/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