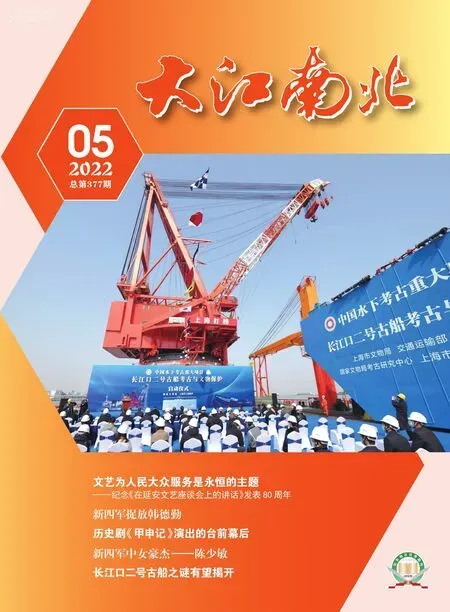三代人的婦女節
劉衛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還是孩提。母親在縣一中當圖書管理員,兼做報刊發放和敲鐘。她早去晚歸,盡職敬業,受到了校長和同事們的稱贊,每年被評為勞動模范。母親說,那時婦女節的意識很淡漠,只是日子到了,校長就會開個簡單的茶話會,吃點糖和瓜子,領導向全體女同志表示節日祝賀,沒任何福利,倒是可以申述自己家庭和工作上的困難,譬如,兩地分居、住房狹小、懷孕期想調課等。領導們辦事效率也很高,現場會商,能及時解決的,不拖延;暫時不行的,解釋理由,將盡力去協調。那時,母親覺得我家情況尚可,也就沒有給領導添麻煩。盡管如此,從校領導關心其他女職工的作為上,母親收獲了感動。
記得,有一年婦女節,身為單位領導的父親一直忙工作,節日到來了也無動于衷,既無言語表示,也沒備禮物。為此,母親心里很失落。直到出完差,父親半夜才回家。放下公文包,父親似乎意識到大事不好,急沖進廚房,在冰箱翻出一小塊瘦肉,細心做了一碗肉絲雞蛋面,端上來,權作補償。同時,父親還一個勁地道歉,說好話。盡管做得不咋地,但那一刻,母親覺得心頭暖暖的,眼里閃動出感動的淚花。此后,母親也一直會念叨,那年的婦女節最難忘,一碗面讓她哭得稀里嘩啦,其中藏著兩老濃濃的夫妻情。
到我們這一代,我妻子把婦女節看得挺重的。年過完,她就扳著手指算日子,更積極地圖表現,爭取她負責的班組實現一季度的開門紅。她所在的國企整染布廠,百分之九十的職工為女工,她們是生產主力軍。上班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但女工們干得熱火朝天,很少計較工作上的得失。那個年代,改革開放剛開始,隨著體改的深入,周圍的一些廠有的倒閉,有的轉產。同行里,就數她們廠一花獨秀。這不僅歸結于頭們的領導有方,也與他們對女工關愛有加是分不開的。三八婦女節在廠里搞得很隆重,不僅給勞模們發重獎,會上介紹經驗,中午吃豐盛大餐,下午看包場電影,每個人還能領豐厚生活用品。那一天,女工們是最放松最快樂的。妻子的格局比較大,常懷初心,她說:這個節日可以檢驗女同志對促進經濟發展所作貢獻的認可度。
我女兒成家立業后,也被順理成章地劃為婦女群。她大學畢業后,被聘為一家織布廠的生產調度。女兒的性格潑辣、能力強,自薦為工會副主席,遇事跟老板搬條文,據理力爭,為維護職工正當權益做了很多事。三八節被列為企業的大節。女兒組織活動,親力親為,把這天慶祝會開成了勵志會、鼓勁會、建議會。她與老板和管理中層互動,坦誠溝通,同心協力謀發展。她認為,不僅要讓女員工物質上收獲頗豐,精神上也要加深對企業的認同和粘合度。老板逢人就夸,對她這個工會女主管,既“怵”,但又離不開。每年的三八節,老板過得有些膽戰心驚,擔心她又會整出什么“幺蛾子”來。工友們,尤其是企業里的姐妹,倒是樂于由她代言。
不同時代的三八婦女節,都會打上不同的烙印。我們要重視這個特殊的節日,讓淡漠的意識重新煥發出光彩,更要看到婦女在提高家庭福祉和社會發展中所作的特殊貢獻。
(本欄編輯 盧天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