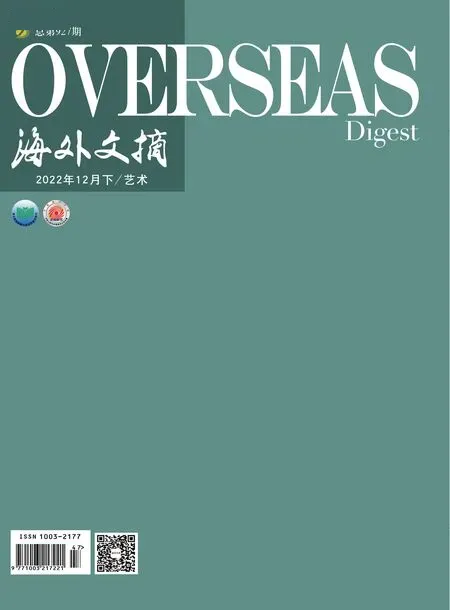文化的承繼:英格蘭“醫院”的衰落與“學院”的興起
□劉苜檸 盧泰宇/文
英格蘭醫院前身是公元6世紀不列顛拉丁化時期所建立的教會醫院,“hospital”一詞也發軔于拉丁語hospitalis。中世紀時期醫院并非是單一的疾病救治機構,而是集行旅接待、慈善救濟、救治病患、宗教管束等社會職能為一體的綜合性實體,屬于基督教的院內救濟,宗教色彩濃厚。隨著由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的到來,英格蘭的醫院逐漸衰落,或是資金不足,地處偏僻荒涼而成為廢墟,或是被拆除成為貴族或皇室的私人地產,或是幸存下來重組為救濟院等,但其中一部分轉變了職能,為學院的興起提供了物質準備,英格蘭醫院的衰落與學院的興起是14-17世紀英格蘭經濟模式和政治結構深刻變動的微縮反映。
自中世紀早期,英格蘭的醫院大多由教會直接建立、依靠世俗捐贈維持運轉,以宗教管束為核心職能,發揮著慈善救濟的功能,依附于修道院。而在整個中世紀,宗教神學在教育中占據統治地位,對知識教育的高度壟斷更是神權統治的重要根基,但隨著12世紀以來市民階層群體的壯大、對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的強烈需求,宗教神學愈發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桎梏,世俗化、平民化、專業化的高等教育成為時代呼喚的產物,而大學則是最合適的載體。需要注意的是,中世紀的神學教育與近現代的高等教育之間并不是完全割裂的關系,前者不會突然消失,后者也不可能突然出現,兩者之間顯然存在一種繼承與發展式的過渡,醫院向學院的轉型便是如此。學院在舊社會體制的母體中孕育而生,吸收并轉化著舊體制中歷經現代化洗禮的良性殘余,茁壯成長。
1 英格蘭醫院衰落的時代背景
在中世紀末期的14-16世紀,英格蘭修道院的慈善事業一直處于日漸衰落趨勢,最終因16世紀亨利八世實施宗教改革、解散所有修道院而從世俗關注中淡出。作為修道院慈善事業的載體,15世紀末、16世紀初時,已基本不再新建教會醫院了,依舊殘存的醫院則呈現出普遍衰退的跡象,其社會救助和醫療功能也日漸退化。根據傳統,教會組織作為占據歐洲土地的1/3并擁有什一稅收入的存在,本應將其收入的1/4或1/3用于濟貧。但因教會自身存在大量寄生人口,加之文藝復興所導致教會體系世俗化趨勢加強,其濟貧經費實際上呈現出大幅度的下降[1]。16世紀上半葉,因宗教改革,醫院更是幾乎全部被廢除,教會濟貧事業發展傾頹之勢可見一斑。一切跡象都在表明,醫院此時在社會救濟體系中的地位已遠不如前。
在教會為修道院的世俗化所采取的措施與社會整體變動的綜合影響下,英格蘭修道院慈善事業之衰落無從避免。
首先,醫院是脫胎于教會的產物,教會體系的沒落是造成修道院醫療慈善走向衰敗的根源。修道院作為西歐宗教事業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在10-13世紀興盛之后隨即進入衰落期。雖然其衰落是在諸多因素疊加影響之下共促而成,但“天主教會大分裂”與西歐各國王權普遍集中背景下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無疑主導了這一進程。此外,中世紀晚期以來,社會宗教熱情轉向以及修道院中世俗成分的增加也使得院內原本的修道生活不再純粹。《維多利亞郡史》中就有不少因貪污腐敗所導致的醫院衰落的例證,如坎伯蘭郡卡萊爾的圣尼古拉斯醫院便是因院長將醫院公章據為己有,并在沒有征得修士和修女同意的情況下責成醫院向不同的人收取租金,于是屬于這所醫院的篇章很快終結了[2]。
其次,在中世紀后期,無論是救濟院、麻風病院還是教會醫院均普遍出現衰落跡象,這與社會捐助減少、資金短缺有很大關系。究其根本,中世紀時醫院的資金主要來自社會捐助和醫院自身的地產及經營收益,穩定性較差[3]。而醫院的經費來源受限,在某種程度上便直接抑制了其救助功能的正常執行。再者,受治療水平限制,缺少具體分工與專業治療手段的教會醫院并不具備現代型醫院類似的醫療功能,它們實際上往往只能作為預防疫病蔓延的隔離場所,缺乏長足發展的先決條件。
最后,戰爭也是當時醫院覆滅的因素之一。作為人類歷史的重要內容,戰爭在王朝更替、階級沖突、權力斗爭和社會演變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歷史這座龐大機器的發動機、推動力,或者更確切地說,起到了齒輪的作用。[4]”從《維多利亞郡史》記載看,坎伯蘭郡卡萊爾的圣尼古拉斯醫院就未能在13世紀末爆發的蘇格蘭抗英戰爭中幸免于難,而切斯特郡的圣吉爾斯醫院也淪為17世紀內戰不可抗因素之下的犧牲品。
總而言之,教會醫院在新舊事物的碰撞中顯現出過渡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在14-17世紀教俗兩界的激烈沖突中逐漸弱化自身的社會救助和醫療功能,最終與教會一同走向衰亡,而不得不轉型。
2 醫院轉向學院
現代大學的直接源頭是歐洲中世紀的大學[5]。大學是中世紀的特殊產物,也是中世紀留給后世重要的的文化遺產。目前多數學者認為中世紀大學產生于12世紀,也有人認為產生于11世紀末[6]。大學出現后不久,學院(College)也始見雛形。1180年首個學院在法國的巴黎大學建立。這里所談的學院特指學院制下的學院[7],這些學院并不是按學科來劃分的,而是將不同學科的學生融于一個學院之中。學院的規模不大,且每個學院都是一個獨立的法人,擁有自己的教師、職員、校舍、基金、各種學習和生活娛樂設施。學院制使大學像一個由眾多自治共和國組成的聯邦,大學和學院分工協作,共同培養人才[8]。學院制雖然源于巴黎大學,但卻興盛于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英格蘭的大學里學院的獨立性更強[9:129+264]。
在英格蘭醫院向學院轉型的過程中,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共有9個學院與英格蘭醫院轉型產生了重要聯系,其中牛津大學4個,劍橋大學5個。
這些教會醫院的衰落為學院提供了辦學場地。如牛津大學的默頓學院就購買了貝辛斯托克的圣約翰浸信會醫院的一座莊園、150英畝土地、6英畝草場和4英畝牧場及附屬物以及伊沃德的16英畝土地[10],這無疑讓默頓學院得到了更寬闊舒適的辦學場所,推動了它的辦學進程。
中世紀醫院作為修道院的附屬機構,其嚴格的宗教管束和醫院管理模式對中世紀大學校園管理產生影響。醫院作為修道院的附屬機構,宗教管理和作息安排異常嚴苛:如位于赫斯福德郡圣朱利安的圣奧爾本斯醫院遵循的《修道院章程》表明病人們的衣著(要穿包裹全身的黑色長袍和軟底靴子)、日常生活、活動區域都受到極大的限制[11]。而早期的中世紀大學,“管理大學的權力一般隸屬于教會”,且教會還掌握著報時的控制權,可想而知其為大學管理模式帶來的巨大影響:牛津大學有著嚴格的學校規章制度,如固定的開門、鎖門及宵禁時間,定時進行各種宗教活動等[9:246]。這是醫院的管理文化在大學和學院中承繼的體現。
由醫院向學院轉型還和教派紛爭有關。1448年貝德福德郡的法利醫院[12]和白金漢郡的呂杰斯霍爾醫院都由于外來的宗教原因被亨利六世授予了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這里的外來宗教原因指的是約翰·威克利夫的學說,他的教義已經在牛津大學引發了混亂(如圖1所示)。國王學院的創建者都是王室貴族,他們擔心倘若大家聽從威克利夫,就會在劍橋大學形成一個專為會讀會寫的新興資產階級服務的羅拉德派。他們不希望這樣的異端邪說給劍橋大學帶來影響[13]。于是亨利六世直接將這兩所醫院中的羅拉德派鎮壓下來,以此反過來增強劍橋大學中對羅拉德派的抵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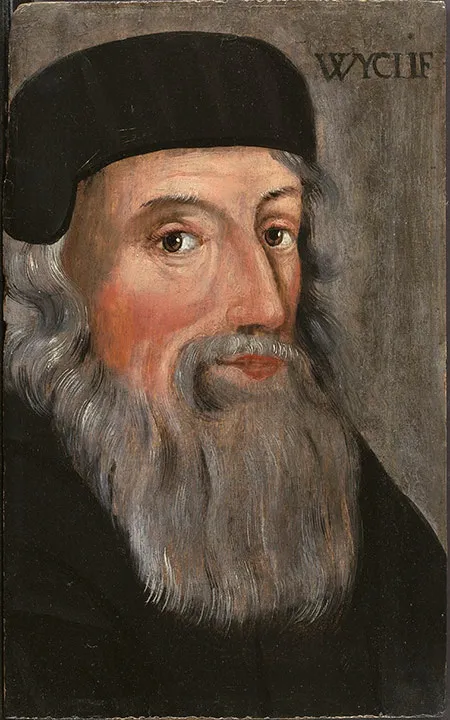
圖1 約翰·威克利夫,一幅16世紀的肖像
在醫院向學院的轉型過程中,也受到了王室和貴族很大程度的推動。對于劍橋大學的圣約翰學院來說,圣約翰醫院是其直接前身。大約在1470年,林肯主教兼大學校長托馬斯·羅瑟漢姆考慮到院外人士經常對醫院造成傷害,于是將大學會員的特權擴大到了醫院[14]。有觀點認為,早在15世紀時的圣約翰醫院就因為享有這些特權,已經融入到了大學的機體當中,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學院了。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學院向醫院的大轉型是由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博福夫人和劍橋大學校長約翰·費舍爾在16世紀初直接推動的。瑪格麗特不僅是一位強硬的政治家,同時還是學術與藝術的贊助者,伊拉斯謨稱她為“神圣的女英雄”,而作為劍橋大學校長的費舍爾則是瑪格麗特的私人神甫[13]。瑪格麗特在費舍爾的勸說下,將新學院的選址放在了圣約翰醫院,并為其留下了豐厚的捐贈資產。在圣約翰醫院所在的地方建造一所學院的工程費用在5000英鎊左右,在那個時代是個大數目。正因為瑪格麗特的捐贈過于豐厚,以致于她的孫兒亨利八世都想來分一杯羹。瑪格麗特過世后,費舍爾歷經磨難,最終才為醫院的解散和學院的建立爭取到了教皇、王室和主教的許可[15]。1512年后圣約翰學院在圣約翰醫院的土地上逐步建立起來。除了醫院的小教堂以外,很多東西都是新建而非翻修的。廚房、餐廳和壯觀的門樓在這塊土地上建起來了(如圖2所示)。

圖2 圣約翰學院大門
總之,英格蘭醫院向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學院的轉型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私人關系、教派紛爭、財產爭奪的漩渦當中,經歷了相當曲折的歷程,體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另一方面,醫院向學院的轉型也為學院提供了更廣闊的辦學環境,更嚴格細致的規章,以至于直接的生長母體,醫院的文化也在這一過程中承繼下來,對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發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綜上所述,醫院的世俗化轉型使其逐漸從最初的宗教慈善機構過渡到開始為現實社會服務的地方實體,這既是宗教內部各種因素邁向現實的世俗社會的過程,也是宗教外部政治、教育、科學文化等不同社會要素陸續排除宗教支配與影響力,逐步實現宗教分離的過程。并且,醫院在衰落以及向學院轉型過程中積極迎合時代需要,無疑為世俗社會高等教育以及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動力。■
引用
[1] 向榮.論16、17世紀英國理性的貧窮觀[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69-74.
[2]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umberland: Volume 2[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05.
[3] 鄒翔.中世紀晚期與近代早期英國醫院的世俗化轉型[J].史學集刊,2010(6):18-23.
[4] [西]胡安·卡洛斯·洛薩達·馬爾瓦萊斯.從投石索到無人機:戰爭推動歷史[M].宓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5]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6] 賀國慶.歐洲中世紀大學起源探微[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21-28.
[7] 范廣欣.從“大書院”到“大學”:近代中國對university的翻譯[J].江海學刊,2019(4):179-187+255.
[8] 劉寶存.牛津大學辦學理念探析[J].比較教育研究,2004(2):16-22.
[9] 希爾德·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1卷[M].張斌賢,等,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10]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Hampshire: Volume 2[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03.
[11]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Hertford: Volume 4[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71.
[12]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Bedford:Volume1[M].London: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04.
[13] G.R.埃文斯.劍橋大學新史[M].丁振琴,米春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14]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ambridge and the Isle of Ely: Volume 2[M].London: 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48:303-307.
[15] 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ambridge and the Isle of Ely:Volume 3,the City 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M].London:Victoria County History,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