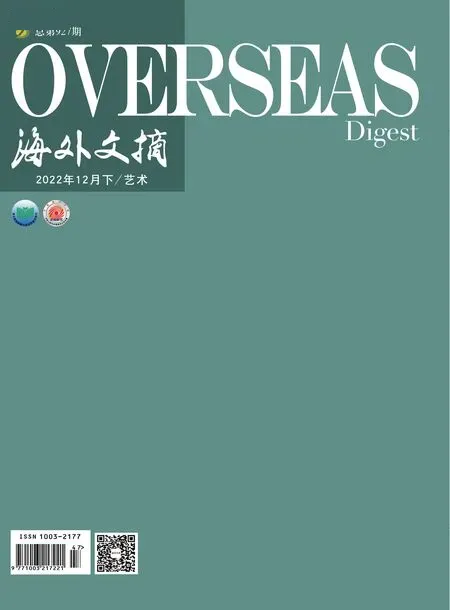西魏佛教供養人雕塑之美
——以麥積山石窟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為例
□化雷 劉琪/文
麥積山石窟供養人像,從視覺上看,具有一種脫穎而出、不俗的質感,但又有著古樸、樸素的形體特征。歷史上有很多人因信仰某種宗教,通過提供資金、物品或勞力,開鑿石窟、繪制壁畫或建造雕像,并且在繪畫或雕像的邊角或者側面雕刻自己、家族或親眷等人的形像,這些形像,又稱為供養人像。通常情況下,佛像受樣式主義的影響比供養人像嚴重,因為佛像本身是一種信仰,佛像的出現不是為了滿足藝術的需要,也不是一種藝術行為,而是一種宗教信仰行為。因此,在判斷塑像藝術價值或者藝術行為水平高低上,供養人像往往更能表現出與其產生時代相匹配的審美取向。時至今日,雕塑的表現已經從昔日為了滿足宗教的需求而進行的雕塑行為,演變成可以為了各種行為進行雕塑藝術創作,這是社會文明開放、文化發展的結果。雕塑的形式多樣化了,語言豐富了,表現的主題也從宗教雕塑橫向開來。我們有必要回頭審視古代的佛教雕塑,感受不同于今日的雕塑之美,本文便以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為例進行討論。
1 表現形式與語言的統一
“思維可以看作是作品的靈魂,而外在形式則是作品的生命,沒有了形式,作品不能成立。[1]”雕塑的語言依附于作品的形式,往往采用哪種藝術形式會制約甚至決定采用什么樣的表現語言。
麥積山石窟北魏的泥塑在麥積山石窟造像中占有很大比例,好的作品基本上也是以這個時間段的為主。但是,供養人像卻不同于其他塑像,有著自己獨特的樣式。西魏時期的供養人像在麥積山石窟中尤為突出,大多是以單體直立形式重復的出現,缺少群雕形式,構圖形式多使用直線形式和三角形式,這些特點使其具有獨特的藝術美。
從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第123窟童男童女造像的形式上看,以直立式的圓雕為主,直線與弧線、團塊和線相互結合,且多采用豎式構圖,這種構圖給人一種安靜祥和的氣氛,動態上不作過多的追求。豎式或者站立式雕像,在佛教雕刻中是很常見的一種形式,符合審美的需求,還有一種向上、升華、安靜、肅穆等心理情感的特點。如女供養人的一臂置于胸前,一臂下垂,或雙手攏于袖內,雖是恭敬肅然的姿態,但又不失人正常狀態下的自然動作和行為之感。與佛像的立式無為相不同,它是一種自然狀態下人的站立動態。雖是自然站立的動態,卻是創作者有意而為之的,這是想要通過自然站立傳達安靜祥和的氛圍,表現出人在佛面前是有安全感的,在精神上是愉悅、輕松的,而不是緊張的,內心是平和的,并非是恐慌的,這是一種自省而自信的轉變。
2 以情趣為主的語言表現
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供養人造像的表現語言在情趣中尋求相向、相似,忽略解剖的嚴謹性帶來的嚴肅之感,強調泥塑最本質、最樸素的審美情趣。
童男童女供養人像,基本上放棄了解剖學的制作方式,完全按照制作者的理解進行制作。例如供養人像頭大身子細,臂膀細小,從頭到手也沒有任何解剖學應該有的痕跡,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一件非常符合對象特征的作品,結構在形體特征的支撐下是非常合理的。能在不符合解剖學的理論下創作出更美的雕塑是眾多雕塑家一直以來的藝術追求,完全可以在符合人體結構特征的前提下放棄對解剖學的觀念進行創作,這就是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供養人像帶來的審美觀念。
供養人造像的整個形體表面沒有“曹家樣”的“曹衣出水”和吳道子的“吳帶當風”,更沒有顧愷之和陸探微的“秀骨清像”,因此少了些文化制約的痕跡,少了幾許宗教的痕跡,人面對泥塑有些釋懷。也正是因為沒有這種“曹衣出水”和“吳帶當風”,才突出了泥塑的整體性和形體感,引入眼簾的是泥塑形體內在的張力。
3 線性語言在作品中的表達
線是構成麥積山石窟泥塑的骨架、是泥塑體現情感的載體、維持泥塑生命的靈魂……線在麥積山石窟西魏供養人像的表現語言中,像音樂一樣,作為“音符”為其演奏歌唱,以其高、低、長、短的韻律打動著觀眾的心弦。美國學者威爾·杜蘭一語道破了中國傳統藝術中線與韻律的重要性:“中國藝術不求濃烈的色彩,只求韻律和精確地線條,中國藝術幾乎完全基于精準和優美的線條。[2]”
童男童女供養人像在形體的處理中以長直線和短弧線為主,造型簡練概括,極好地表現出人們所追求的內在的精神和理想的美。在衣服的處理方面,都是以長直線為主線,用衣服來襯托身體;修長的身體顯示出健康的體魄和供養人在身體發育時期的生理特征,以及女供養人(圖2)的亭亭玉立之美。短弧線主要用在發辮和臉部的口鼻眉目等主要部分,簡單的幾根線條,表現出男供養人(圖1)天真樸實和女供養人美麗純潔的面貌,在耳朵與面頰之間壓了一條淺淺的陰刻線,恰當的顯現出女供養人的豐腴與可愛;同時帶給人們一種訴說安詳的審美意境。

圖2 麥積山石窟第123窟西魏童女
4 形體中對體積的追求
我國臺灣藝術評論家蔣勛先生在對欣賞雕塑藝術品的原則上提出了十分有深意的觀點:“把雕塑還原為材質的體積、重量與質感。[3]”不同的材質在藝術品中的應用,既是作品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又是美的原始的體現;材料的不同對于藝術審美能夠間接地起到自然的暗示和經驗的提升心理作用。
體積感是衡量雕塑藝術品的一個基本要求,也是人們在欣賞雕塑時的第一感受。從整體的體積感看,童男的動態設計只是用橫、豎兩個圓柱組合而成,很像“十”字形;身體上沒有過多的裝飾,連表現人物內心情緒的手也給隱藏的一點不露,以雙手籠袖交握來處理。包括頭上戴的氈帽和領口,都是以圓圈帶過,沒有過多復雜的造型。衣紋也只是用幾道陰刻線沿著形體轉折來表現完成,使線做到了附著于體,襯托于形的作用。這種處理手法使得所表現的男性兒童顯得更加的淳樸、憨厚,極其符合勞動人民的形象。而童女的整體動態設計相對復雜一些,右臂自然下垂于體側,左臂彎曲,手置于胸前;設計者也是從整體考慮,用寬長的衣袖遮住了右手,只留左手置于從鼻尖到兩腳之間的中軸線上,目的是將人的視點集中到上半身及頭部。頭上的丫髻是女供養人的點睛之筆,好似一對天使的翅膀置于后腦的兩側,既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生活氣息,又擴展了人們的想象空間。丫髻的處理和身上衣紋的處理是一樣的,都是用陰刻線的手法表現發絲和衣紋,沒有過多的裝飾。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供養人領口處的圓圈,很多人認為這是個項圈,其實它是衣服的領口,是當時很有特色的當地少數民族服飾,窄袖、圓領長袍。設計者對這個圓領的處理相當大膽、簡潔和概括,只是做了一個簡單的圓形就代表了,而且在銜接的地方做了一個錯位處理,代表衣服的開口處;這些特點也符合供養人在這個年齡段所具有的趣味性裝飾因素。作為一個形態飽滿活生生的藝術形象,作者從整體出發,把枝枝叉叉的一些瑣碎的東西全部去掉,剩下的就是給人們最深刻、最具有濃厚生活氣息的人民的形象,使人感到更加可親可愛,正如王子云先生所言:“塑工們在塑像過程中,把民間的生活現實,如實地帶進佛窟中來,使神界和人界化為了一體,因而使得麥積山石窟造像,格外富有人情味和民間氣息。[4]”
5 心理活動的表現
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供養人像對童男童女心理的刻畫,一方面體現在動態上,在隨和、寧靜、閑適的不經意中,揭示出佛教隨意、自然修行的活潑風習。因此佛教藝術品所受經典嚴格束縛的意味大為減輕。
澄懷觀道、般若自在的思想彌漫在童男童女周身,那天真爛漫,自然、純情的神情和心理刻畫,似乎要引領眾人擺脫現實世界的物我糾纏,達到返璞歸真的忘我境界。這一造像深刻的內涵,活潑的形式為我們營造了一個清新的佛的觀照氛圍。
不管童男童女的形象在佛教中寓意是忍辱樂法,還是在現實中目的是普度眾生;不管是人物造型的整體處理,還是面部表情的微妙變化,都圍繞著欣賞者的心理及佛意開花為初衷,這亦反映出佛家借物晤悟,資助修行的至深情結。
童男童女的表情及身體語言均著力表現一種虔誠、聰慧、天真而又純樸的性格,無論是雙手攏于袖,還是單手置于前;無論是微瞇的雙眼,還是微翹的嘴角,都表達出一種極強的個性,引入另一種精神世界。
石窟中供養人的形象多是虔恭、善良、恬然、委婉的,童男童女形象也許是因為年齡的關系,多了一些甜蜜、淳樸,多了一些現實和希望。這正是麥積山石窟西魏時期供養人像在心理活動表現上的成功之處,以及童男童女能夠在眾多塑像中脫穎而出,讓人流連忘返的原因。表現形式和語言吸引的多是專業的雕塑創作者,而心理活動的表現吸引了所有欣賞者,人們不自覺地通過他們的面部表情去探究他們的內心,并且從中獲得一份平和。這也正如徐人伯先生所說:“人們對于藝術的欣賞是喜歡讓自己熟悉的東西在藝術中出現。[5]”
6 結論
線與體的交織,光與色、色與體的交集,親切、趣味、質樸、形體,這是所能表達石窟泥塑的最好的詞匯,沒有厚重的、沉甸甸的讓人抬不起頭來的質感,只有親切的、仿佛剛剛完成的生動與新鮮。這種生動與新鮮,是雕塑本身的氣質,是和質樸親切相映成趣又相互統一的。泥塑的面部塑造摒棄了北魏時期超越現實的理想型容貌,使其更加接近現實,更具濃厚的生活化氣息,從今天的審美角度來看,恰到好處。
在古代的造型藝術反應現實生活還不是很廣闊的時候,藝術家能夠通過他的作品表現出活生生的現實社會的人及其豐富的內心情緒,對今天的繼承與創作有重大的意義。歷代的雕塑家在不斷繼承與創作中逐漸形成本民族傳統雕塑的特點,就是突出的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而達到形神兼備的完美境界。因此,在麥積山石窟的諸多作品中,西魏時期的供養人像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引用
[1] 蔣躍.繪畫的終極——繪畫形式觀念與語言的意義[J].文化藝術研究,2009,2(1):205-210.
[2] 威爾·杜蘭.東方的遺產[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
[3] 蔣勳.美的沉思:中國藝術思想芻論[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4] 王子云.中國雕塑藝術史(上中下)(中國文庫藝術類)[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5] 徐人伯.麥積山佛像雕塑藝術研究[J].西北美術:西安美術學院學報,1991(3):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