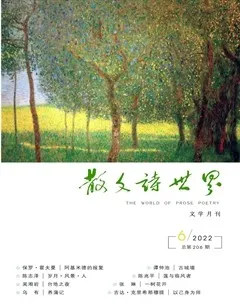散文詩,用真情記錄生活
張曉裕
寫一首冗長的散文詩太難了。像你愛的人向你索要一萬個愛她的理由,如若沒有身體的切實體會,心里沒有真情實感,愛得不夠徹底的話,撕扯心底的鉛墜不是一般的重。所以,散文詩同愛情一樣,都是在細心品鑒生活后產生的細膩情感,而散文詩需要用詩人積淀的文化輸出。
席慕蓉先生在《無怨的青春》代序《詩的瞬間》中寫道:“詩,只是一個困惑的人,用一顆困惑的心在辨識著自己此刻的處境。”“困惑”的東西太多:四季為何輪換著來,貓站在墻頭不動——它在想什么,父親的背為何一日比一日彎曲,若干,都來源于生活;而“處境”是內心的處境(身體的處境表達為動作,內心的處境表達為語言和情感)。身體留在現實,把內心和靈魂抽離出來匯聚,在紙上鋪開,斷斷續續,情真意切,就是散文詩。散文詩沒有拘束,不拘泥于作品的音韻和格式,是跳動的斷章還是連續的長詩,云卷云舒,就看作者心里的風怎么刮了。
散文詩是用真情記錄生活,但作者不能把自己困在現實里創作,抽離出來的靈魂和內心要像百靈一樣靈活,能歌唱也能飛翔,澄宇了無邊際,思想插上翅膀,散文詩就不只是人間煙火(這并不與我“用真情記錄生活”中的“生活”所矛盾,生活包含萬物,散文詩也寫不完)。散文詩中的思想需要讀者理解,它的巧在于文字的魅力,象征的魅力,散文詩創始人之一波德萊爾就是西方象征派詩人,寫作名家梁鴻在倫敦光華書店的演講中說到:“寫作與世界的關系,就像魔術師與真相的關系”,散文詩魔術家表演的魔術可能是假的,但是真相——表達的情感,應該確保是來自于生活的真情實感。以便于讀者在經過對作品的深刻解讀之后,能奔跑在詩人真情的原野,享受散文詩的巧妙帶來的思想上的洗禮。
生活是冰山,粗心的人只能看見露在水面的那一部分。散文詩是一條小船,在眾多觀察生活的巨輪間,依然能帶著自己的水手震撼于冰山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