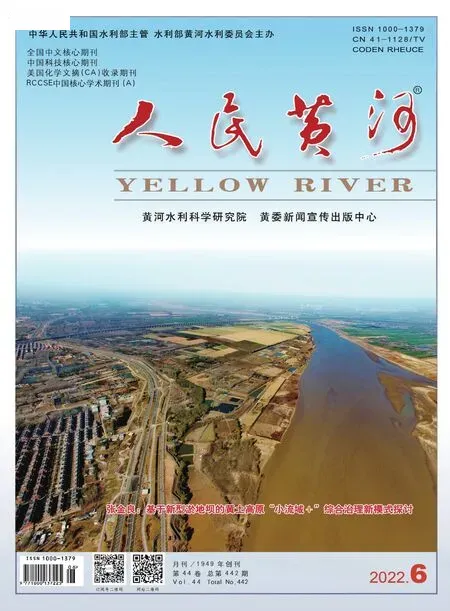黃河下游平原區典型城市“三生”國土空間特征分析
崔繼昌,郭貫成,張 輝
(1.南京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2.德州市自然資源局,山東 德州 253058)
生產、生活、生態(簡稱“三生”)空間在區域發展中承擔著不同功能。 隨著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城市建設對空間的需求日益高漲,功能空間快速重構與無序擴張并存,呈現多樣化與復雜化的特征:生態空間不斷被蠶食,生產空間粗放利用,生活與生產空間布局分離[1]。 “三生”空間優化的前提是對要素稟賦及其格局的識別。 要素稟賦是指生產單元所擁有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豐歉程度。 區域要素稟賦的不同決定了區際分工與生產交換,引起區域間要素非均衡流動,最終影響國土空間開發[2]。 “三生”空間研究常用方法可概括為歸并分類和量化測算兩類,歸并分類是基于“三生”概念對土地利用分類體系的重分類[3-5],量化測算主要是通過構建“三生”績效指標體系評價空間承載能力[6-8]。 兩類方法的共同之處在于,在研究視角方面,均以要素的功能為標準界定“三生”空間;在研究對象方面,多聚焦于省域、市域等宏觀尺度[8-9],或是特色地域的案例分析[10],缺乏對城市內部“三生”空間的關注。
自2019 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以來,黃河流域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11-12]。 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發展存在明顯差異,以河南桃花峪為分界點,至山東東營墾利區入海口,黃河下游平原區城市化發展在整個流域中處于領先地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高于流域其他地區的[12],城市“三生”空間矛盾突出。 鑒于此,通過構建“三生”國土空間分類體系,基于系統論的“要素-結構-功能”分析框架,以山東省德州市德城區12 個街道(鎮)為研究對象,借助景觀生態學方法和GIS 分析技術,利用2019 年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分析其“三生”國土空間特征,以期為優化黃河下游平原地區城市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和秩序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研究區概況。 德州市位于山東省西北部、黃河下游北岸,德州市德城區共轄7 個街道和5 個鎮,土地總面積538.31 km2,2020 年年末常住人口100.51萬,國內生產總值713.28 億元。 德州市作為第一批國家新型城鎮化試點城市之一,以農村居住社區和產業園區就地共同建設(簡稱“兩區同建”)模式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城鄉功能空間保持良性互動。
(2)數據來源。 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及空間數據來源于德州市2019 年土地變更調查數據庫,由德州市自然資源局提供。 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 21010—2017)標準,土地利用類型分為12 個一級類,73 個二級類。
2 研究方法
構建分類和評價體系是科學辨識“三生”空間格局的關鍵。 基于土地多功能性視角,在《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 21010—2017)基礎上建立包含空間和要素層的“三生”國土空間分類體系,見表1。 土地的多功能性和不可分割性決定了一種地類可能兼具多種功能,且存在主次和強弱差異。 借鑒劉繼來等[13]的分級賦分評價標準,征詢專家意見,將各地類依據其“三生”功能強弱劃分為4 個等級,其中功能強為5 分、功能中等為3 分、功能弱為1 分、功能缺失為0 分,見表1。 “三生”國土空間分類體系一級類為空間類型,設有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二級類為要素類型,分別以產業類型、生活需求和土地覆被為依據,劃分為14 個二級類。 單一地類可能兼具多種功能,對于主導功能明顯的地類,根據主導性原則劃分;對于多種功能強弱程度相近的地類,基于用地主體的主觀用地意圖劃分[4],例如耕地、園地和人工牧草地兼具生態功能,但是以持續獲取農牧產品的農業生產為主要目的,因此將其歸并于農業生產用地。

表1 “三生”國土空間分類及功能賦分
根據要素-結構-功能框架,采用多種方法對“三生”空間結構進行量化。 對于土地要素稟賦的定量描述,多樣化指數、集中化指數和組合類型可從多角度相互驗證[14]。

式中:Ai為多樣化指數,取值范圍為[0,1],其值越大,街道(鎮)i的地類多樣化程度越高;xij為街道(鎮)i地類j的面積;Bi為集中化指數,其數值越大,街道(鎮)i的地類集中化程度越高;Ii為街道(鎮)i各地類面積占研究區面積的百分比由大到小排序后的累加之和;R為假設各地類均勻分布時德城區各地類面積百分比累加之和,R為750;M為假設各地類集中分布時面積百分比的累加之和,德城區M為1 400。
對于街道(鎮)i的組合類型,首先按照各地類j的實際面積占比Tij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按照均勻分布的假設確定地類占比理想化方案,共14 種方案;然后計算每種分配方案的均勻假設分布占比T′ij與實際分布占比Tij之差的平方和,即組合系數;最后依次對比找到最小組合系數Ci,確定對應的組合類型。

對于結構區位,區位指數可對地類復雜區域的類型做出判斷:

式中:Di j為區位指數,其值大于1,則街道(鎮)i地類j相對集聚,即在整個德城區內街道(鎮)i地類j相對于其他街道(鎮)具有區位意義;fij為街道(鎮)i地類j的面積;Fj為德城區地類j的面積。
對于功能格局,采用多屬性疊置法構建“三生”功能指數[7,15],并結合空間自相關分析識別“三生”空間格局分異,空間自相關主要用于分析事物空間分布格局的依存關系,包括全局空間自相關與局部空間自相關。 全局空間自相關可探索“三生”功能值在研究區的地理關聯特征,取值范圍為[-1,1],絕對值越大空間自相關越強。 局部空間自相關反映區域內集聚狀態的具體位置,高值H-H 與低值L-L 集聚單元呈協同關系,低值與高值L-H 與高值與低值H-L 集聚單元呈異質關系。

式中:E為某街道(鎮)單項功能指數,E越大,該功能越強,在求得單項功能指數基礎上,以等權重求得“三生”綜合功能指數;Gj為地類j功能得分;Hj為地類j的面積占比。
3 結果與分析
3.1 “三生”空間要素稟賦
不同功能用地之間相互聯系,德城區各街道(鎮)“三生”空間土地要素稟賦存在差異,見表2。 多樣化指數為0.29 ~0.84。 市區各街道和袁橋鎮的多樣化指數高于全區均值0.64,“三生”用地類型較為齊全;二屯鎮、抬頭寺鎮、黃河涯鎮和趙虎鎮用地類型多樣化水平較低。 集中化指數為0.63 ~0.95,除新湖街道外,其他街道和袁橋鎮的集中化指數低于全區均值0.79,“三生”用地規模分布相對均衡,但遠郊各鎮和新湖街道集中化程度較高,功能類型相對專門、單一。 德城區“三生”用地組合類型可分為3 類:市區核心區各街道對應地類數至少為4,涵蓋生產與生活用地;德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范圍內天衢街道、宋官屯街道和袁橋鎮對應地類數為2,呈以工業生產用地、農業生產用地互為主輔的雙重主導結構;其他各鎮對應地類數為1,呈現以農業生產用地為主的單一結構類型。

表2 多樣化指數、集中化指數及組合類型
3.2 “三生”空間的結構區位
德城區各類用地在各街道(鎮)的區位指數存在差異(見表3),生產和生活用地的互動成為主要矛盾,交互結果影響著生態用地。 具體而言,新湖街道與廣川街道位于老城區核心地帶,商服業用地、城鎮居住用地和公共服務用地的區位指數明顯高于其他街道(鎮),城市功能區位優勢顯著。 城市發展過程中,伴隨著主導產業升級,人口等不斷向郊區轉移,區位條件較好的外圍區域成為建設用地拓展的首選。 長河街道是西連老城區的新城區中心地帶,非農生活用地和部分生態用地區位指數均大于1,在德城區內具有區位意義。 在城區邊緣區,運河街道、宋官屯街道、新華街道、天衢街道擺脫了單一農業生產局面,產業結構向多元化發展,工業園區集中,工業生產用地區位意義突顯。 由于位于城鄉結合地帶,內緣區城市周邊的基礎設施具有外部性,尚能夠滿足居民生活、生產需求,表現為部分街道基礎設施用地、公共服務用地等城市特征用地區位意義衰減。 外緣區的袁橋鎮農村居住用地、工業生產用地區位指數較大,功能結構呈現出過渡特征。 對于區位條件較差的趙虎鎮、抬頭寺鎮、黃河涯鎮、二屯鎮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聚居區,非農產業發展緩慢,農業生產用地和農村居住用地區位指數較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遠離市區,因此趙虎鎮表現出較完整的農村農業用地特征,農業生產用地區位指數為德城區最高值,但同時也造成了對生態用地的侵占,不存在生態用地優勢地類。

表3 區位指數
3.3 “三生”空間的功能格局
(1)空間格局特征。 借助ArcGIS 的自然斷點法將功能空間劃分為3 個等級,德城區各街道(鎮)的“三生”功能存在明顯的空間差異,見圖1。

圖1 “三生”空間分布格局
生產功能空間梯度特征明顯,生產功能指數為229.94~362.41,均值為299.31,標準差為49.11,高中低值單元數量較平衡。 高值區(326.57 ~362.41)共4個,多位于市區次核心區,且皆為以開發區為發展載體的街道;中值區(249.07 ~326.57)共4 個,為市區核心區各街道和袁橋鎮,均為城鎮化建設領先地區,其中袁橋鎮在地理空間上雖然距市區核心區較遠,但其長期發展極具特色的就地城鎮化,實現了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兼顧;低值區(229.94 ~249.07)共4 個,均位于周邊市郊鎮,耕地分布廣泛,以農業生產為主,第二、第三產業整體生產功能較弱。
生活功能指數由市區核心區向外逐漸減小,空間分布呈“中心-外圍”特征。 生活功能指數為47.03 ~318.80,均值為137.17,標準差為93.82,生活功能差異明顯,離散程度較高。 高值區(207.12~318.80)新湖街道和廣川街道作為老城區核心區,宜居性高;中值區(105.36~207.12)長河街道、新華街道和運河街道緊鄰核心區,受輻射帶動和擴散效應明顯。 低值區(47.03~105.36)集中分布于天衢街道、宋官屯街道和周邊市郊鎮,多為重要的農業、工業生產區和生態功能保護區,生活功能的保障缺乏比較優勢。
生態功能指數呈四周大、中間小的特征。 生態功能指數為7.09 ~185.94,均值為111.41,標準差為59.70,生態功能整體得分較低。 高值區(108.88 ~185.94)共5 個,均為周圍市郊鎮,生態用地集中;中值區(36.50~108.88)共5 個,多分布于市區次核心區;低值區(7.09 ~36.50)新湖街道和廣川街道土地開發強度大,市區核心區的生態功能低。
“三生” 功能空間呈圈層分布,功能指數為154.13~225.12,高值區(197.95 ~225.12)為新湖街道和廣川街道,中值區(172.21~197.95)集中在新湖和廣川街道周邊街道,低值區(154.13~172.21)位于中值區四周的市郊鎮。
(2)空間集聚特征。 為更加精確描述在地理空間上德城區的集聚程度,借助GeoDa 軟件,建立一階Queen 空間權重矩陣,計算“三生”功能空間自相關系數和莫蘭指數,見表4。 全局莫蘭指數均為正,即“三生”功能值相近的街道(鎮)趨于地理相鄰。 僅生產功能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顯著性水平p<0.1),呈極弱空間正相關趨勢,緣于各街道(鎮)均有產業發展的需求,積極布局產業用地。

表4 “三生”功能空間自相關系數和莫蘭指數
進一步采用LISA 圖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見圖2。 生產功能的H-H 集聚單元為廣川街道和長河街道,作為市區核心發揮著區域增長極作用。 生活功能的H-H 集聚單元為廣川街道,天衢街道為L-H 集聚單元,袁橋鎮為L-L 集聚單元。 在城市外圍新建產業園是中國城市主要擴張方式[1]。 依托天衢產業園發展的天衢街道工業生產功能較強,職住分離矛盾突出,生活功能低于臨近街道。 袁橋鎮“兩區同建”就地城鎮化模式是對農村、農業資源的再配置,政府通過引導非農生產要素集聚,打破原有農業為主格局,規劃構建區域新增長極。 從目前結構區位看,與周邊遠郊鎮相比,工業生產用地和城鎮居住用地區位優勢上升,農業生產用地和農村居住用地區位優勢下降,但相比市區核心區尚存在差異,農村社區為主體的生活空間尚在向城市化轉型的過渡階段。 生態功能的L-L 集聚單元為天衢街道、廣川街道和新華街道,集中連片性特征明顯。 生態功能很大程度上由生態資源分布決定,生產、生活功能的提升剝奪了生態功能發展的可能。

圖2 “三生”空間集聚格局
“三生”功能的H-H 集聚單元為廣川街道,L-H集聚單元為天衢街道,L-L 集聚單元為袁橋鎮。 “三生”功能與生活功能的集聚單元重合度較高。 袁橋鎮在空間自相關分析中呈現城市“飛地”的特征,源于其在地域上位于城區邊緣的外緣區,是發達城區與落后鄉村間的梯度地帶。 內緣區(宋官屯等街道)受市區核心區輻射帶動,是城市功能用地為主導的區域,通過極化效應吸引外緣區要素向自身集聚。 圍繞袁橋鎮地域特點布局的產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成為加工制造業和原市區落后產能轉移的承接地,重點解決附近社區村民就業問題,尚未形成足夠的集聚規模。 同時,農業與非農生產功能用地高度互斥,非農產業發展占用農用地和生態用地,吸納農村轉業人口,因此相較于其他城市腹地,農業功能要素流失,綜合因素導致袁橋鎮成為德城區“三生”功能洼地。
4 結 語
通過構建“三生”國土空間分類體系,基于“要素-結構-功能”框架,分析了2019 年德城區“三生”空間格局特征。 對于“三生”空間的土地要素稟賦,市區各街道多樣化水平相對高,集中化程度相對低,組合類型豐富程度高,且以生活用地為主,而郊區各鎮則與之相反,且用地組合逐漸過渡到以工業、農業生產用地為主。 對于“三生”空間的結構區位,農業生產用地在除袁橋鎮外的市郊鎮區位意義明顯,而市區各街道和袁橋鎮城鎮居住用地和非農生產用地區位意義明顯;農村居住用地區位優勢區為新華街道和市郊鎮,其他類型生活用地在市區各街道區位意義明顯;生態用地在除趙虎鎮外的單元均具有區位意義。 對于“三生”空間的功能格局,生產功能梯度特征明顯,高值集聚單元為城市核心區;生活功能由核心區向外逐漸減弱,高值集聚單元為廣川街道,低值集聚單元為袁橋鎮;生態功能呈現四周高、中間低的特征,低值區集中連片性明顯;“三生”功能空間呈圈層分布,且與生活功能的集聚單元重合度較高。
生態保護與生態用地空間分布及其功能強弱密切相關。 德城區地處黃河下游平原地區,各類生態用地分布集中程度低,與生產、生活用地交錯分布,生態空間不具備“全域覆蓋”“依山傍水”的特征[7,10]。 缺乏山脈、湖泊等天然屏障,迫于產業發展的現實壓力,集中連片的生產、生活用地蠶食生態功能地類,破碎的生態空間加劇生態安全破壞的可能。 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地區城鎮化發展僅僅強調生態空間的單一保護遠遠不夠,應積極探索生態空間的可持續利用,在對邊界進行控制基礎上,重視內部結構和功能的連續性與完整性,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