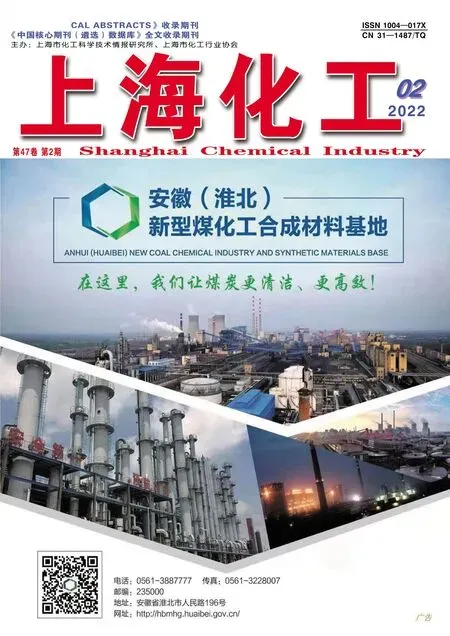上海化工產業的發展與低碳時代城市競爭力的塑造
孫建國
上海化學工業區發展有限公司(上海 201507)
2021年9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1](以下簡稱《意見》)出臺。《意見》指出,碳達峰、碳中和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以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引領。
這充分說明,碳達峰、碳中和不僅僅是溫室氣體減排的技術問題,更是一場對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所建立的經濟社會發展邏輯、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全球經濟體系將圍繞碳價值鏈的構建發生解構和重構,一場不亞于工業革命的產業革命正在發生,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2021年上海市委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抓緊部署綠色低碳賽道”,積極地把綠色低碳發展定位為重要的發展機遇。但是,如何布局綠色低碳賽道,目前上海市尚未出臺明確規劃。在2022年1月發布的《2022年上海市擴大有效投資穩定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有關于“加快推動能源綠色低碳發展”的表述:出臺新一輪可再生能源、充換電設施扶持政策,推動杭州灣海域海上風電項目全面開發,加快各行業領域“光伏+”綜合開發利用。制定出臺并推進落實碳達峰碳中和實施意見及配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綠色低碳新賽道。具體發展方向僅涉及新能源,其他發展方向有待“落實碳達峰碳中和實施意見及配套政策措施”的出臺。
從原理上來說,要實現低碳發展,主要需從兩個維度著力:一個是少用碳,即減少含碳化石能源的使用,新能源的發展主要貢獻于這一方面;另一個是少排碳,即在使用含碳化石能源的同時減少碳排放。本課題主要從發揮好上海化工產業優勢,“用好碳、不排碳”,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并從在綠色低碳新賽道上確立上海城市競爭力的角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1 化工與減碳
一般意義上,化工行業被認為是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在討論“綠色低碳”發展的時候,人們往往關注化工行業的消極作用,而容易忽視其積極作用。事實上,就二氧化碳排放貢獻率(見表1)來說,化工行業(行業代碼26,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占比為1.69%,即使加上行業代碼2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總占比也僅為3.5%左右[根據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中國分部門核算碳排放清單1997—2019”][2]。通過行業用電量占比結合行業代碼44(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對化工行業消耗的電力、熱力等能源帶來的間接排放進行估算,其占比約為2.97%。可見,化工行業在全社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直接和間接合計)不到5%。

表1 化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貢獻率%
與此相對,在今后全社會的碳達峰、碳中和進程中,需要化工行業發揮巨大作用。據估算,在實現碳中和過程中,化工行業對減碳的綜合貢獻率將超過1/3。
1.1 化石能源的低碳利用需要化工產業支撐
我國碳排放來源主要是化石能源的使用。一方面,根據Our World In Data提供的“分國別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排放數據(CO2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untry Profiles)”,2020年,來源于煤、石油、天然氣的碳排放在我國二氧化碳排放中占比分別為69.56%、15.11%、5.67%,3種化石能源累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達90.35%。另一方面,從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來看,2020年為15.8%;根據碳達峰行動方案,到2025年,這一比例將達到20%,到2030年為25%。考慮到我國的能源結構和能源安全,化石能源仍將是我國能源消費的主要支撐。發展可再生能源發電等非化石能源是非常重要也是當前最高效的碳減排途徑,但受到資源稟賦和產業特性限制,對化石能源的替代能力有限。在化石能源仍將在很長時期內占據重要地位的情況下,化石能源低碳利用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顯,化工產業將在其中發揮核心作用。
首先,化工產業可以實現化石能源的固碳利用。不同于能源行業主要以燃燒方式利用化石能源從而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化工行業把化石能源作為原料,其中含有的碳被固化在產品中,而并不排放到大氣中。化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來自于水、電、氣、“三廢”處理等公用工程,工藝過程產生的碳排放極其有限。因此,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要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原料用能不再納入能耗考核。
其次,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需要化工產業。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被認為是兜底的減碳技術。二氧化碳封存受制于資源條件,且封存后還存在逃逸風險,因而碳的轉化利用成為業界高度關注的研究領域。二氧化碳的轉化利用是一個化學過程,各國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把二氧化碳作為化工原料使用。在火力發電、能源化工、合成材料等產業界,已經有不少二氧化碳轉化利用技術路線在開展面向工程化的試驗,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可逐步實現產業化。鑒于化工材料的廣泛應用,二氧化碳轉化利用的前景非常廣闊。
1.2 全社會低碳發展需要化工行業提供減碳工具
2021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4]確定的十大重點任務中,多數領域和化工有關,需要化工產業提供產品和技術支撐。
一方面,化工行業為社會面的節能減排提供大量的材料支持,例如:建筑節能領域的保溫材料,常見的有聚苯板(EPS)、擠塑板(XPS)、酚醛泡沫和硬泡聚氨酯等;交通節能領域的輕量化材料,包括碳纖維及各種合成樹脂等。
另一方面,為其他行業碳減排工具(如風電、光伏、儲能等)提供所需的化工材料和特種化學品,如風葉涂料、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等光伏組件材料、聚四氟乙烯(PVDF)和碳酸二甲酯(DMC)等儲能電池材料。
同時,當前備受矚目的氫能、氨能本身就是基礎化工產品。化工副產氫氣可為燃料電池汽車等氫能應用提供可靠的氫能保障。氨作為氫的載體,在儲運方面相比氫具有巨大的優勢。氨直接作為能源用于發電、內燃機的研究和應用也在逐步推進。化工與可再生能源發電耦合生產綠氫、綠氨則是業界高度關注的未來清潔能源領域。
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碳達峰、碳中和離不開化工產業的支撐。可以說,化工產業的發展質量,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國的綠色低碳發展水平和碳達峰、碳中和進程。
上海是中國化工產業的搖籃,歷史悠久,產業基礎雄厚,人才技術優勢明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啟動上海化工區的開發建設以來,在工業化時代,以高質量的發展引領并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化工產業現代化的進程。在碳達峰、碳中和時代,上海化工產業也應有能力且有責任引領中國化工行業的產業低碳化、低碳產業化進程。為此,對上海市及上海化工產業提出建議如下。
2.1 轉變觀念,重新定位化工產業
傳統意義上,化工行業高能耗、高排放,對全社會的碳排放總量貢獻也大,容易被認為是應該限制發展的行業。但事實上,從碳減排的角度看,化工行業的貢獻率將更大。在碳達峰、碳中和時代,化工行業并不是低碳發展的攔路石,而將是碳減排的主力軍。[5]化工產業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在過去以同時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為導向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綠色低碳發展需求導向。建議上海市從城市發展戰略的高度,從推動城市綠色低碳發展和發展上海綠色低碳產業的角度,來重新界定化工產業在低碳時代的地位和作用,并推動全社會對化工產業的理性認知。
2.2 引入碳排放雙控機制,鼓勵化工產業自身減排
貫徹落實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盡快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在保障化工產業發展空間的同時,提升化工產業的綠色低碳發展水平。建立市場化機制,鼓勵企業采用生物質原料、循環再生原料、可再生能源,推動企業產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跡減量。強化政策激勵,鼓勵企業持續推進過程減排和末端處置,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工藝排放。
2.3 發展化工新材料,支持社會面節能降碳
從原來的以滿足社會生產、消費需求為導向,改為以支持全社會節能降碳為引領,推動化工新材料產業的轉型升級。鼓勵企業發展全社會節能降碳所需的新材料、新技術和解決方案,特別是建筑節能、交通節能、新能源、儲能等領域所需的各類化工材料。
2.4 發展氫能等無碳能源,推動能源消費低碳化
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耦合電解水制氫(“綠氫”)受資源局限且成本高企的情況下,根據國家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計劃要求,立足上海產業實際,鼓勵采用富氫原料(包括甲烷、乙烷、丙烷等)發展新材料產業,利用副產氫氣(“藍氫”)發展上海氫能產業,同時副產的部分二氧化碳可捕集利用(如煤制合成氣,可以采用同樣路徑實現煤炭的低碳利用)。此外,鑒于氫的理化特性,同時關注、評估氨作為氫能載體和作為氨能利用的可行性。
2.5 發展循環經濟,推動能源和化工材料的循環利用
除了在化工園區和化工產業基地內部進一步推動水、熱能等循環利用,以及對副產品乃至廢料的“吃干榨盡”(完全利用)外,推動全社會的大循環建設,支持企業推動合成材料化學回收技術產業化,開發“城市礦產”,使回收的合成樹脂等化工材料成為再次生產化工產品的原料,部分實現對原油等一次原料的替代,從而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
2.6 發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技術,推動能源和工業領域實現“用碳不排碳”
把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產業定位為上海市戰略性重點發展產業,鼓勵企業創新引領,發展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技術。強化政策激勵,推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技術的工程化、市場化。加強跨行業協同,推進能源與化工產業的深度融合,開展發電行業二氧化碳的化工轉化利用示范。在推進上海“雙碳”工作的同時,打造上海市產業在全國乃至世界二氧化碳減排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2.7 發揮上海“五個中心”優勢,構建“碳價值鏈”,打造新低碳經濟
傳統產業經濟圍繞人流、物流、資金流做文章。低碳時代,需要圍繞“碳流”重構產業體系,圍繞“碳價值鏈”打造新經濟體系。上海應發揮“五個中心”所具有的金融、貿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等優勢,打通化工產業等實體經濟和金融、數字等虛擬經濟的界限,打造能源、制造、環保、金融、數字等產業高度融合的新低碳經濟。
3 結語
綜上所述,化石能源用得好,可以實現低碳利用;化工產業發展得好,可以為全社會的低碳發展提供動力。“雙碳”目標對傳統發展模式是約束和挑戰,但同時也是打造新低碳經濟、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機遇和動力。上海應在這場深刻的變革中順勢而動,在實現產業低碳化發展的同時,發揮好自身產業優勢,加速推進低碳產業化,發展低碳產業鏈,打造低碳時代的城市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