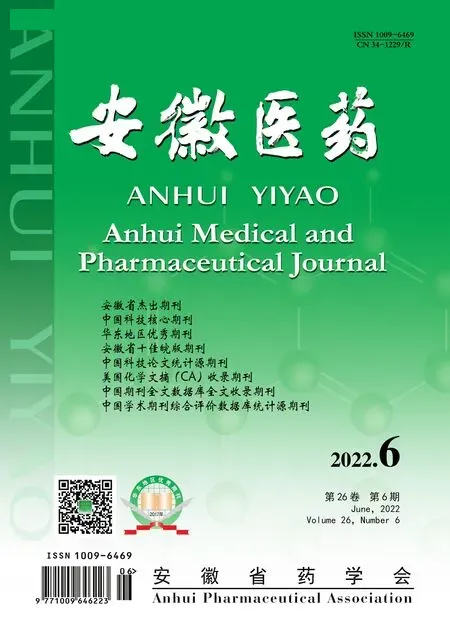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炎性蛋白水平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預測價值分析
鄭桂蓮,耿曉慧,張莎莎,王茜,高文香
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DVT)是全膝關節置換術后的常見并發癥之一,若無任何形式的預防措施,DVT的發生率高達50%~60%,可能誘發肺栓塞等,威脅病人生命安全,因此早期識別DVT的危險因素,并預測DVT發生風險意義重大。動物學研究表明,給予肽酰基精氨酸脫亞氨酶4破壞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NETs),可降低動脈損傷小鼠動脈內膜損傷的程度與急性血栓并發癥的發生,提示NETs與急性血栓類疾病的發生有關[1]。C反應蛋白(CRP)、巨噬細胞炎性蛋白1α(MIP-1α)是兩種炎性蛋白[2]。根據以往資料,低CRP與高CRP病人外周血脂蛋白相關凝血抑制物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CRP與凝血功能有關,而MIP-1α被證實與糖尿病微血管病變、血栓形成密切相關[3-4]。但NETs、CRP、MIP-1α在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中的研究較少。基于此,本研究首次探討NETs、CRP、MIP-1α對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預測價值,旨在為臨床提供參考依據,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河南省洛陽正骨醫院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110例,根據是否伴有DVT分為觀察組36例(DVT病人)及對照組74例(無DVT病人)。所有病人術后均出現下肢疼痛、皮膚顏色異常等疑似DVT癥狀,DVT診斷標準參照中華醫學會制定的《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第二版)》[5]。確診后給予常規抗DVT治療。入組者均對該研究知情,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該研究符合《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相關要求。
1.2納入、排除標準納入標準:于該院行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觀察組符合DVT診斷標準;圍手術期無發熱等感染跡象或感染疾病;無認知功能障礙;檢測配合度良好;入組前3個月無急性腦梗死、心肌梗死。排除標準:合并白血病者;長期應用免疫調節劑及影響凝血功能藥物者;有精神病史者;術后傷口有紅腫或淺表感染者;凝血功能異常者。
1.3標本采集與檢測(1)主要試劑、儀器:低溫高速離心機、超凈工作臺(美國Thermo);低速離心機(日本KUBOTA);移液器(法國Gilson);anti-MPO monoclonal capture antibody(美國ABD Serotec);per‐oxidase substrate(ABTIS)、顯色劑(TMB)、peroxi‐dase-labeled anti-DNA monoclonal antibody(德國Ro‐hce);CRP試劑盒(艾美捷科技有限公司);MIP-1α試劑盒(上海康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兩組術前12 h均給予低分子肝素(深圳賽保爾生物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60190)100U/kg,皮下注射,術后每日皮下注射1次,100 U/kg,共注射3次。術前、術后1 d、術后3 d分別采集空腹肘部靜脈血5 mL,3 000 r/min,離心15 min,上清置入EP管中,保存于?80℃。采用MPO-DNA復合物的捕獲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NETs。96孔板中,加入75μg濃度為5 mg/L anti-MPOmonoclonal capture antibody于每孔,4℃冰箱中過夜。次日取出96孔板,棄去孔內液,加入300μL洗滌液,重復3次。加入1%牛血清白蛋白(BSA)125μL于每孔進行封閉。棄去孔內液,加入300μL洗滌液,重復3次。每孔加入20μL血清與80μL含有peroxidase-la‐beled anti-DNA monoclonal antibody的反應緩沖液(稀釋比為1∶25),室溫下,300 r/min搖96孔板2 h。棄去孔內液,加入300μL洗滌液,重復3次。加入100μL顯色劑,室溫下避光反應0.5 h,加入終止液,405 nm波長位置記錄吸光度。
(3)通過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血清CRP、MIP-1α水平。實驗開始前,各試劑均應平衡至室溫;試劑或樣品配制時,均需充分混勻,并盡量避免起泡。分別設空白孔、標準孔、待測樣品孔。空白孔加標準品&樣品稀釋液100μL,余孔分別加標準品或待測樣品100μL。給酶標板覆膜,37℃孵育90 min。棄去孔內液體,甩干,不用洗板,每孔中加入生物素化抗體工作液100μL(在使用前20 min內配制),給酶標板加上覆膜,37℃溫育1 h。棄去液體,洗板3次,每次浸泡30 s,大約350微升/孔,甩干并在吸水紙上輕拍將孔內液體拍干。每孔加酶結合物工作液(臨用前20 min內配制,避光放置)100μL,加上覆膜,37℃溫育30 min。棄去孔內液體,甩干,洗板5次。每孔加顯色劑(TMB)90μL,酶標板加上覆膜37℃避光孵育15 min。每孔加終止液50μL,終止反應,此時藍色立轉黃色。立即用酶標儀在450 nm波長測量各孔的吸光度。分別以標準品濃度為橫坐標,吸光度為縱坐標繪制標準曲線,根據樣本吸光度在曲線上計算出各指標濃度。
1.4觀察指標(1)比較兩組一般資料。(2)比較兩組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3)分析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危險因素。(4)分析血清NETs、CRP、MIP-1α單獨及聯合預測下肢DVT的效能參數。
1.5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行兩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用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逐步回歸法分析DVT發生的影響因素,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及曲線下面積(AUC)分析各指標預測DVT的價值。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兩組一般資料兩組年齡、體質量指數(BMI)、合并內科疾病比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一般資料比較
2.2兩組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觀察組術后1 d、術后3 d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s

表2 兩組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s
注:NETs為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CRP為C反應蛋白,MIP-1α為巨噬細胞炎性蛋白1α。
組別對照組術前術后1 d術后3 d觀察組術前術后1 d術后3 d組間t,P值術前術后1 d術后3 d例數74 36 NETs(吸光度)0.19±0.06 0.38±0.13 0.37±0.13 0.20±0.08 0.52±0.16 0.26±0.08 0.73,0.465 4.91,<0.001 5.47,<0.001 CRP/(mg/L)10.58±2.69 25.28±8.42 13.16±4.37 10.26±2.34 35.27±11.74 19.64±6.55 0.61,0.543 5.11,<0.001 6.16,<0.001 MIP-1α/(ng/L)10.90±2.81 26.63±8.84 15.22±5.10 11.34±3.15 38.09±12.68 21.07±7.02 0.74,0.461 5.51,<0.001 4.97,<0.001
2.3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影響因素以全膝關節置換術后是否有下肢DVT作為因變量(0=否,1=是),年齡(1=≤60歲,2=>60歲)、合并內科疾病(0=無,1=有)、BMI(1=≤24 kg/m2,2=>24 kg/m2)、術后3 d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作為自變量(多重共線性診斷結果提示術后1 d、3 d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同時術后1d由于創傷、疼痛產生的應激反應可能會對各指標變化造成較大影響,故將術后1 d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予以剔除),進行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合并內科疾病、BMI、術后3 d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是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獨立影響因素(P<0.05),見表3。

表3 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DVT)的影響因素
2.4血清NETs、CRP、MIP-1α單獨及聯合檢測對下肢DVT的預測價值術后3 d血清CRP預測下肢DVT的靈敏度最高,而術后3 d聯合檢測預測下肢DVT的特異度、準確度、約登指數和AUC值最高,見表4。

表4 各指標單獨及聯合檢測對全膝關節置換術病人術后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DVT)預測的效能參數
3 討論
全膝關節置換術后DVT發生率較高,如何防治DVT成為臨床研究的熱點與難點。劉宏煒等[6]報道指出,高齡、患有糖尿病是DVT發生的相關危險因素。該研究顯示,除以上因素外,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是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的重要影響因素,與DVT發生密切相關,可為臨床針對性篩查DVT高危人群提供參考。
NETs由活化的中性粒細胞釋放及組蛋白、中性粒細胞細胞內顆粒組成的細胞外小段DNA結構,具有抗微生物特性,在結扎小鼠下腔靜脈血栓小鼠模型外周循環中的表達高于正常小鼠[7-8]。而預先通過脫氧核糖核酸酶降解DNA成分去除NETs后,小鼠靜脈血栓形成明顯改善[9]。該研究顯示,DVT病人術后1 d、術后3 d血清NETs水平高于無DVT病人,表明NETs與DVT發生有關,調控DVT高風險人群NETs或從基因水平靶向NETs有助于預防DVT的發生。薛龍等[10]研究發現,術后NETs水平與全膝關節置換術后下肢DVT具有相關性,支持該研究結論。NETs在靜脈內皮細胞表面大量聚集之后,可啟動與內皮細胞、血小板間的反應,并結合Ⅻ因子和VWF等,促進纖維蛋白形成、紅細胞與血小板聚集,加快血液凝固,且NETs還能為靜脈血栓形成提供纖維樣骨架結構,故可影響DVT的發生[11-12],可為臨床預測DVT的發生提供量化參考。
CRP系細胞膜糖蛋白,主要由肝臟合成。鄭春蓮等[13]報道顯示,DVT病人治療前CRP較高,而治療后CRP降低,并伴有病情的改善,提示CRP與DVT有關。該研究顯示,DVT病人術后1 d、術后3 d血清CRP水平高于無DVT病人,表明CRP與DVT發生有關,調控CRP或從基因水平靶向CRP,可能為DVT的防治提供了一個潛在新思路。佟冰渡等[14]研究發現,DVT病人自術后第3天開始,CRP持續高于非DVT病人,從側面論證了該研究結論。CRP可刺激誘導機體單核細胞分泌組織因子、炎癥遞質,損傷血管內皮,介導血小板凝聚,并引起人體內皮細胞合成凝血因子,啟動凝血瀑布樣反應,從而影響DVT的發生[15-16],可為臨床預測DVT發生選取合適的指標提供參考。
MIP-1α主要由成纖維細胞、單核細胞等產生,參與炎癥反應[17-18]。注射MIP-1α抗體誘導MIP-1α的耗竭,可減小小鼠模型的血栓,提示MIP-1α可能與血栓形成有關[19]。該研究顯示,MIP-1α在DVT中表達高于無DVT病人,表明MIP-1α可影響DVT的發生,抑制MIP-1α表達有助于減少高風險人群DVT的發生。且術后3 d MIP-1α預測DVT發生的AUC達0.737,截斷值>18.57 ng/L時,靈敏度為0.667,特異度為0.730,可為臨床提供量化的參考信息。結合文獻分析,MIP-1α可趨化單核細胞、T細胞、中性粒細胞向損傷部位遷移,誘發炎癥反應與血小板在損傷部位的聚集,從而增加DVT發生風險。
現階段全膝關節置換術后DVT的評估常采用超聲檢查、凝血功能檢查等,但多在發生后方可明確,不利于DVT的預防。有研究報道,MIP-1α預測老年臥床靜脈血栓栓塞癥的AUC為0.739[20],與該研究MIP-1α的AUC相似。且該研究還發現,NETs、CRP、MIP-1α能預測DVT的發生,且在術后3 d進行三者的聯合預測具有更高的特異度、準確度、約登指數和AUC值,可防患于未然,盡早采取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以減少或避免DVT的發生,為臨床預防DVT提供客觀數據與循證支持,而選擇術后3 d各指標變化進行預測,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術后早期由于創傷引起的各指標應激性升高而導致的假陽性率升高的可能。但不足之處在于,納入樣本量較少,可能造成數據的偏倚,仍需后續增加病例數進行進一步地驗證、完善。
綜上所述,NETs、CRP、MIP-1α在全膝關節置換術后DVT病人中呈高表達,與DVT發生顯著相關,并對DVT發生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尤其是三者聯合檢測具有更高的預測效能。靶向NETs、CRP、MIP-1α可能為防治DVT提供了一個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