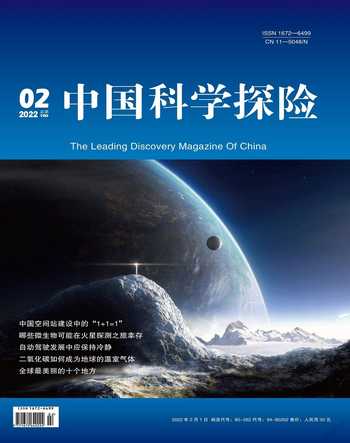中國百變邊陲城市——伊犁














伊犁因為優美的風景漸漸成為當今網紅旅游勝地。2021年春季“旅游蜂向標”大數據結果顯示,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熱度上漲了317%,成為春季國內旅游熱度漲幅最高的目的地。2021年五一黃金周,伊犁累計接待國內游客216.67萬人次,同比增長111.68%。
新疆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的地方,而且別指望能看完新疆的景色,因為每一年都不一樣。確實如此,單就伊犁就有看不完的美景,每一幀都美到令人失語。
如若錯過了吐爾根鄉杏花溝,還有被譽為“中國薰衣草之鄉”的霍城縣、油菜花和向日葵遍布的昭蘇縣、五彩斑斕花色點綴的那拉提草原……這些遠遠不夠,你永遠都看不透伊犁到底有多少張面孔,或許中國最百變的顏霸之地,就是它了。
伊犁到底有多美
都說“不到新疆不知中國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新疆的廣博毋庸置疑,幾乎每個地方都堪稱絕美。但要說新疆最受上天眷顧的地方,非伊犁莫屬。
伊犁位于新疆西北部邊陲,是全國唯一一個副省級,同時管轄地區、縣市的自治州。它得名于新疆流量最大的內陸河——伊犁河,地處天山腹地,且三面環山。
北邊屏蔽了北冰洋和西伯利亞寒流,南邊天山擋住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熱浪,因而伊犁坐山環水,是新疆最濕潤的地帶,素有“中亞濕島”和“塞外江南”的美譽。
伊犁是新疆最濕潤的地帶
毫不夸張地說,這里是西部生態資源最富饒的地方之一,既有肥沃遼闊的草原森林,又有廣袤無垠的天地河川,還有雄奇壯麗的雪峰冰川,名片樣樣拿得出手——“中國最美的草原”“中國最美的綠谷”“中國最美的森林”“薰衣草之鄉”“天馬之鄉”“蘋果之鄉”……伊犁是百變的。尤其到了花季,你根本不知道它可以變幻出多少不同的顏色。
四月春季杏花開,尤其在霍城縣西北的大西溝,你會見到一幅野生豪放派的杏花寫真,燦若云霞開遍溝內。等到五月,天山上的紅花映成了紅色花海,濃烈紅火之勢昭示著伊犁盛夏的來臨。
大西溝的花季
每年的六月到七月,是昭蘇油菜花開的時節。在昭蘇高原,能看到一望無際的向日葵和油菜花。這里有全國最大的油菜花田,就像一條條金黃色的織毯席卷著廣袤無垠的昭蘇大草原,遠處還有連綿的雪白天山和田野村莊點綴。
盛夏六月是伊犁薰衣草花季,霍城就是紫色的薰衣草之城。這里是全世界繼法國普羅旺斯、日本富良野之后的第三大薰衣草種植基地,也是我國唯一的薰衣草主產地。
時而金黃時而浪漫紫的伊犁
霍城有薰衣草主題觀光園叫“解憂公主薰衣草園”,這名起得可真妙,整個伊犁河谷都變成香薰的紫色世界,還有什么憂愁煩惱,似乎都能隨著淡淡幽香消散。
伊犁最有名的風景莫過于草原。不同于國內其他草原,伊犁的草原有種超然絕美的氣質。最名震中外的當屬那拉提草原,這里自古便是著名的牧場,河谷平展、水草豐美,草原和雪山交相輝映,如今開遍山崗的各色野花打破了山村的寧靜和祥和。
那拉提草原
素有“伊犁第一景”之稱的果子溝,以野果多而得名,果樹叢生、野花競放、峽谷回轉,怪不得古人曾賦詩贊嘆其“山水之奇,媲于桂林,崖石之怪,勝于雁巖”。
如果想欣賞未經雕琢的原始地貌,唐布拉草原或許是不錯的去處,這里喀什河穿流而過,水轉景移,錯落著高山、冰川、溝谷、山溪和湖泊。
如果喜歡雪嶺云杉綠谷就去庫爾德寧,那里有全球雪山最集中的分布區,享有“天山最美綠谷”的美譽。
最讓人稱奇的還是夏塔古道,起始于昭蘇縣的夏塔鄉境內,向南沿夏塔河谷直到溫蘇縣境內。
當你看到叢山峻嶺中一瀉千里的夏塔河,中間劃開一片遼闊的草原,隨后夏塔河再匯入煙波浩渺的特克斯河,河兩邊攤開另一片坦蕩如砥的平原天地,田園縱橫交錯,寧靜如畫。
你永遠都概括不了什么是伊犁
僅僅用“美”來概括伊犁,確實單薄了點兒。伊犁的百變還在于文化的厚度。別看伊犁地處西北邊陲,歷史上它處在陸上絲綢之路北道的要沖,是絲綢之路的重鎮。
這里有條通道連接天山南北,向東可以控制天山中部的焉耆地區,向南可以控制龜茲地區,向北越過天山連接絲綢之路北道,與蒙古高原相連,向西連接哈薩克草原,具有可四面出擊的優勢。
天山是新疆人的母親山
優越的地理環境讓伊犁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的生活之地——先秦時它是塞人牧地,西漢初年為大月氏所據,也是烏孫國的所在地,烏孫即為現代哈薩克族的祖源之一;隋唐時期為西突厥的聚集地,到了明清時期,又成了蒙古準噶爾部游牧地。
曾經的伊犁從經濟和地理上,都處于新疆的中心。清朝曾正式設立伊犁將軍一職統領新疆全省,晚清時期沙皇俄國入侵,由于這里的地形不易防守,新疆的中心才不得不從伊犁遷往烏魯木齊。
伊犁文化的厚度就在于交融。季羨林老先生曾經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遼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而這四大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也就只有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
歷代戰亂的民族遷徙、古代絲綢之路的多民族交流,讓伊犁這片地,就有哈薩克、維吾爾、回、漢、蒙古等47個民族,有“東方人種博物館”之稱。伊斯蘭文化、中亞文化、中原文化在這里交匯積淀,形成伊犁獨特而豐厚的多元文化。
這里有中國最獨特的縣城——“八卦城”特克斯。這里曾是西域最大的游牧古國——烏孫國的所在地,世界上唯一的烏孫文化和易經文化于此處交織,也是中國現存烏孫古墓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國古代有史記載遠嫁公主最多的地方。
這里的傳奇之處為人所道:整座縣城因八卦的布局而聞名,是國內唯一沒有紅綠燈的城市,且從不堵車。8條主干道環環相扣,無論走哪條路都能走到想去的地方,但交錯縱橫的小巷容易讓外鄉人迷路。
50多米的八卦觀光塔是全城唯一的C位,只要一登上塔鳥瞰觀光塔下方,青灰色的街道、綠色的草地縱橫交錯,形如八卦盤的全貌盡收眼底。
這里還有中國西部最大的陸路口岸——霍爾果斯口岸,它是中國最早向西開放的公路口岸,是古絲綢之路新北道上的重要驛站,也是面向中亞、西亞乃至歐洲距離最近的開放窗口。
霍爾果斯:中國最早向西開放的公路口岸
如今霍爾果斯已成為獨具異域風情的邊境小鎮,在這里能買到來自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的手信以及各具特色的民族工藝品,這里也將建成中國西部最大的免稅購物區。
如果要欣賞“塞外江南”的異域風情,還有厚重的歷史感,不妨到伊犁首府伊寧走一走。被稱為“西域天府”的伊寧市,在市中心六星街就彌漫著一股濃厚的混血氣質,尖頂厚墻的俄式房屋、大橡樹、東正教堂、俄羅斯陵園,處處都是中俄交融的痕跡。
伊寧彌漫著濃厚的中俄混血氣質
伊犁就是一碗熱茶,粗獷而又溫暖
如何形容伊犁的氣質?
作家畢淑敏出生在伊寧市巴彥岱鎮的一座俄式老房子里,從小母親就對她說:“你出生的地方伊寧是一座百花之城,是一座白楊之城。”在她看來,伊犁或許是那個陽光、溫潤、綠色的故鄉。
這里曾是伊寧俄羅斯人的“故鄉”,也許你走在街邊、河岸邊都能聽到伴著教堂的圣歌、手風琴聲。
如今也多了不少維吾爾族人生活的印跡,刻著民族特色的花紋門窗和種了一院子花、搭滿葡萄架的院子讓陽光都顯得柔美,不時能聽到悠長的馬蹄聲,恍惚間還以為到了哪里的田園夢境。
在艾克拜爾·米吉提的散文集《伊犁記憶》里,伊犁是一種記憶,是漫山遍野怒放的郁金香,也是密布城市的白楊樹,每家每戶庭院的各色花開。
伊犁是中國哈薩克族人口最多的城市,作為新疆唯一還在延續著游牧生活的民族,馬是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動物,甚至成了他們的信仰,因此這里被譽為“天馬之鄉”,天馬指的就是伊犁馬。
如今在天山北麓伊吾山城城西的圓盤山上,還有一尊背馱兩只水桶、揚鬃奮蹄的大理石戰馬的雕像。這座雕像是伊吾縣人民政府為紀念在伊吾40天保衛戰中做出特殊貢獻的軍功馬而塑造的。
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2、3世紀,生活在今哈薩克斯坦和中亞遼闊地區的哈薩克族先輩塞人從事畜牧業,他們大量養馬、羊、牛,且當時就有飲用馬奶的習慣。
哈薩克有句諺語“奶子是哈薩克的糧食”,加上一日三餐喝茶,他們也喜歡喝咸奶茶,一次能喝十多碗,講究喝足、喝透,喝到出汗為止。
哈薩克人以淳樸厚實、熱情好客為人所道,他們宴請賓客的禮儀也很有趣:肉熟之前,他們會將餐巾鋪好,端上包爾沙克(油果)、奶疙瘩、奶豆腐、酥油等,等到大家圍著餐巾席地而坐,主婦便蹲在壺具旁調配奶茶,喝完奶茶又換喝馬奶酒。這時主人會彈起冬不拉,唱起歌,邀請客人唱歌跳舞。金杯銀盞交錯當中,潔白的馬奶酒浸染著伊犁鮮活的氣息。
在王蒙的《淡灰色的眼珠》中,伊犁的多面被幻化成三個主人公的眼珠意象——端莊、慈祥又深不見底的淡灰色,熱情沖動,像還沒被套上籠頭的馬的烏黑色,又像天空和草地般一望無邊的藍色和綠色。伊犁這種繁復、瑰麗、包容的文化色調,王蒙稱之為“雜色”,即“雜多的統一”。
當你漫步在伊寧的大街小巷,或許會更能直觀感受到這里潤入生活的“雜色”。伊寧市有一條名聲響亮的“漢人街”,都說不到漢人街不算來過伊犁。這里車水馬龍,商貿興旺,如今它搖身一變成美味的世界——烤羊肉串、熏馬腸、面肺子、酸奶疙瘩、錫伯餅、薄皮包子……叫得上名和叫不上名的地道新疆風味,都集結于此。
對于外鄉人來說,伊犁似乎更像是精神原鄉。
曾長期生活在這里,自稱是“北京-巴彥岱人”的作家王蒙回憶起伊犁時光,說雖然苦澀,但整體仍是陽光——“新疆文化對于逆境者是一件御寒的袷袢,是一碗熱茶”。
伊犁于他,或許就是那碗熱茶,粗獷而又溫柔。他回憶起來:“我們幾個男性,穿著短褲,拍著肚皮,喝著熱茶,吹著海風,談天說地,海闊天空,邊寫邊看,邊說邊罵,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輕輕幾筆勾勒,似乎人生有再多的苦,都能被伊犁的博大和遼闊給熨帖,畢竟誰不貪得那一草一木的深情?
伊犁是否也是治愈你的那碗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