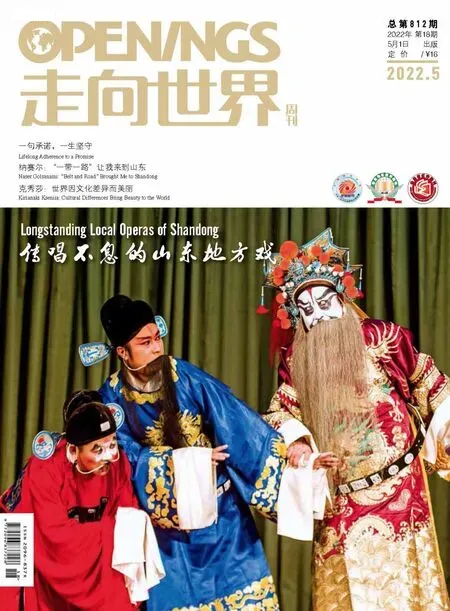窯變刻瓷,工巧合一
文/胡建昌
所謂“窯變”,主要是指瓷器在燒制過程中,由于窯內(nèi)溫度變化而導(dǎo)致其釉面發(fā)生的不確定性變化。
古人對窯變的定義與分類相對比較寬泛,有的甚至將瓷器器型的形狀也包括在內(nèi)。例如《稗史匯編》認(rèn)為“瓷有同是一質(zhì),遂成異質(zhì),同是一色,遂成異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謂窯變。”《陶成紀(jì)事碑記》則將“人巧”所為的釉色變化,增加進(jìn)了窯變之中。《景德鎮(zhèn)陶錄》也認(rèn)為“窯變之器有三,二為天工,一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則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態(tài),直名之曰窯變,殊數(shù)見不鮮耳。”對于這種具體的“人巧”之法,《南窯筆記》記載道:“法用白釉為底,外加釉里紅元子少許,罩以玻璃紅寶石晶料為釉,涂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顏色變幻,聽其自然,而非有意預(yù)定為某色也。其覆火數(shù)次成者,其色愈佳。”這種“人巧”的穿變往往不是一種特定的色彩設(shè)計理念。



淄博,地處中國華東地區(qū),不但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陶瓷之都,上千年的制陶歷史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陶瓷人。說起淄博的陶瓷藝術(shù),首推的便是刻瓷。
刻瓷是用特制刀具對瓷器、瓷板等的釉面進(jìn)行刻畫、鑿鐫而產(chǎn)生各種各樣圖案的一門藝術(shù),也指在瓷器上雕刻而成的造型工藝品。清代光緒年間,北京的書畫名家鄧石如、華法在瓷器上自寫自畫自刻,促進(jìn)了刻瓷藝術(shù)的發(fā)展。華法的刻瓷以工筆為主,以刀代筆,運用自如,并傳授給北京的朱友麟、陳智光等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農(nóng)工商部工藝局學(xué)堂設(shè)有鐫瓷科,朱友麟為第一屆畢業(yè)生,后留校任教,其傳世作品有《一品紅》等。到了20世紀(jì),北京、上海、淄博、青島、南京等地均有刻瓷藝術(shù)工作者和愛好者。
刻瓷所用的特制刀具用高碳鋼和金剛石制成,頂端呈錐狀,便于在堅硬的瓷器表面雕刻。在瓷器上書寫或者繪畫時,要依據(jù)瓷器上的畫稿用鉆刀雕刻,使畫面形成點、線、面的布局;上色時可根據(jù)畫面效果進(jìn)行濃淡干濕、深淺變化的處理,形成獨特的陶瓷語言表達(dá)方式。
刻瓷通常是在瓷盤、瓷板、瓷瓶上進(jìn)行藝術(shù)裝飾。近年來,在淄博刻瓷藝術(shù)大師及筆者的不懈努力下,以窯變刻瓷為主要表現(xiàn)形式的刻瓷作品多次在國家級和省級大賽中取得金獎、特等獎等優(yōu)異成績。
窯變刻瓷作品形態(tài)美觀,或如燦爛云霞,或如春花爛漫,或如云海松濤,或如牧歌田園。在這樣的畫面上構(gòu)思創(chuàng)作,須有畫龍點睛之筆,如果沒有精致的構(gòu)思、巧妙的設(shè)計,反倒成了畫蛇添足。這一過程,是成功與否的關(guān)鍵。



筆者創(chuàng)作的《山間情趣》系列作品主要采用點、線、面的構(gòu)圖,搭配技巧手法創(chuàng)作完成。當(dāng)花釉盤燒制而成后,筆者思考了許久,經(jīng)常一人到山中寫生,尋找靈感。傍晚時分,夕陽西下,彩霞滿天,見此景象,筆者兒時的記憶一幕幕浮現(xiàn)在眼前,似乎瞬間找到了想要的東西。返回工作室挑燈夜戰(zhàn),經(jīng)一夜時間完成畫面中大的結(jié)構(gòu)和布局框架,接下來就是很長時間的細(xì)細(xì)調(diào)整和整理。
從事窯變刻瓷設(shè)計多年,筆者常常思考如何在繼承傳統(tǒng)優(yōu)秀技藝的同時,讓刻瓷藝術(shù)不斷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傳承與創(chuàng)新是每一位藝術(shù)工作者的使命和夢想,只有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不斷創(chuàng)新才能把自己熱愛的刻瓷藝術(shù)傳承下去,只有時刻牢記責(zé)任和使命才能不斷前行,探索和研究更多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