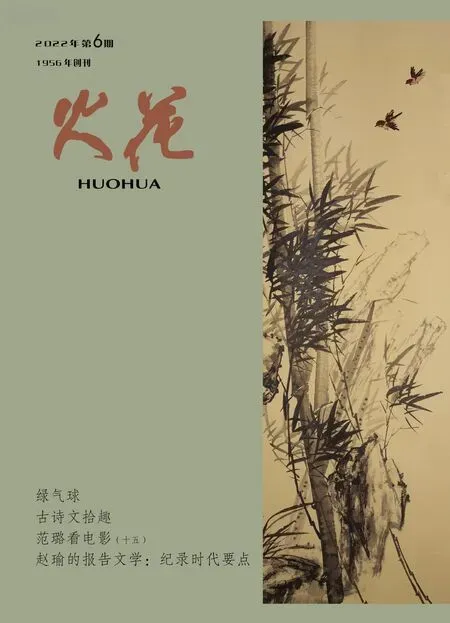古詩文拾趣
孟憲歧
汪倫的情
汪倫,黟縣人,曾任涇縣縣令,卸任后由于留戀桃花潭,將其家由黟縣遷往涇縣。
唐天寶年間,汪倫聽說大詩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陽冰家,便寫信邀請李白到家中做客。
信上說:“先生好游乎?此處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處有萬家酒店。”
李白素好飲酒,又聞有如此美景,欣然前往,卻未見信中所言勝景。
汪倫盛情款待,搬出用桃花潭水釀成的美酒與李白同飲,并笑告李白:“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無十里桃花。萬家者,乃酒店主人姓萬,并非有萬家酒店。”
李白聽后大笑不止,并不以為被汪倫愚弄,反而為汪倫盛情所感動。適逢春風桃李花開日,群山無處不飛紅,加之潭水深碧,清澈晶瑩,翠巒倒映,端得是個好去處,李白大喜。汪倫每日以美酒相待,李白樂不思蜀。
惜別之日,李白自東園古渡乘舟欲往萬村,登旱路去廬山。汪倫送李白名馬八匹、官錦十端,并在古岸閣設宴為李白餞行,拍手踏腳,唱民歌《踏歌》相送。
李白深感汪倫盛意,作《贈汪倫》詩一首:“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李白的豁達、不羈、重友,汪倫的幽默、灑脫、鐘情均為世人稱道,留下了千古佳話。
歐陽修的醉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廬陵人。北宋慶歷五年,被貶以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他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記》和《豐樂亭記》,使二亭聞名于世。
其實,在滁州為官,正是歐陽修人生的低谷。但他心胸寬闊,始終保持輕松的心態,笑對人生。他在滁州為政“寬簡”,愛民如子。在他的努力下,滁州百姓安居樂業。
歐陽修喜歡喝酒,喜歡游玩,經常帶著部下和老百姓一道游山玩水與民同樂。
貫穿《醉翁亭記》全文的主線是“樂”字,醉和樂是統一的,醉是“表象”,“樂”才是主旨,寫醉正是為了寫樂。無論是寫山,寫亭,寫水,寫人都暗喻一個“樂”字,最后破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也”。
一個醉字,妙義無窮。
看“然而禽鳥之山林而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其文也,太守也”。
醉得好,也樂得好。歐陽修真乃深藏不露的高人也!
蘇軾的孤傲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雖是大文豪,但仕途多舛,屢次放逐。
后來因與司馬光政見不同,再度被貶瓜州,與金山寺僅一江之隔。
那時,金山寺內有一法號為佛印的和尚很有名氣,聰慧過人,才氣超群。蘇軾心里頗有不服,極想與之會面一比高下。兩人見面后,蘇軾侃侃而談,三皇五帝,天文地理,治國治家,口若懸河。
佛印洗耳恭聽。
蘇軾見佛印一味點頭,并無一言,越發覺得佛印徒有虛名。暗想,此人乃墻上蘆葦山間竹筍也!
待蘇軾滔滔不絕講完,佛印呵呵一笑,問:“在先生眼里,老衲何許人也?”
蘇軾鄙夷地說:“凡夫俗子看來,爾佛教大家,其淺薄無知;我以為,不過是欺世盜名,江湖術士而已。”
佛印臉無慍色,笑容可掬,不置可否。
蘇軾覺得佛印真是不過如此,庸才也!
蘇軾興猶未盡,問佛印:“在你眼里,我如何?”
佛印答曰:“大學士飽讀詩書,橫貫古今,學富五車,修養極高,吾望塵莫及,慚愧!慚愧!”
蘇軾乘興而歸。見小妹,說佛印乃不學無術之人,并把今日和佛印所談與小妹學說一遍。
小妹嗤嗤笑:“佛印高于你了!”蘇軾驚問:“何故?”小妹說:“你因貶損而獲贊譽,誰高?”蘇軾思忖再三,點頭稱是。
后,蘇軾與佛印成為莫逆之交。
佛印的風趣
佛印,法名了元,字覺老,俗姓林,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人。他是北宋云門宗的高僧,自幼學習儒家經典,三歲能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能誦詩三千首,被稱為神童。
佛印與蘇軾交情深厚。有一天,蘇軾和佛印乘船游覽瘦西湖,佛印大師突然拿出一把提有東坡居士詩詞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聲道:“水流東坡詩(尸)!”當時蘇軾愣了一下,但很快笑指著河岸上正在啃骨頭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
那日,蘇軾閑來無事,便去金山寺拜訪佛印,沒料到佛印不在,一個小和尚前來開門,蘇軾大聲問道:“禿驢何在?”小和尚淡淡一笑,用手一指東面山坡上的佛印答:“東坡吃草!”蘇軾愕然問:“誰言?”小和尚答:“師傅言!”蘇軾大笑而去。
佛印雖是出家人,卻頓頓不避酒肉。這日,佛印煎了魚下酒,正巧蘇軾登門來訪。佛印急忙把魚藏在大磬(木魚)之下。蘇軾早已聞到魚香,進門不見,心里一轉,計上心來,故意說道:“今日來向大師請教,向陽門第春常在的下句是什么?”佛印對老友念出人所共知的舊句深感詫異,順口說出下句:“積善人家慶有余。”蘇軾撫掌大笑:“既然磬(慶)里有魚(余),那就積點善,拿來共享吧。”
杜甫與黃四娘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人,唐朝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著名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合稱“李杜”。李白史稱“詩仙”,杜甫史稱“詩圣”。
公元759年冬,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妻挈兒由隴右(今甘肅南部)入蜀,輾轉來到成都。次年春,在友人的幫助下,在成都西郊風景如畫的浣花溪畔修建一座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稱“成都草堂”。
杜甫的一生,正處在唐朝由盛轉衰的動蕩時期,與時代一樣,他的生活也動蕩不安,遭遇坎坷,仕途多舛,四處漂泊,寄人籬下,郁郁而不得志。他在成都草堂前后居住了將近四年,這四年,也是他生活較為安靜的一段難得的日子,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佳作。如《春夜喜雨》《蜀相》《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名篇。
其中,有一首《江畔獨步尋花》讓一位女人名傳千古。
這個幸福的女人就是黃四娘。
杜甫老先生在這首詩里寫到:“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呵呵,真是絕妙的好詩!黃四娘家真是一個百花園啊,到處都是鮮花,爭奇斗艷,蝶飛鳳舞,百鳥啼囀,美不勝收。通過這首詩,可想而知此時此刻杜甫的心境是歡暢的。歷經戰亂的杜甫,覓得一處棲身之所,環境優美,景色迷人,與左鄰右舍和諧相處,不為生活所累,詩興大發,該是何等高興啊!
黃四娘僅是杜甫的鄰居。
這個鄰居肯定與眾不同,黃四娘的不同之處在于,她能讓自己的小院子充滿詩情畫意,可見她的品味絕非等閑之輩。
關于黃四娘何許人也,歷來有不同說法。
其一,“伎人說”。清代人浦起龍根據詩中“戲蝶”“嬌鶯”等字眼,認為黃四娘應該是一位古代以唱歌、跳舞供人娛樂的“伎人”。后經今人考證,此說法很牽強。因為“娘”“娘子”是唐代對一般婦女的習慣稱謂,并不是對“伎人”的特有稱呼。
其二,“平民說”。宋代大文豪蘇軾認為黃四娘只是普普通通的農家婦女。如果是普通農家女,把院子里弄得如此讓杜甫贊不絕口,估計可能性也不大。
其三,“花禪說”。還有人做論文考證,黃四娘應該是“花禪”,即妓女贖身后來遁入空門做了尼姑。
當然上述觀點迄今沒有定論。
不管黃四娘為何人,但能把自家居住的環境美化到如此地步,黃四娘的生活品味肯定不低。此外,杜甫寫“花滿枝”,寫“戲蝶”,寫“嬌鶯”,孰能說他沒有贊頌小院主人呢?黃四娘一定是位貌美如花的女人。
這樣的女人,打造了這樣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杜甫的青睞,杜甫一揮筆,黃四娘便和杜甫的詩流傳千古了!
蘇軾和王弗
在文學史上,唐詩宋詞元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大文豪蘇軾,在宋詞中所占的位置幾乎無人可比。人們熟悉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是蘇軾豪放風格的經典之作,也是奠定蘇軾豪放派詞人的扛鼎之作。
蘇軾不但有豪放大氣的詞作,還有婉約細膩的詞作,最典型的莫過于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四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這首感情深摯的悼亡詞,作于宋神宗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時年蘇軾四十歲,剛任密州(今山東諸城)知州不久。
該詞是寫給妻子王弗的。
王弗(公元1039—1065年),四川眉州青神(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人,系鄉貢進士王方之女。王弗聰慧謙謹,知書達理,十六歲即與十九歲蘇軾成婚。可惜天命無常,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五月,王弗病逝,年方二十七歲。
蘇軾和王弗的愛情經歷,也正是才子佳人的幸福婚姻,有趣而令人唏噓不止。
蘇軾少時,看淡功名利祿,常逃到大山中去求仙成道,同時也在逃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蘇軾有一位姐姐叫八娘,因父母包辦,嫁給了程之才,飽受婆婆虐待而慘死,這在蘇軾的心靈埋下了重重的陰影。
也是緣分所致,王弗的家鄉有一個天然的池塘,游人一拍手,那魚兒便歡呼跳躍而至,令人歡欣鼓舞。王弗的父親在當地有些名望,想請一些青年才俊們給池塘起了名字。然起名是一,暗中為王弗擇婿是二。那時的王弗,才貌出眾,文采過人,是方圓百里男人求婚的對象。那天蘇軾也來湊熱鬧,大家說出了許多名字,王弗的父親均不滿意。當蘇軾喊出“喚魚池”時,王父欣然稱妙。躲在窗后的王弗大喜,她給出的名字也是“喚魚池”。兩人琴瑟合一,一見鐘情。
婚后二人相敬如賓,恩愛有加,享受著愛情的甜蜜。
誰知紅顏薄命,王弗竟然早逝,讓蘇軾難以釋懷。王弗病逝后,蘇軾與朝中權貴不和,被外任多年,抑郁不得志。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蘇軾睡中一夢驚醒,夜不能寐,提筆填詞,“乙卯正月二十日記夢”寫下了這首著名的悼亡詞。
全詞感情真摯,詞句無粉飾,更不假斧鑿,不事藻飾,就是這樣一首洗盡鉛華、如出天籟的小詞,九百多年來撥動了多少人的心弦,使多少人潸然淚下!
究其原因,就是此詞以深摯的真情取勝,一個“情”字就是此詞的詩魂。
王弗,獨享此詞,千古第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