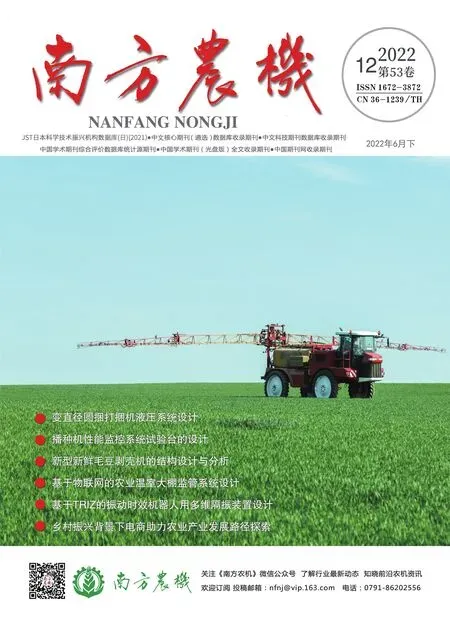鄉村治理對農村勞動力外流影響的分析*
——基于CFPS2018 的微觀證據
曾尉峰
(湖南農業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0)
0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此后,各地的鄉村治理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大學生村官、駐村干部等政策的實施,為鄉村帶來了活力,農村的新面貌逐漸展現出來。目前,農村地區缺少青壯年勞動力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有數據顯示,2016—2019 年我國農民工總規模上升了906 萬人。農村勞動力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因素,要想實現鄉村的進一步發展,吸引有能力有想法的村民主動留在鄉村是至關重要的。
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的困境體現在基層黨組織建設滯后、村民自治虛置、鄉村文化衰弱、生態環境惡化、治理目標驅動缺少空間系統性思維等方面[1-2](黃博琛,2022;李娜,2021)。針對治理困境,現有研究從民事習慣、黨領導鄉村文化、增強農民自治能力等各個方面提出鄉村治理改進方案[1](黃博琛,2022)。此外,引入不同的參與主體也能促進鄉村產業的發展,助力鄉村振興,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配置[3](文豐安,2021)。有學者提出農村勞動力轉移會對農地效率、宅基地退出行為產生影響[4-5](孫學濤,2021;張慧利,2022)。而農業勞動力的回流涉及多方因素,在經濟效益越高的家庭中,中青年女性的回流概率與回流彈性越大[6](李芳華等,2022)。
綜上,雖然我國對于鄉村治理和農村勞動力的研究比較豐富,但對于二者內在聯系的分析尚缺乏。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研究鄉村治理水平如何影響農村勞動力外流,對吸引農村人才主動在鄉就業、激發農村地區活力與內生動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理論假說和數據變量說明
1.1 理論假說
良好的鄉村治理對構建現代農業體系、發展特色農業產業、促進農民就業創業、提升居民保障水平等方面具有推動作用[7](李聰等,2021)。這不僅能為鄉村帶來新的面貌,也能為農民指明另一條出路,選擇留在家鄉就業的農民也能保證日常生活所需,這吸引更多的人主動留在農村地區。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1。
H1:良好的鄉村治理能減緩農村勞動力外出流動。
在農村社會,年齡是影響外出務工的重要因素。農村中老年勞動力由于身體素質等各項機能逐漸退化,選擇外出務工的意愿相對降低;相反,年輕人基于自身素質、心理等方面的優勢,即使良好的鄉村治理給當地帶來新的就業機會,更多的也會選擇外出務工。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2。
H2:良好的鄉村治理對農村中老年外出務工的影響更為顯著。
1.2 數據選取與變量說明
本文數據來源于2018 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項目(CFPS),數據覆蓋全國31 個省份。對數據進行清洗處理后,最終有效樣本為17 226 戶,涉及個人、家庭、社會、地區等特征數據。
本文選擇是否外出務工作為被解釋變量,反映農村勞動力外流程度。參考已有研究[7-8](李聰等,2021;羅美娟,2021),選擇對政府的評價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反映鄉村治理水平的高低。關于控制變量,本文選擇性別、年齡、社會保障問題、健康狀況等可能對外出務工產生影響的相關變量進行研究,具體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由表1 可知,“work”均值大于0.5,說明被調查對象中,農民外出流動仍是目前的主流趨勢;“eval”均值大于2.5,表示被調查村民群體認為鄉村治理水平成效并不明顯,總體治理水平有待提高;控制變量中,“soci”的平均值為5.982,說明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問題較嚴重,社會保障水平亟待提升;“medi”變量均值為0.862,該數據結構并非正態分布,對于后文的回歸結果有影響。
本文將30 歲以下、30~60 歲、60 歲以上的農民分類為青年、中年、老年,由表2 可知,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外出務工的選擇意愿逐漸降低。此外,老年人群對鄉村治理水平的評價最高,青年人次之,中年人評價最低。在家庭人數方面,本文將家庭成員數為0~3 人、4~7 人、8 人及以上的分類為小規模、中等規模、大規模,分析得出,三者“外出務工”表現出較強的異質性,其中大規模家庭中選擇外出務工的更多,規模較小的家庭對于外出務工的意愿較弱。在三種規模對于政府鄉村治理的評價中,中等規模家庭的評價較低,大規模家庭對于鄉村治理的評價相對較高。

表2 異質性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2 模型選定與實證結果分析
2.1 模型選定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是否外出務工,樣本只有1 和0 來表示是或否。因此,本文選擇適用于離散變量的二元選擇模型Logit 模型,檢驗鄉村治理對農村勞動力外出流動的影響。模型公式如下:

其中,work為被解釋變量,eval為核心解釋變量,X為控制變量;α為截距項,β1為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β2為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
2.2 基準回歸
1)在個人特征變量方面,性別對外出務工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受到家庭、性別觀念等方面的制約,其外出務工的選擇應該明顯不同于男性。王春凱(2019)[9]認為由于女性性別觀念、社會容納度等方面的提升,性別差異對外出務工的影響越來越小,與本文結論具有一致性。年齡與農民外出務工呈顯著負相關,原因在于年齡較小的人在身體素質、社會崗位接納程度等方面都具有優勢。
2)在家庭特征變量方面,家庭成員數量與農民外出務工呈顯著正相關,原因在于成員多的家庭支出成本較大,無法從鄉村社會得到所需。家庭生產規模與農民外出務工呈顯著負相關,由于土地資源稟賦較少或資金、技術不足,農民無法產生規模效益,這一部分細碎化、小規模農戶為了更高利益,選擇外出務工。農業經營性收入與農民外出務工呈顯著負相關,表明較低的農業收入會導致農民外出流動務工。
3)在社會特征變量方面,社會保障問題嚴重程度與外出務工呈顯著正相關,原因在于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并不能帶給農民安全感,為了賺取收入農民選擇外出務工,說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有待完善。醫療保險與農民外出務工呈顯著正相關,該變量取值并非正態分布,導致回歸估計有偏誤,醫保對于外出務工的影響有待商榷。
4)關于地區特征變量方面,選擇地方人均GDP增長率作為控制變量引入模型回歸,地區經濟因素對于農民外出務工影響并不顯著。基于CFPS 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省級層面進行人均GDP 增長率的統計,并未精確到農戶的村級單位,這一部分的實證有待后續完善。
3 進一步研究
3.1 穩健性檢驗
為了避免變量選取有誤對回歸模型造成影響,本文采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對干部的信任度”變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地區鄉村治理水平,因此用該變量替換“eval”引入模型。結果顯示,農民對干部的信任度對是否外出務工的影響系數為-0.026,且在99%的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民對干部的信任度越低,選擇外出務工的農民越多。該檢驗與基準回歸的結論基本一致,說明結果是穩健的。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3.2 異質性分析
根據受訪者的不同,本文從年齡差異、家庭成員規模差異兩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為政府針對具體特征人群制定不同的措施提供政策性參考。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異質性分析
1)對不同年齡的異質性檢驗。研究表明,青年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鄉村治理對中老年外出務工的影響依舊顯著。原因是影響青年外出務工的主要因素并非鄉村治理水平,青年人不用養育家庭,加之身體素質較好,隨著知識水平得到提升,更愿意外出打拼。而中老年人更多考慮社會保障,在鄉村治理有所好轉、農村各方面逐漸完善的前提下,中老年人外出務工的意愿降低。綜上,鄉村治理水平對于中老年外出務工的影響更為顯著,假說H2得以驗證。
2)對不同家庭人數的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鄉村治理水平對于中小規模家庭外出務工的影響較為顯著,大規模家庭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原因在于,中小規模家庭所承受的壓力較小,在鄉村治理水平得到改善的條件下,在農村就能保證家庭基本收支;而大規模家庭在現有條件下,即使鄉村治理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依舊無法在鄉村獲得保證家庭基本所需。因此,鄉村治理對農民外出流動的影響在中小規模家庭中更為顯著。
4 結論與啟示
隨著農村地區勞動力外出流動規模越來越大,如何激發鄉村活力,讓農村地區產生內生發展動力是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從鄉村治理的視角,研究良好的鄉村治理是否能吸引農民主動在鄉就業[10-11]。結論如下:1)良好的鄉村治理能有效減緩農村勞動力外出流動;2)鄉村治理水平對于農民外出務工的影響在中老年人群中更為顯著;3)鄉村治理水平對農村勞動力外流的影響在中小規模家庭中更為顯著。
鑒于此,得到以下啟示:1)政府要加強鄉村治理措施在吸引勞動力在鄉就業中的效果,加強農村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如農村水利建設、道路建設、廁所改革等,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培養一批合格的村級領導隊伍,提高鄉村治理水平;2)在農村地區引進具有活力的新興產業,促進三產融合,鄉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對年輕人的影響并不顯著,而鄉村振興更需要具有創造性與活力的年輕人,引進新興產業能吸引更多年輕人的目光;3)鄉村治理措施的制定與執行要考慮到家庭成員特征的不同,對于成員較多的家庭提供力度更大的社會保障扶持;4)加大農村土地平整與土地流轉力度,擴大土地的規模效應,使更多有一定規模的農戶主動留在農村地區,為廣大鄉村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