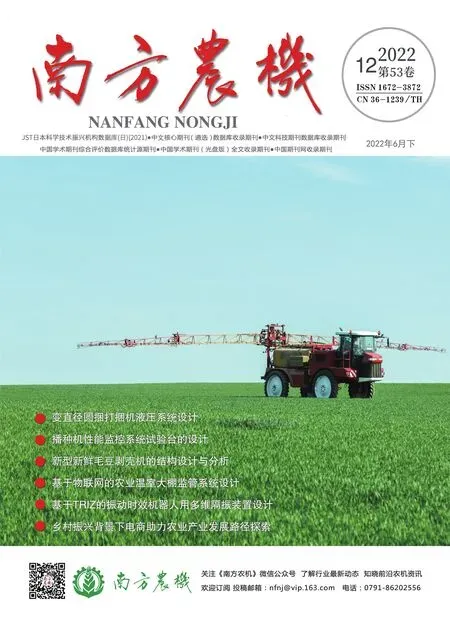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研究
——基于16 個州市的面板數據
韋仕濤 , 李 皎 , 馮 韜
(云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201)
0 引言
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進入了新階段,意味著現階段的農業發展不再限于追求種養加銷模式,而是要實現向多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轉變。2022 年中央1 號文件指出,要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持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要繼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豐富農村經濟業態,拓展農民增收空間。在我國農業農村進入了新發展模式的現實背景下,推動農村產業融合發展不僅是提升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關鍵舉措,更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增加農民多元收入的重要途徑[1]。農民增收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黨和政府關注的重點,2021 年2月頒布的《云南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第十六篇指出,要持續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優先目標。在強農惠農的政策支持下,2011—2020 年云南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為10.64%,與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相比高出2.11%。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011 年的3.47 降至2020 年的2.92,但2020 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絕對差值相比2011 年增加了11 872 元,城鄉收入差距依舊明顯,云南省提升農民收入水平的任務仍然艱巨。因此,深入探討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對增加云南省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有著重要的意義。
現有文獻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及增收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1)對農村產業融合與農民收入的內在邏輯和影響機理進行了探討。如郭軍等(2019)通過對河南省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案例進行分析,得出農村一二三產業可以通過產業整合、產業延伸、產業交叉、技術滲透等多種模式的融合來影響農民收入[2];李乾等(2018)基于實地調研得知,當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主要通過勞動力、土地、資金及產品等促進農民增收,且二者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互促關系[3];李姣媛等(2020)通過實地調研數據評估了三產融合對農戶收入的影響效應,研究認為參與三產融合能使農戶家庭人均經營性收入得到顯著提升[4]。2)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實證研究檢驗了農村產業融合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王麗納等(2019)和譚燕芝等(2021)基于省域面板數據,在構建了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分別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實證考察了中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增收的影響[5-6];陳湘滿等(2022)則采用了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分析,研究認為我國農村產業融合對農村居民收入影響呈現空間正相關性[7];齊文浩等(2021)根據入戶調研數據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檢驗了產業融合與農戶收入之間的關系,認為農村產業融合可以提高不同收入水平農戶的收入,不僅有利于低收入水平農戶收入的增加,而且有助于縮小其與高收入水平農戶的收入差距[8]。
盡管現有研究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增收效應進行了大量的計量分析和論述,然而大多數研究的經驗證據集中于我國省級層面和我國東部、中部的某一區域,對云南省等西部地區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指標構建、測度與農民增收效應的研究仍較為匱乏。鑒于此,本研究在參考前人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選取的基礎上,結合本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現狀,構建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指標體系并進行計算,在此基礎上進行實證檢驗,并分析2011—2020年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程度。
1 研究方法
1.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農村產業融合就是指農村第一產業和第二、第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是以農業產業為基礎,依托地方經濟資源優勢實現第二、第三產業的聯動與重組,模糊產業邊界并擴大產業范圍的現代化產業體系[9]。在現有測算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研究中,并沒有普遍接受的評價指標體系。因此,在整理已有研究中構建的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如表1 所示,保留統計穩定性相對較高的二級指標,從產業鏈延伸水平、農業多功能拓展、農業服務業融合發展、鄉村產業融合的經濟社會效益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 所示。本研究所涉及的數據均來源于2011—2020年《云南統計年鑒》。

表1 代表性研究中的農村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維度

表2 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1.2 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指數的計算
權重計算常用的方法有層次分析法(AHP)、Delphi 等,但這類分析法容易因專家的個人判斷造成主觀偏差,因此,本研究選用較為客觀的熵權法來進行賦權,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賦權的準確性和科學性。熵權法是依據所觀測數據集的信息熵特征,測算出所選取指標的離散度,然后依據離散度對指標進行客觀賦值,其計算步驟如下。
1)對所選取的數據分別通過公式(1)、公式(2)對正指標與負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假設有n 個年度來觀測,共有m 個指標,那么每個隨機變量的取值為Xij(i=1,…,n;j=1,…,m),Yij是指標準化后的數據,則標準化過程如下。
對于正指標:

對于負指標:

2)對標準化后的Yij在該指標中所占的比重為Pij進行測算:

3)計算各指標的信息熵:

4)計算各指標的差異系數:

5)計算各指標的權重:

2 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增收效應分析
2.1 變量選取
由于是分析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研究的主要變量為2011—2020 年云南省16 個州市的農民收入水平及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通過分析文獻可知,農民收入水平還受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化水平等的影響。為更全面、準確地分析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增收效應,避免因遺漏相關解釋變量而造成的內生性問題,需要將上述變量逐步加入回歸模型中,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
2.2 模型的設定
為檢驗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于地區農民收入是否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本研究在參考相關研究并結合數據可得性的基礎上,構建的基礎計量模型如下:

式中,i代表各州市;t代表年份;NSRit代表i地區t年份的農民收入;NCYit代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X代表除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外其他可能影響分析結果的變量,在本文里包括金融發展水平(NJR)、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水平(DGD)、地區生產總值(GDP)、地區開放水平(DKF)、城鎮化水平(CZH)。α表示常數項;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3 雙向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估計結果
通過Hausman 檢驗的P 值為0 可知,應拒絕隨機效應的原假設而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考慮到各州市隨時間發展的社會經濟水平差異較大,可能存在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因此,本研究選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來檢驗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 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所有模型的R2均接近1,表明估計的回歸方程與樣本觀測擬合得較好。從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在1%的水平下對農民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系數為0.128 6,即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收入農村產業融合水平每提高1%,云南省農民收入水平將會增加0.128 6%。隨著控制變量的逐步加入,發現農村產業融合對農民收入水平的回歸系數在逐漸減小,但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本研究所構建模型的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計量結果(6)可知,當同時加入所有變量后,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仍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且其系數為0.095 5。

表4 雙向固定效應面板回歸結果
從控制變量來看,觀察計量結果(2)可知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在1%的水平下與農民收入顯著正相關,其回歸系數為0.203 5,說明隨著地區固定資產的不斷增加,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如基礎設施建設等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投入越高,越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促進農民增收。從回歸結果(3)可知,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與農民收入水平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正相關,說明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加快資金的流通與融合,這對農業再生產中的要素投入和資源優化配置具有正向作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從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4)和(5)來看,在加入了地區生產總值和地區開放水平兩個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相關系數均為正且相差不大。這說明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的增收效應,同時受到農村內、外部經濟條件的影響,如生產總值和地區開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發展當地的農產品加工業,改善農產品供給,能為當地農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10-11]。城鎮化率對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呈微弱的負向作用,是由于云南省城鎮化還處于中期階段,城市的快速發展仍需農業為其提供大量的農產品、勞動力、市場等資源[12],導致大部分資源向城市富集,城鄉二元結構依舊明顯,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發展,因此不利于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4 穩健性檢驗
為了排除模型中的內生性影響并保證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性,課題組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分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檢驗:1)剔除省會城市昆明市,由于省會城市相對于其他州市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因此本研究將樣本中的昆明市剔除之后再進行回歸檢驗;2)考慮到產業融合發展到農民增收之間存在一定時滯性,同時也擔心其他控制變量也存在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對核心解釋變量和其他滯后變量均進行了滯后一期處理,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均控制了個體和時間固定效應。以上兩個檢驗內容分別如表5 中的列(1)和列(2)。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表
從穩健性檢驗的結果(1)可知,在剔除了作為省會城市的昆明市后,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回歸系數為0.101 4,與基準回歸系數相差不大。從結果(2)來看,在對所有變量進行滯后一階處理后,各項回歸系數及符號、顯著性水平均與前文基本一致,這也證明了本研究的研究結論是穩健和可信的。
5 結論及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基于云南省16 個州市2011—2020 年的面板數據,在綜合測算了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指數的基礎上,利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一步分析了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并通過穩定性檢驗進一步證實了本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研究發現,云南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對農民增收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且回歸系數為0.128 6,在增加了其他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其促進作用仍在1%的結果上顯著。同時,在剔除了昆明市以及對所有變量進行滯后一階處理后,本文通過穩健性檢驗得到的結論依舊成立。基于此,筆者建議:1)各地區應該根據發展實際,因地制宜發展和壯大農村產業。在當前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打造現代化的農村產業體系,加快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這對提高云南省農民收入水平有著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2)通過促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實現農民增收來源的多元化。要發揮好現代農業產業園和產業融合示范園等平臺的載體作用,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休閑農業,確保農民能有效實現多渠道增收。3)加強農村三大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使農村三大產業快速融合發展,規范各地區的農村市場環境,確保各地農村產業的有效參與,確保農民的參與權及收益權得到有效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