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詩中的西寧
一
我們習慣將昌耀目為被雪山草原、歷史民風、漢語奧義所召喚和挑選,從而粲然而立的“民族的大詩人”。從昌耀的作品考察,這樣的表述也是成立的。然而,昌耀畢竟不是洛爾迦、葉賽寧這樣純粹的“土地詩人”,并且也不像卞之琳、廢名那般在詞語的密林里極盡曲幽——昌耀的氣質更接近于惠特曼、郭沫若、艾青——詩人處在時代變革時期,因此,作品的時間支點是以撬動未來為目的的,方向(目光)是向前的。讀昌耀早期詩歌,盡管泥土的溫暖、草原文化剛健的氣息撲面可感,但是不難感受其詩核仍然是現代的——也就是說,一種來自時代的罡風奇妙地融燃于高大陸,那些古老的、健朗的、質樸的、明亮的事物隨之而煥發出嶄新的形象和意義。雪線之上太陽涂染于騎者的青銅色塊與漢語深處的青銅沉著,在詩人的熔煉爐里熔溶再生,成為“投向雪朝而口誦潔白之所蘊含”。
昌耀的深刻、敏銳和對于“他者”靈魂般的指認命名能力,非常人所及。除去稟賦,則起自五四以來新風的熏陶(昌耀幼年讀物可為佐證),當然更來自十三歲始自作主張離家別母投筆從戎后的一系列經歷的調度。在這樣復雜的藝術發生過程中,城市和城市所代表的性格、氣質、方向,其實是昌耀大地之詩的重要計量和準星。其間,與詩人生活和命運發生長達三四十年的扭結的西寧,無可辯駁地成為了昌耀詩歌重要的胎盤和壇城。西寧和昌耀長時間地相互浸潤、投射、互塑,終究形成一個讓人體會和深思的文化現象。
二
我注意到1955年昌耀初到西寧時表露的情緒。那時,年僅19歲的詩人被分配到青海省貿易公司任秘書。顯然,和西寧比較,這位已經在見識過多座城市、經過戰火考驗的詩人,更衷情于西寧周邊的自然風貌、民風民俗和邊地文化景觀。1956年5月,《青海文藝》創刊,昌耀的組詩《魯沙爾燈節速寫》得以刊發。翻讀那個時期昌耀的作品,感覺西寧不過是他的寄生之地,詩人始終精神飽滿地處在下鄉的準備和旅途中,好像并沒有時間和興趣指認聚焦這座位于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交接處的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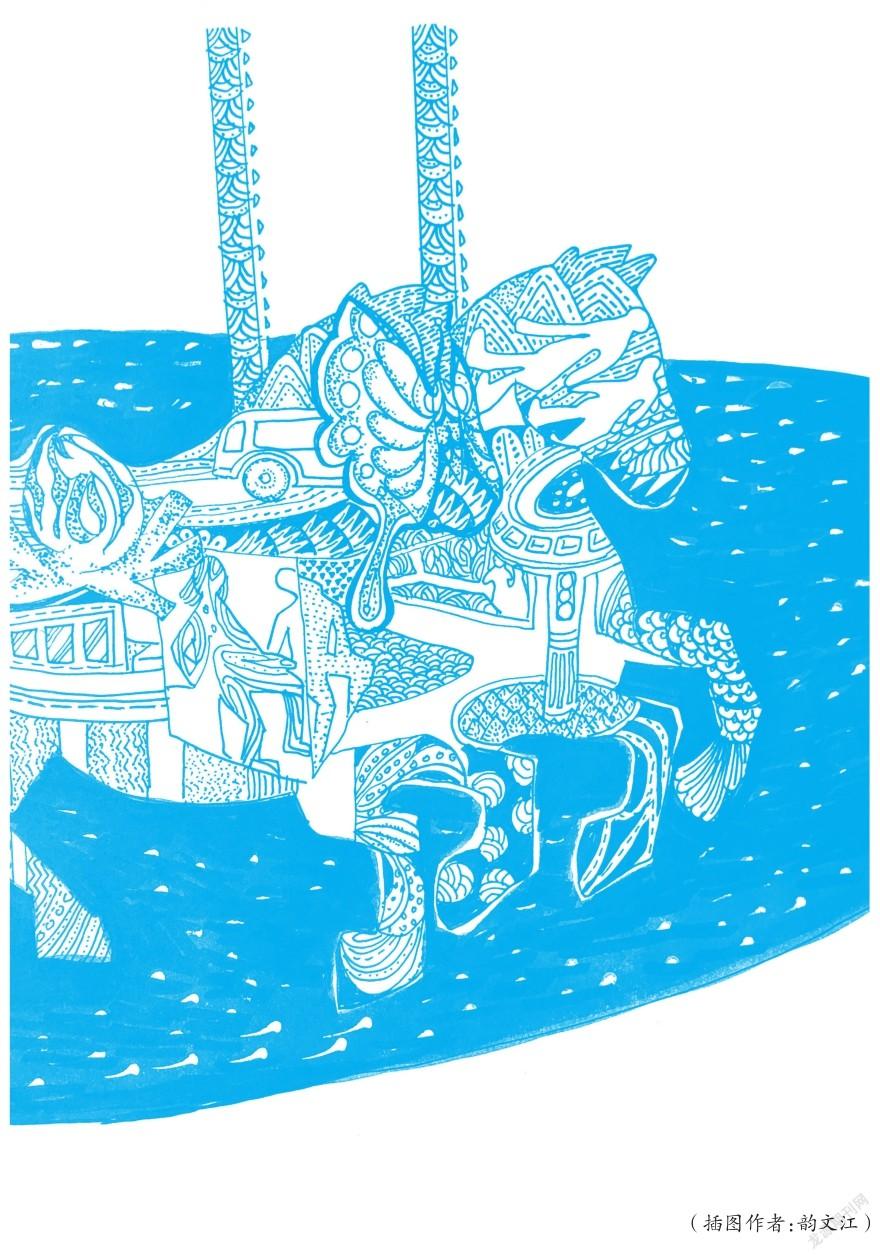
真正進入詩人視野的西寧,是詩人被湟源縣撤銷錯誤判決后,自祁連縣獨入省城準備申訴之時。經過四年人生磨難和淬火,昌耀早已從一個外來者完成了對于青海大地的高度認同,并且將自己提升到 “墾荒者”“勞動者”和美的創造者的詩意高度。在詩歌中,昌耀將自己等同幻化為那片荒土:“我躺著,開拓我吧!……(見同題詩)“我是這片土地的兒子”(《兇年逸稿》);他將自己完全地融入勞動者的行列:“我們都是年輕的漢子。/我們什么也不在乎。/我們恪守各人的崗位。/我們抬起腳丫朝前畫一個半圓,/又一聲吼叫地落在甲板,作狠命一擊。”(《水手長——渡船——我們》)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篝火,燃燒著。/我們壯實的肌體散發著奶的膻香。”(《獵戶》)與這些詩作比較,寫于1962年的《夜潭》顯示出一種復雜的人生況味:
子夜
郊原燈火像是叛離花枝的蝴蝶
隨我搭乘的長途車一路奔逐
直伴我進入睡眠迷蒙的市區
誰也不再認識我
那些高大的建筑體內流蕩光明
使我依稀恢復了幾分現代意識。
但是他們多半是我去后的新客
而詫異我紫赯的面孔透露出草原雷雨氣息。
今夜,我唱一支非聽覺所能感知的歌曲,
只唱給你——囚禁在時裝櫥窗的木制女郎……
1962.9.23.夜12時
記于西寧南大街旅邸
西寧以詩歌的主體進入昌耀的視野,是以這樣混合現實和象征、記憶與期望的狀態的,實在耐人尋味。需知,自1957年離開省城,輾轉于湟源、祁連、西寧南川等地,被命運一遍遍烘烤澆洗的昌耀,急切地希望手寫的長達兩萬多字的《甄別材料》和湟源縣發出的糾錯文書,能在省城讓他得到公正的對待。選擇以夜入城,既是出行實際,也有暫不與人面對的心理實際。“郊原燈火像是叛離花枝的彩蝶”,顯示了詩人卓越的視覺捕捉和造像能力,“叛離”二字明為后馳而去的視覺經驗,暗指自我困厄的現實處境。寓苦痛于超拔,變寒陋為華彩,是昌耀詩歌的兆象之一,于此再得應證。詩人接著寫到西寧市區是“進入睡眠迷蒙”的,并且“誰也不認識我”。這樣一座睽違日久,從各個方面都與詩人產生陌生感覺的城市,似乎預示此次詩人的申訴必然毫無結果。事實的確如此。在那個時期,人事也如“叛離花枝的彩蝶”時常迭變。昌耀甚至連遞交申訴書的領導都沒見到,又悻悻返回祁連,等待“聽取冰河在遠方發出了第一聲大笑”。然而,在祁連大野放逐的詩人盡管得到過獨屬的良宵;但是西寧“那些高大的建筑體內流蕩光明,”昌耀實際看重“使我依稀恢復了幾分現代意識”。昌耀稱自己是“歲月有意孕成的一爿琴鍵”,這爿琴鍵首先是現代意識所形制的。換句話說,中國現代詩,以及昌耀的久唱都是城市文化孕生的結果。在《夜潭》這首詩中,西寧作為現代的而非歷史的城市,第一次被昌耀凝視和反觀。“但他們多半是我去后的新客/而詫異我紫赯的面孔透出草原雷雨氣息”——來而再, 西寧此時像是昌耀命運的分水嶺,召示草原上的經歷、事物和眾神,將成為詩人恒久的精神瀑泉和柏香,等待他去創造中同現代詩虬枝吐綠的古勁新篇。這兩句詩頗有“盡是劉郎去后栽”的運思,卻少了調侃,多了健朗的氣質。短短十一行詩,像是一部濃縮的電影講述著時代和個人命運的糾扭,傾吐著詩人欲語還休的心事。最后一節只有兩行:“今夜,我唱一支非聽覺的所能感知的歌曲 /只唱給你——囚禁在時裝櫥窗的墓木制女郎……”經過詩歌第一節快速播放的鏡頭,和逐漸沉緩的思索,昌耀將最后的兩行詩予以了“莫可聽者”,予以了另外一種囚禁的形象——時裝櫥窗的木制女郎。這大概是這位年僅二十四歲卻已經歷盡滄桑而不改癡心的詩人,所找到的自我命運對應物……BE419673-19DA-4599-AD92-EA74976732BE
昌耀詩歌瓷實、充沛,這首《夜潭》閃爍著“瞳孔有鉆石的結晶”的光亮。即便不去深揣詩意,詩中流布的氣息,也是六十年前西寧的一種詩證。這是另一種光彩,比如,時裝櫥柜的木制女郎,濃烈地召示了西寧現代商業的狀況。昌耀初到青海被分配在商貿公司,詩中出現關于商業的標志意象乃理所當然。事實上,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西寧的現代化建設就急速而起。到1959年,大十字因為有郵電大樓、新華書店,尤其是百貨大樓的聳起,而成為全市、乃至全省的繁華中心。昌耀詩中的木制女郎當是大十字百貨商店櫥窗的。一別西寧,再回來時只有櫥窗女郎相望,而且,即便這櫥窗也是別后新有,于此,更覺詩人寂寞。從大十字南行,即為西寧舊時府衙寺廟商鋪所在。再往上走則為南灘,后來成為青海省公安司法單位的主要分布區。昌耀詩末題寫“記于西寧南大街旅邸”,會不會是當年的“勞改局招待所”,只能待以后考證。無論如何,西寧、南大街在昌耀生命中具有著標志性的年份顯現出來,在詩人的筆下成為具有實證價值的歷史景觀。大概意味著其后成為土伯特人“待娶的新娘”的詩人,必將選擇一個時刻榮耀回來。
三
1978年,昌耀回歸,終點是西寧。同年8月6日在中南關旅邸,詩人寫下如此迫切得有些潦草的詩行:“二十三年高原客,多驚夢——/……我更何求?但愿我的心胸作長街/……多留下些明快節奏,//君不見江河赴海,寒來暑往,時不我待,/轉眼又是春綠/秋風有意,使人著急。”全詩罕見地只是傳達心杼,而不見昌耀極為擅長的“道寓于器”的精微藝術表現力,可知詩人由“大山的囚徒”,或只能歌予“櫥窗木制女郎”的游子,而成為城市一員,甚至是城市(時代)號手的那種感奮心情。1979年8月9日至10月14日,昌耀在西寧寫下“流放四部曲”的首篇《大山的囚徒》,這首長達五百多行的詩歌,是昌耀采擷熔煉于艱難歲月的“金薔薇”,飽滿地表達了一代人的心聲。從平反昭正,回到省城開始,昌耀進入了一個創作的高峰期。青海的牧野鄉魂,通過詩人的妙筆得到不同層面的凝塑;而復出之后的新旅,比如乘坐京華地鐵等等經驗,都成為昌耀硯洗新墨的書寫。比之于五十年代詩人自謂“詩運亨通”,現在的文壇詩界寄于昌耀更多的禮遇。《大山的囚徒》迅即在《詩刊》隆重刊出,引起讀者的呼應。一系列短章長篇,正在詩人筆下呼之欲出。在這段亢奮的創作時期,西寧的具體風貌風物不再進入昌耀的詩筆——因為詩人正在應和時代的命題,“懷著開拓者最初于深井掘進的記憶 /希望的潛艇才這樣一路雷霆/呼叫著新的地平線”(《京華詩稿》)此刻的西寧安詳地、溫暖地張開雙臂,擁抱回歸的詩人噴涌那“灼耀著生命的光斑”的詩情。
詩人終于要回報西寧了。1981年年末,雖然時代賦予的強烈的節奏和韻律還在昌耀筆下持續,但是他已經開始從文化的、歷史的、精神的角度重新審讀種種詩材。昌耀用一個月時間完成了一首題為《城市》的短詩,用時之長可見題材的變換之于詩人的考驗。“顫動的城市。/顫動的/是它同時閃亮的百萬張向陽的玻璃窗葉。/是它同時熄滅的百萬張背陰的玻璃窗葉……”昌耀的城市詠唱明朗昂奮,帶著惠特曼聶魯達艾青的混響。當讀者以為這首詩將成為《劃呀,劃呀,父親們》的孿生詩篇時,卻訝然發現,詩人在第二節鍥入了另一個醒目的主題:“城市:草原的一個/壯觀的結構。/大膽的欲念。”昌耀天才地把握住了西寧這座多元文化地理交接匯合處的城市的前生后世,準確地指出其深潛的生命力,以及時代塑造的現代形象。昌耀在詩中加入了西寧人民公園標志性的游樂設施:“顫抖著的還有回轉的木馬。/——在圓形廣場,/在廣場的同一平面二度空間,/兒童的回旋木馬/與正午的車流以同一的轉速/在顫動。/就這么顫動。”將人們司空見慣的場景和物事,抽取和重塑其特征,而熔鑄成極具表現力的詩語,是昌耀高度轉喻和象征的藝術手段之一。詩人在這首詩中,予以西寧代表國家民族奮進精神的榮耀,并且進而指出“牧羊人的角笛愈來愈遠去了。/而新的城市站在值得驕傲的緯度/用鋼筋和混凝土確定自己的位置。”不知雪域高原西羌大野的歷史地理人文,無以深沉摸測昌耀詩心。同樣,不明昌耀精神的時代負重和儒者仁心,無以融洽感應詩人“凌晨七時的野嶺/獨有一輛吉普在前驅馳”的執拗,更無從為“理想者的排蕭,/吹呀 吹呀,以整個身心”的那種歌哭而靈魂激振。《城市》意味著采用藝術復眼觀照事物的詩人回到了西寧,意味過于高亢的聲調正在昌耀筆下調整。這首詩是調整自我時期的昌耀,給西寧留下的一座具有時代特征的語言雕像。
昌耀的每一次視角、筆觸、構圖的調整,都意味著其后詩藝新的邁越。果不其然,他的新詩從不同的側面塑形西寧形象、氣質和精神。《邊關:24部燈》是一首深深激動西寧人、青海人,并且在全國引起廣泛回應的佳作。近三十年后,昌耀已經是西寧驕傲的市民——他的這種驕傲無人替代。在這首詩的題記,昌耀這樣寫道:“一座規模恢宏的體育館,一座全新的兒童樂園,一座前所未有的鐵塔——24部燈,構成了80年代初古城西寧的驕傲。……我曾問一位遠方來訪的詩人可曾注意到當時尚在施工中的這座建筑。他說:“那不是傘塔嗎?”我笑了:“不,那是燈的塔。是我們24部燈!”昌耀的語氣活脫脫是個西寧的驕傲少年,耐心地、細密地、深邃地,借助矗立于五岔路口的這部燈塔,給遠方的朋友講述高大陸的姿容、氣度和連通太平洋的生命能量。
“曠古未聞的一幢鋼鐵樹直矗天宇宏觀的星海……”每每經過幾經城市改造,24部燈塔早已不在的五岔路口,我總會想起昌耀的這首詩。這首詩就是詩人給西寧立傳,給青海立傳。《邊關:24部燈》和詩騷中的那些經典的描繪和抒發一樣,跨越了具體事物和時間的阻礙,融入了文化書寫的傳統,成為青海和西寧的文化記憶。
昌耀寫作的多姿和多義,很多時候是通過對稱、對映的多重鏡像的互照顯示的。不足百行的《邊關:24部燈》是具有民族史詩涵度的一次吟哦,另一首名作《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則是西寧日常生活的精微的詩意刻畫和升華。這部作品精準的構圖、交錯的記憶,極具象征意味的場景、飽滿的情緒,疊交渲染,立體多維地展示出生活的美質和溫暖,仿佛是現代畫風傾倒于古拙的一次扭轉,是人間溫暖的一次動情的綻放。“西羌雪域。除夕。/一個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個孩子/同聲合唱著一首古歌:/——咕得爾咕,拉風匣,/鍋里煮了個羊肋巴……”昌耀寫于1982年的這首詩,先于艾軒陳丹青朱乃正何多苓等畫家,而以出色的筆墨給青藏人家繪就了生活氣息濃郁的特寫和長卷。“那一夕,九九八十一層地下室洶涌的/春潮和土伯特的古謠曲洗亮了這間/封凍的玻璃窗。我看到冰山從這紅塵崩潰,/幻變五色的杉樹枝由漫漶消融而至滴瀝。”昌耀的詩行釉質明亮,在百年新詩中未見如此情感深厚、多姿多彩的生活的贊美詩。BE419673-19DA-4599-AD92-EA74976732BE
從70年代末入城到80年代中期,西寧是昌耀完全和完整意義上的家的所在地,昌耀相應也成為了西寧和青海的詩歌名片。在這種語境下,昌耀的詩境更加廣闊邃遠多象,漸具大師氣象。寫于1985年的名作《斯人》,將詩人和西寧放置于大時空中呼應密西西比河的風雨,深沉的哲思以詩美的翼顫,格外打動人心。作家和地理地域從來都是一種互屬和互塑的關系,比如魯迅和紹興,沈從文和湘西,蕭紅和呼蘭河等等,無不如此。昌耀持久地在西寧、在青海造境塑像,二者不可剝離,從而形成了當代詩歌之于地理地域的黃金言說。
四
西寧與昌耀的互動,在詩歌中形成了多重景觀。詩人再度閱讀這座城市的時候,往往思接萬千云蒸霞蔚。西寧是詩人的瞭望點、出征地,是撬起關于西部、乃至中國宏遠歷史的族群記憶的支撐點,其詩質既有現實當量,又充滿神話美質。“西部的城。西關橋上。一年年/我看著南川河夏日里體態豐盈肥碩,/而秋后復歸清瘦蕭索。/在我傾心的塞上有一撮不化的白雪,/那卻是祁連山高潔的冰峰。/被迫西征的大月氏人曾在那里支起游蕩的穹廬。/我已幾次食言推遲我的訪問。/日久,阿力克雪原的大風/可還記得我年幼的飄發?/其實我何曾離開過那條山脈,/在收獲銅石、稞麥與雄麝之寶的夢里/我永遠是新墾地的一個磨鐮人。……”寫于1984年的《巨靈》,從西寧和西關橋起筆,思追千載目接萬里,這是昌耀又一次為腳下的大地和身處的時代作傳。他的寶石般明耀、極具生存和生活顆粒感的詩句,鑲嵌在充滿神話和歷史的追述里,構筑了立足于泥土和生命經驗,而又超越土地敘事的詩意文化景觀。中國人素有詩教傳統,昌耀的《巨靈》等作品包含地理歷史文化因素,當是西寧人和青海人頌之詠之的詩歌教材。
與《巨靈》投向歷史深處鮮活脈動的目光不同,大組詩《青藏高原的形體》是昌耀以牧野生命記憶和城市生命躍動的交織視角,細描、渲染和深度推演的藝術實踐。露宿廣場的河源子民,站在劇院前庭的草原母親,俱以城市為背景,形成了極具思辨能量和精神張力構圖,遠遠超越了那種寫實的或者夸張的風俗畫風。精神的內驅力和不懈前行的姿態與步履,長久以來都是昌耀詩歌的核爆點。西寧作為昌耀詩歌意義上下求索的起點,而連通起廣場、街道、劇院,繼而抵及古本喬尖,“將一泡童子尿澆向天邊那堆晶亮的野火”,乃至“白頭的巴顏喀拉”,那為“萬千頭牦牛的乳房所澆灌的土地”,乃至銅色河——終于看到“黃河是一株盤龍虬枝的水晶樹”,看到“黃河樹的第一個曲莖就有我們鳥巢般的家室“……在昌耀筆下,西寧是神話歷史的一部分,是走向息壤的起點, 同時也是時間和記憶的匯聚所在,并在“懷春者”的邀約中綻放奪目的新生之美。
進入90年代,昌耀漸漸收來神話思維,其詩性智慧日趨內轉。西寧相應成為急驟變化的外部世界的征象,而在詩中顯示出烘燒、逼仄、空曠、冷漠、逐利的一面。其時有變,詩人的生活一樣在發生劇烈的變動。“江湖遠人”“大街看守”“托缽苦行僧”……昌耀以這樣的自我命名定位與現實的關系。西寧或者城市,或者居所,有時是詩人造夢所在,是“古瑟古瑟當當/昴哀窕島岡桑”的幻覺、象界;有時是上演種種活劇的舞臺:“醉鬼們的歌喉/撕扯著人心,誰能對他們說教仁愛禮義/一會兒是夜歸人狠揍一扇鐵門/嗩吶終于吹得天花亂墜,陪送靈車趕往西天。”還有的時候,是詩人只能與修篁避坐郊野的片刻的靈息的溝通:“一種英雄的方式對于平庸的排拒……”居住西寧的人們,可以輕易地從昌耀詩歌中辨識出90年代的西大街,以及西郊北野;如懷有詩心,不難感受到在商品經濟呼嘯的時期,這位清癯的詩人的處境和心境。然而,昌耀畢竟是英雄血脈的傳人,他排拒的豈只是平庸,他的思慮與行動又豈僅止于排拒?在生活新的挫磨和拷問下,詩人仍然以全部的精血護持“感受白羊的一刻”,“屈指構思,一片金箔的折疊。”昌耀的詩材變形術在此期間反而迸發出強烈的輻射力,西寧城中司空見慣的一些物象隨之而被繪彩出求道尋真的寓意。“但此刻我又見他守在路邊,真是一個噩夢/那臉孔混沌一片,好似熔融的賽璐璐/獨眼空曠紅肉外翻重塑了災變現場/他咿呀作聲向行人伸帽兜乞討憐憫/人們避猶不及誰又肯于施舍/如果必要的死亡是一種壯美/那么茍活已使徒勞的拼搏失去英雄本色。”
當年,西寧西大街常有一據說傷于火災的殘疾乞者,他的被火焰摧殘的臉讓行人避之不及。這樣一個人物進入昌耀詩歌《一天》,成為了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的腳注,而“那么茍活正使徒勞的拼搏失去英雄本色”,也是詩人予以自我的讖語和心理規定。在昌耀的眼里,平凡的事物也煥發著精神征兆的氣質和氣象。“手執熱苞谷的一對小男孩在街頭追戲”/手執熱苞谷如同奧林匹亞圣火接力的火炬。/一切都在加快成熟。……”(《熱包谷》)當時,在西寧東關一帶常見的那些叫賣熱苞谷的男孩,就這樣活力四射地成為接力圣火的圣童。在昌耀的詩歌中,有關西寧的詩句散布于他的那些多種聲道的詠嘆和嘯唱中,與這座千年古城的根脈、鄉土景觀和精神遠景同構,而成為了一種思維和美感堅實的琺瑯質,如同“晴光白銀一樣耀目”。
昌耀曾說,“請將詩藝看作一種素質”。何止是素質,昌耀的“詩西寧”,歸根結底是關涉人們內心的“未可抵達的暖房”。
【作者簡介】郭建強,1971年出生于青海西寧。著有詩集《穿過》《植物園之詩》《昆侖書》,散文隨筆集《大道與別徑》等。獲青海省第六屆和第八屆文學藝術創作獎,第二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人民文學》2015年度詩歌獎,2017年《文學港》儲吉旺優秀獎,第二屆孫犁散文獎雙年獎。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西寧市作家協會主席,青海法治報總編輯。BE419673-19DA-4599-AD92-EA74976732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