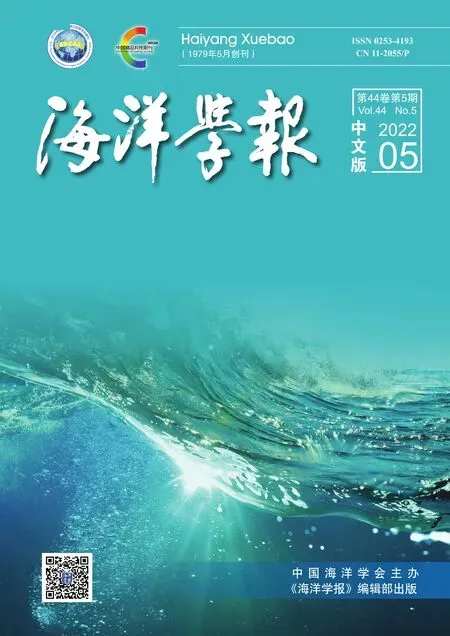波弗特海2019 年夏季海冰極端低值成因研究
魏碩,張永莉,聶紅濤*,魏皓
(1.天津大學 海洋科學與技術學院,天津 300072)
1 引言
近幾十年來北冰洋海冰覆蓋面積和范圍急劇減小[1-3],海冰厚度和海冰密集度也不斷降低,對區域氣候環境、生態系統和經濟活動均產生深遠影響[4]。波弗特海(圖1)位于西北冰洋,是北冰洋海冰變化最劇烈的邊緣海之一。波弗特海海冰融化早晚影響著浮游植物藻華,對區域的生態系統具有重要影響[5]。融冰形成的淡水增加了北冰洋淡水含量,并使波弗特流渦局部變淡[6-7]。此外,波弗特海是西北航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海冰狀況對于航道開通時間意義重大[8]。
在海冰總體減少的趨勢下,波弗特海海冰年際變化明顯。研究表明,波弗特海海冰覆蓋面積在3 月最大,9 月最小,海冰通常從5 月開始融化[9]。隨著多年冰覆蓋范圍不斷減小[6,10-11],海冰厚度不斷變薄[12],冰漂移速度加快[13],波弗特海夏季冰邊緣線快速向北退縮[14-15]。從1998 年開始,波弗特海海冰類型逐漸由多年冰向一年冰轉化[9,11,16]。1998 年也是1953 年以來波弗特海海冰的極端低值年,9 月份海冰覆蓋面積較1953-1997 年平均低39%[17];此后,2008 年又出現了極端低值[18]。2012 年夏季,波弗特海出現了31 d 的無冰期[19];僅僅4 年之后,2016 年夏季波弗特海再次出現無冰現象[20]。夏季海冰覆蓋面積的長期年際變化不僅取決于當前季節的熱力和動力貢獻,還與此前季節的熱力和動力學過程有關[21]。1998 年夏季海冰低值與北極震蕩指數的低值以及1997 年11 月至1998 年4 月持續東風和南風下多年冰不斷輸出有關[17,22]。2007 年夏季,波弗特海海冰覆蓋面積低于1998 年之后任何一個夏季[23-24],導致2007 年冬季結冰較晚,2008 年夏季開闊水域形成較早[6]。2012 年海冰極小值是因為浮冰更容易受到8 月初北極氣旋的影響[25],這是幾十年來海冰不斷減少的結果[26]。2016 年1-4 月份波弗特海海冰輸出遠高于1979-2016 年38 年的平均水平,造成了2016 年的海冰異常[20]。基于美國國家冰雪數據中心(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NSIDC)發布的海冰密集度(Sea Ice Concentration,SIC)數據,本文追蹤波弗特海海冰面積(Sea Ice Area,SIA)年際變化,發現2019 年波弗特海夏季再次出現了海冰面積極端低值。此次海冰異常是如何形成的,其與之前的海冰面積極端低值年形成機制是否相同值得探究。對海冰異常形成規律的分析,有助于進一步探究近年來北冰洋邊緣海海冰迅速減少的原因,從而對預測海冰變化提供支持。
2 數據和方法
2.1 研究區域
波弗特海是北冰洋美亞海盆的陸架邊緣海,位于美國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加拿大西北部沿岸,西側是楚科奇海,東側延伸至班克斯島,北部與加拿大海盆相連(圖1)。

圖1 研究區域Fig.1 Study area
2.2 數據來源
海冰密集度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冰雪數據中心發布的微波遙感海冰密集度數據[27](Nimbus-7 SMMR and DMSP SSM/I-SSMIS Passive Microwave Data,version 1)。該數據集由以下3 種被動微波觀測記錄,分別為Nimbus-7 衛星搭載的掃描式多通道微波輻射計(SMMR)、美國國防氣象衛星搭載的多波段微波轄射掃描儀(SSMI)和多波段微波轄射成像探測器(SSMIS)。一般來說,冬季海冰密集度誤差在5%左右,而在夏季存在融池時,誤差較大,整體在15%以內[27]。數據覆蓋范圍包括30.98°~90°N 的整個區域,空間分辨率為25km×25km,時間從1978年10月26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對于1978 月11 月1 日至1987 年7 月7 日期間隔天提供的數據,采用線性內插將數據補全。1987 年12 月2 日至1988 年1 月12 日的缺失數據不影響本文結果,暫未處理。除上述外的其余時段提供逐日數據。
海冰漂移數據來自NSIDC[28]。該數據由多套衛星遙感數據、漂流浮標數據以及再分析數據融合而成,提供每日和每周的海冰漂移矢量數據。該數據集緯向分量偏差約±0.05 cm/s,經向分量偏差在0.4~0.7 cm/s之間[28]。空間上覆蓋了29.7°~90°N 的整個區域,空間分辨率為25 km×25 km,時間從1978 年10 月25 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
海冰厚度數據來自華盛頓大學研發的PIOMAS海冰模式數據[29],PIOMAS 的數據已廣泛應用到極地海冰的研究中[30-32]。該數據空間覆蓋范圍包括45°~90°N的整個區域,模式網格點為360×120,時間從197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時間分辨率為1d。
大氣強迫數據來自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ECMWF)的第五代大氣再分析數據集ERA5,包括10 m風場、短波輻射、長波輻射、感熱通量、潛熱通量。覆蓋范圍為全球,空間分辨率為0.25°×0.25°,時間從1979 年1 月1 日至今,時間分辨率為1 h。
2.3 方法
本文海冰覆蓋面積的計算采用海冰密集度15%作為閾值[33-34],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wi為每個網格的權重系數;si為每個網格的面積;ci為每個網格的海冰密集度。當網格內海冰密集度低于15%時,則相應的權重系數為0,認為該網格區域內無冰;當網格內海冰密集度超過和等于15%時,其權重系數為1,該網格內海冰覆蓋面積為相應海冰密集度與網格面積的乘積。將區域內網格海冰面積加總得到該區域的海冰總面積。
海冰漂移數據在波弗特海東邊界(125°W)存在缺失,無法估計;西邊界(150°W)、北邊界(75°N)海冰面積通量(Fi)的計算參照下式[20]:

式中,ci為邊界上每個網格點的海冰密集度;ui為對應網格點上的海冰漂移速度;Δx為每個網格的寬度。正通量表示海冰向波弗特海區域輸入,海冰增加;負通量表示波弗特海內海冰向外輸出,海冰減少。參照Babb 等[20]采用的方法,某一段時間內波弗特海海冰面積減小量由海冰輸出量和海冰融化量組成,海冰動力輸出貢獻為兩個邊界的動力輸出量之和,海冰面積減小總量減去動力輸出貢獻即可得到由于熱力過程導致的海冰面積損失量。由于觀測數據限制,本文未考慮海冰擠壓、成脊等物理過程造成的海冰面積變化。
在任何給定的時間間隔內,面積通量(σF)的不確定性可以通過下式計算得出[35]:

式中,L為斷面寬度;σu為運動估計的標準差;Nd為估計時段的天數;Ns為每個斷面上網格點的個數。
海表面凈熱通量由感熱通量、潛熱通量、長波輻射和短波輻射組成。海表面凈熱通量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Qnet為凈熱通量;Qsw和Qlw分別代表進入海表面的太陽輻射以及海表面對外的長波輻射;Qlat和Qsen分別是潛熱通量和感熱通量。當Qlw、Qlat和Qsen為負值時,表明海洋損失熱量,Qnet和Qsw為正時,表明海洋得到熱量。
利用逐日海冰密集度和短波輻射來估計波弗特海開闊水域吸收的太陽輻射量(Fow),計算公式如下[20]:

式中,F為到達海表的短波輻射,單位為W/m2;α為開闊水域的反照率(0.07);Aow為開闊水域的面積。
3 結果與分析
3.1 2019 年海冰極端低值
波弗特海融冰季節(5-9 月)海冰覆蓋面積如圖2所示。1979-2020 年,波弗特海融冰季節海冰覆蓋面積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下降速率約為3 460 km2/a。從1998 年開始,前后兩個階段海冰覆蓋面積有著明顯的差異[16,20]。1979-1997 年,融冰季波弗特海平均海冰面積為(3.04±0.48)×105km2,下降速率并不明顯,約為1 010 km2/a。1998-2020 年,平均海冰面積為(2.26±0.64)×105km2,海冰面積減小速率十分顯著,約為3 580 km2/a。從圖2 可以看出,自波弗特海1998 年首次出現極端低值年以來,2008 年、2012 年、2016 年極端低值年相繼出現。僅在3 年之后,2019 年波弗特海再次出現極端低值。

圖2 1979-2020 年波弗特海融冰季海冰覆蓋面積年際變化Fig.2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sea ice cover in the melt season of Beaufort Sea during 1979-2020
1998-2019 年多年平均結果表明,波弗特海融冰從阿蒙森灣口開始,開闊水域逐漸向北部和西部擴展(圖3a 至圖3e)。5-6 月份,整個海域依然被海冰覆蓋,東南部以及阿蒙森灣口海冰密集度逐漸減小;直到7 月份,東南部海域逐漸出現開闊水域,開闊水域在8 月和9 月繼續向西和向北擴展。8 月,波弗特海南部已經完全成為開闊水域。通過比較發現,2019 年5 月份,整個波弗特海域,海冰密集度遠低于多年平均結果,并且低海冰密集度區域集中在波弗特海南部。6 月份,波弗特海南部已經基本完全形成開闊水域,而多年平均結果南部依然被海冰覆蓋。事實上,從逐日海冰密集度數據可以看出,2019 年5 月16 日開始,波弗特海東南部已經開始出現開闊水域;5 月22 日,西南部也出現開闊水域。7 月,多年平均結果顯示開闊水域還僅僅存在于波弗特海東南部,而2019 年除東北部外,西部大部分區域已經沒有海冰。8-9 月份,海冰逐漸減少,并且主要集中在波弗特海東北部地區(圖3f 至圖3j)。2019 年波弗特海海冰密集度與多年平均對比結果表明融冰季節波弗特海絕大多數區域都小于多年平均結果(圖3k 至圖3o)。

圖3 1998-2019 年多年平均以及2019 年融冰季海冰密集度Fig.3 Sea ice concentration in the melt season of multi-year average of 1998-2019 and 2019
3.2 前秋與前冬季節海冰變化
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2019 年波弗特海海冰的極端低值?前人研究結果表明,融冰季海冰覆蓋的情況不僅與當前季節有關,還需考慮前秋和前冬季節的海冰狀況[20-21]。因此,為了便于比較,參照前人的劃分方法將前一年10-12 月份定義為前秋季節,所在年1-4 月份定義為前冬季節,5-9 月份為融冰季節[21]。1998-2019 年多年平均結果(圖4a)表明,前秋季節波弗特海完全被海冰覆蓋,高海冰密集度區域集中在波弗特海北部;而2019 年則集中在波弗特海中部和東部地區,除了西北部邊緣海冰密集度小于多年平均,大部分地區海冰密集度高于多年平均結果(圖4d,圖4g)。前冬季節,整個海域依然被海冰覆蓋,東南部區域海冰密集度略小于其他區域。2019 年東南部與多年平均結果相比略小,但整體差異不大(圖4b,圖4e,圖4h)。然而,在融冰季節,不論是海冰覆蓋區域還是海冰密集度,2019 年與多年平均結果都有很大差異(圖4c,圖4f,圖4i)。

圖4 1998-2019 年多年平均以及2019 年前秋、前冬、融冰季海冰密集度Fig.4 Sea ice concentration in the preceding fall,preceding winter,melt season of multi-year average of 1998-2019 and 2019
按照前文面積通量計算方法,2019 年前秋、前冬以及融冰季北邊界和西邊界海冰面積通量及誤差如表1 所示,可見誤差可以忽略。圖5 展示了1998-2019 年前秋、前冬以及融冰季節海冰面積總變化量(ΔSIAtotal)、動力輸出貢獻(ΔSIAdynamic)、熱力融化貢獻(ΔSIAthermal)以及每個階段末波弗特海剩余的海冰總面積。在所有年份中,熱力過程在前秋季節促使海冰增加,在融冰季節使得海冰減少。雖然2019 年前秋季節海冰面積增加較少,但是2018 年9 月底波弗特海東部存在大量海冰,海冰面積為1.77×105km2,遠高于1998-2019 年平均值1.13×105km2。2019 年前秋季節末,海冰面積為4.71×105km2,略高于1998-2019 年平均值4.67×105km2。2019 年前冬季節,動力輸運為2.18×105km2,僅次于2016 年,遠高于1998-2019 年平均值1.66×105km2。但2019 年熱力貢獻達到1998 年以來最高值,使前冬季節海冰增加1.96×105km2,遠遠高于平均值0.68×105km2,因此,前冬季節海冰僅僅減小0.23×105km2。2019 年前冬季節末海冰面積為4.50×105km2,與1998-2019年平均值4.49×105km2相當。這與1998 年和2016 年極端低值年不同,1998 年和2016 年前冬季節海冰面積減少分別為0.73×105km2和1.58×105km2,季節末海冰覆蓋面積分別為4.07×105km2和3.25×105km2,研究指出前冬季節海冰減少是造成1998 年和2016 年極端年份的主要原因[17,20-21]。2019 年前秋和前冬季節與多年平均結果相當,前秋和前冬季節的海冰狀況不是造成2019 年海冰異常的關鍵因素。

表1 2019 年前秋、前冬以及融冰季節北邊界、西邊界面積通量及計算誤差(括號內為誤差)Table 1 Ice transport and the uncertainty across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gates of 2019 in the preceding fall,preceding winter and melt season (the uncertainty is in brackets)

圖5 1998-2019 年前秋(a)、前冬(b)以及融冰季節(c)內海冰面積總變化量(ΔSIAtotal)、動力輸出貢獻(ΔSIAdynamic)和熱力融化貢獻(ΔSIAthermal)Fig.5 Total variation (ΔSIAtotal),dynamic contribution(ΔSIAdynamic),and thermal contribution (ΔSIAthermal) of sea ice area in the preceding fall (a),preceding winter (b),melt season (c) of 1998-2019
3.3 融冰季動力熱力貢獻
2019 年融冰季海冰面積減小量約為3.75×105km2,而5 月份海冰面積減小為2.33×105km2,占融冰季內海冰面積減小量的62%,另外38%海冰面積減小發生在6-9 月,其中動力輸運使波弗特海海冰面積增加0.85×105km2,熱力融化減小2.27×105km2。2019 年5 月份海冰面積損失是1998-2019 年平均態的3.3 倍,是1998 年以來5 月海冰面積損失的最大值(圖6a)。逐日海冰密集度數據表明2019 年5 月16 日開始,波弗特海南部已經開始出現開闊水域。從圖6b 海冰面積減小量的逐日變化曲線中也可以看出,2019 年5 月16 日之前,雖然海冰面積減小量高于1998-2019 年平均,但曲線平緩,減小速率較慢;5 月16 日開始,海冰快速減少。表2 統計結果表明,5 月1 日至15 日,海冰損失為8.01×104km2,5 月16 日至31 日,海冰損失為15.30×104km2,是前半月的1.9 倍。

表2 2019 年5 月海冰面積收支Table 2 Sea ice area budget in May of 2019

圖6 1998-2019 年5 月海冰面積收支(a)以及2019 年5 月海冰面積總變化量(ΔSIAtotal)(b)、動力輸出貢獻(ΔSIAdynamic)(c)、熱力融化貢獻(ΔSIAthermal)(d)日均累積量Fig.6 Sea ice area budget in the May of 1998-2019 (a)and cumulative of the total variation of sea ice area(ΔSIAtotal) (b),dynamic contribution (ΔSIAdynamic) (c),and thermal contribution (ΔSIAthermal) (d) in May of 2019
海冰減少是動力過程和熱力過程共同作用的結果[12,20-21]。圖6b至圖6d展示了5月海冰面積總量、動力貢獻、熱力貢獻的日均累積量,2019年5月動力輸運、熱力融化導致的海冰損失量分別為1998-2019年平均的2.8倍和3.6倍。2019年5月份熱力融化和動力輸出的海冰之比約為2∶1,熱力融化為15.36×104km2,動力輸出為7.95×104km2,其中北部邊界輸入為4.43×104km2,西邊界輸出為12.38×104km2。熱力融化在5月1日至15日貢獻相對較小,5月16日之后快速增加。在5月1日至15日,動力輸出為4.91×104km2,熱力導致海冰減少只有3.10×104km2,動力輸出是熱力融化的1.6倍。5月16日至31日,海冰融化了12.27×104km2,是動力輸出的4.0 倍。相較于其他極端年份,2019 年5 月海冰減少依然十分顯著。其他異常年5 月份的海冰輸出與多年平均結果相比沒有顯著差異,而2019 年5 月動力輸運一直高于多年平均,熱力融化也較其他異常年較高,2019 年夏季海冰極端低值更多地是依賴于當季的變化。
3.4 2019 年5 月海冰異常的原因分析
1998-2019 年1-4 月海冰厚度平均結果顯示,波弗特海區域除阿蒙森灣口附近海冰厚度偏薄,其他區域海冰厚度都在2 m 上下。而2019 年,波弗特海南部海冰厚度普遍低于2 m,整體海冰厚度也遠小于多年平均結果(圖7)。圖8a 展示了5 月波弗特海10 m緯向分量(u)和經向分量(v)、海冰面積減小量逐日變化。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東風與每天海冰減少量相關系數為0.50(p<0.01),北風與其相關系數為-0.48(p<0.01)。從表1 及3.2 節結果中發現,波弗特海5 月份海冰主要從西邊界輸出,海冰輸出主要與東風有關。2019 年5 月份東風平均風速為-5.08 m/s,是1998-2019 年5 月平均的2.4 倍;由海冰漂移場也可以看出,2019 年5 月冰漂移速度遠大于1998-2019年平均速度(圖9)。5 月1 日至15 日,波弗特海還未形成開闊水域,海表面凈熱通量也保持在較低水平。東風平均風速為-4.29 m/s,在強東風的作用下,波弗特海海冰不斷從西邊界輸出,輸出海冰面積達到7.17×104km2。海冰面積逐日變化量與東風風速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峰值出現時間相吻合(圖8a)。5 月前半月,熱力貢獻較小,因為這一階段波弗特海幾乎完全被海冰覆蓋。隨著海冰的不斷輸出,波弗特海南部海冰不斷減少,開闊水域逐漸形成,熱力貢獻逐漸增加。事實上,5 月12 日,海表面凈熱通量才由負轉為正(圖8b)。5 月16 日至31 日,雖然東風增強,平均風速達到-5.81 m/s,但是隨著海冰的不斷輸出和融化,波弗特海南部開闊水域不斷擴大,存留海冰越來越少,使得這一階段海冰輸出量減小。隨著開闊水域的增大以及海表面凈熱通量增加,更多的太陽輻射進入上層海洋,熱力貢獻大幅增加,這加劇了海冰融化,加強了正反饋循環。5 月后半月,熱力貢獻增加,動力貢獻減少,從圖8a 也可以看出這一階段東風風速與海冰面積逐日變化一致性變差。2019 年5 月風場強度遠大于多年平均結果,海冰不斷向外輸出,造成波弗特海南部較早地形成開闊水域,促使波弗特海吸收更多的太陽輻射。2019 年5 月累積吸收短波輻射量為44.46 MJ/m2(圖8c),約為1998-2019 年多年平均結果的2.5 倍,這加強了區域海冰的正反饋效應,導致海冰更多地融化,使2019 年成為1998 年以來5 月海冰損失量最大的年份。

圖7 PIOMAS 模擬的1-4 月海冰平均厚度Fig.7 Average sea ice thickness from January to April simulated by PIOMAS

圖8 波弗特海2019 年5 月10 m 風場、逐日海冰面積減少量(a)、海表面凈熱通量(b)、短波輻射吸收量(c)和1998-2019 年5 月累積短波輻射和長波輻射年際變化(d)Fig.8 10 m wind field and daily decrease of sea ice area (a),net sea surface heat flux (b),and solar absorption (c) over the Beaufort Sea in May of 2019,and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cumulative solar radiation and thermal radiation in May during 1998-2019 (d)

圖9 5 月海冰漂移場Fig.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a ice drift in May
波弗特海的極端低值都伴隨著異常高的太陽輻射(圖8d),但不同年份又存在差異。1998 年和2016年波弗特海融冰季的海冰極端低值是由于前冬季節的海冰輸出導致的[17,20-21],1998 年和2016 年前冬季節海冰面積減小分別為0.73×105km2和1.58×105km2,季節末海冰覆蓋面積較1998-2019 年平均值分別低9%和28%,海冰面積的減小使得這兩年5 月海表面吸收的短波輻射異常高,分別為1998-2019 年平均值的2.2 倍和4.6 倍。2007 年夏末異常少的海冰以及2008年前冬季節強的海冰輸出造成了2008 年夏季海冰覆蓋面積的異常[21],2008 年前冬季節海冰輸出為1.51×105km2,5 月累積短波輻射吸收量為多年平均的1.7 倍。2012 年的異常是受到8 月初強氣旋的影響[25],融冰季節內海冰面積減小4.4×105km2,是1998-2019 年中的最大值,其中動力輸出為0.76×105km2,是極端年中融冰季節動力輸出最多的一年。2019 年前冬季節末海冰覆蓋面積為4.50×105km2,與多年平均結果4.49×105km2相當,但是5 月份海洋累積吸收的短波輻射量是1998-2019 年平均值的2.5 倍,這一方面是因為2019年較高的太陽輻射,另一方面5 月初異常強的動力環境促使較早形成了開闊水域。海冰的不斷變薄(圖7),以及強動力環境使波弗特海較早地形成了開闊水域,加強了海冰的正反饋效應,伴隨著異常高的海表面凈熱通量,造成了2019 年海冰極端低值。
由于年代際趨勢和季節變化,海冰向更年輕和更薄的冰類型轉化[36-37],使其更容易受到動力和熱力強迫的影響[19]。波弗特海海冰對風場的響應越來越強,這導致了波弗特海向西輸運進入楚科奇海海冰的增加[38],并且西邊界的輸出量大于北邊界[38-39]。同時,21 世紀以來,北極增暖的趨勢十分顯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 倍[40],這加快了海冰融化。因此,一旦波弗特海區域動力環境增強,就可能會導致融冰期過早地形成開闊水域,加強海冰融化的正反饋效應,造成極端低值。隨著波弗特海海冰消退時間的不斷提前[41-42],波弗特海融冰季節海冰的極端低值現象可能更為頻繁地出現,成為波弗特海的常態。
4 總結
本研究基于衛星觀測的海冰密集度數據,對波弗特海融冰季海冰覆蓋面積極端年份進行了探究,并利用冰漂移場、海冰厚度、10 m 風場、海表面凈熱通量等數據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具體結論如下:
(1)繼1998 年、2008 年、2012 年和2016 年波弗特海出現極端低值后,2019 年波弗特海再次出現了極端低值,波弗特海海冰極端低值年出現頻率越來越高。2019 年波弗特海融冰季海冰覆蓋面積為1.38×105km2,遠低于1998-2020 年平均2.28×105km2。
(2)2019 年海冰面積極端低值主要由融冰季節的海冰變化導致,而與前秋和前冬季節海冰覆蓋面積的變化無關。2019 年融冰季(5-9 月)海冰面積減小量約為3.75×105km2,其中5 月份海冰面積減小為2.33×105km2,占融冰季內海冰面積減小量的62%。2019 年融冰伊始海冰厚度較多年平均結果明顯較低,而5 月風場強度遠大于多年平均結果,東風強度是多年平均的兩倍,海冰不斷向外輸出,造成波弗特海南部較早地形成開闊水域;同時異常高的海表面凈熱通量導致海冰更多地融化,以上因素共同造成了2019 年融冰季海冰面積的極端低值。
(3)波弗特海的極端低值都伴隨著異常高的太陽輻射,但不同年份又存在差異。1998 年、2008 年和2016 年是與前冬季節的海冰輸出有關,2012 年與融冰季內北極氣旋存在聯系。2019 年在前冬季節末海冰覆蓋面積與多年平均結果相當,但5 月份太陽輻射吸收量是1998-2019 年多年平均的2.5 倍,除了異常高的太陽輻射,還與2019 年強動力環境導致的開闊水域較早形成密切相關。隨著海冰厚度的不斷變薄,海冰對風場的響應越來越強,海冰消退時間提前,波弗特海夏季海冰的極端低值現象可能更為頻繁地出現,波弗特海海冰預測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