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給了我熒光筆的人
◎ 宋曉光

和C來往是因為一包餅干。
那天,我們剛上了體育課。大汗淋漓的他叫嚷著肚子餓,而坐他后排的我正撕開一包餅干。
我們并不熟悉,雖是前后排,但關系也就僅限于知道彼此的名字而已。他盯著我餅干的樣子好似一只看見香蕉的猴子。他不說話,但就那么死死地盯著我和我的餅干……最后,我把整包餅干給了他。
其實C是轉校生,但他很快就和班里同學打成了一片。兩個月后,他順利加入高中部籃球隊。一個后來者,因為技術過硬和外貌優勢,迅速成為賽場風云人物,很有點現實版流川楓的意味。初中部的女生甚至揣著相機搶拍他投籃的帥氣身姿。他長得濃眉大眼,頭發帶點自來卷,從這個角度看,似乎又更像櫻木花道。
總之,這個類似“二次元帥哥”的男生,因為一包餅干開始找我搭話了。
最開始的內容是這樣的——
“有沒有紙巾?”
“還有餅干嗎?”
“帶了什么吃的?”
逐漸就過渡成了這樣——
“預習?”
“復習啊?”
“你這樣累不累?每天都在學,你不休息的?”
而在此過程中,我有了一個驚恐的發現——自己越來越害怕與他對視了。他的目光就像一壺在燒的水,逐漸從冷水變成了開水。他看向我時,就像幾滴熱水灑出了水壺,濺得我整張臉都發燙。
“你這樣不行啊。”有一天下午,他突然這么說。
我明白他在說什么,正因明白,更覺羞恥難耐。那天上午,數學老師老王讓我說出昨天布置的習題的答案,結果我全錯。那時,函數對我來說,真是比登天還難的存在。
而C,他剛被學校推薦參加了全國數學競賽。
我低著頭,不去看他,也假裝聽不懂:“什么不行?”
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翻出試卷,問我一道英語閱讀題,問完后才說:“以后我們互助,你管英語,我管數學。”
我詫異:“我怎么能教你?”他英語也不差啊!
“怎么不能?”
他說到做到,那天起,每隔一晚就會給我打電話。起初,我們只是對對答案。終于有一次,數學作業全是解答題。對答案顯然行不通,于是就變成了他念解題步驟,我逐一檢查。到了12點,我們還沒對完步驟。我昏昏欲睡,也顧不得電話那頭是誰了,一心只想快點結束:“還繼續?我想睡了。”
等待片刻,他才說:“那你睡吧。”而等待的那十幾秒,我好像聽見他在數數。
有一次,我很清晰地聽見C在電話要掛斷時自言自語:“這應該沒問題了。”
第二天我問他:“你昨天說什么沒問題?”
起先他不肯說,后來許是被我問煩了,才老實交代:“老王留人主要看錯了多少,我不數一下,萬一你錯多了怎么辦?”
“千萬不能外傳啊。”
之前的全國數學競賽,他得了二等獎,此后就成了老王心腹加課代表——原先的課代表因為成績太差被老王撤了。
我感動于他的細心與耐心,他似乎也看出我的這種感動。但我們對此事都不深究,也許是不敢深究。我用一杯奶茶表達了心底的感謝之意,夜深人靜時亦思考過他的舉動背后是否有別的深意,但不敢想太多。我告訴自己,他應該不是只對我如此。我找了很多自己在他眼里并不特殊的證據,又忍不住為發現某些能推翻那些證據的東西而暗自高興。那時,我像個矛盾的集合體,期待著什么,卻又害怕那些期待成為現實。
終于,某一天晚上,電話鈴沒響。第二天,老王照常留人。同桌是個可愛的短發女生,她是語文課代表,去辦公室抱回作文本時,偷偷對我說:“老王又留人了。剛才我趁他不在偷看了作業本,你的也在里面。你先問問C答案吧,不然一會兒吃飯晚了。”
但那天他顯得十分忙,一會兒竄去隔壁班,一會兒又和班里幾個男生打鬧在一起,根本無暇理我。中午放學時,他從辦公室抱來本子,在講臺上一本正經地說:“沒拿到的待會兒留堂。”下面一片哀嚎。
說實話,我不好受,但那不好受并非來自面對作業不合格的些許羞恥感,也非對即將要餓肚子的慘狀的些許畏懼,而是……被他忽略了,我不好受。那一句“萬一你錯多了怎么辦”,是不是被他忘記了呢?
然而,他抱著作業本就那樣站到我跟前。我的本子回到了我手里。在我萬分不解時,他退回到講臺上,很大聲地宣布:“拿到本子的同學可以走了!沒拿到的請等一下王老師。他一會兒就來。”那天晚上,我給他發短信:“你那么幫我,不怕老王罵?”
“沒事的,他要是發現,我就說我放錯了。”原來,最近兩周都是他按老王的規定來分出留堂的人。頓了下,他冒出一句:“明天我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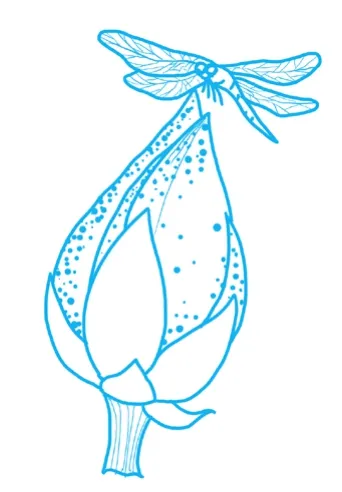
“走?”我很茫然。
“我轉學了。”他說了個距離我所在的城市十萬八千里的地名,然后解釋,“我爸工作調動,所以我們一家都得走。”
現在的我對于那時的情緒,已記不大真切了,只記得當時我是這樣回答的:“哦,那一路順風。”我很想問問,為什么那么晚才告訴我,但我什么也沒問。
第二天在教室,班主任宣布了C要離開的事。不少同學爭著與他留影。老師請人拍了一張大合照。C和平時幾個要好的男生站成一排,就在我身后。突然,他拍拍我肩膀,湊過來,很小聲地說:“你抽屜里有東西。”
我沒來得及問,攝影師就讓我們扭臉,站好,看鏡頭,一起喊“茄子”。照完相,他提著書包就走了,背影很是灑脫。我注視著并不能看見他身影的窗外,溫軟的陽光透過云層灑落在窗臺上。我想象著他走出學校的樣子。今天的陽光真的很淡、很淺,他的影子,會不會也是淡淡的呢?
直到午休時,我才拿出抽屜里那個牛皮紙大信封。它被壓在一本物理參考書下。信封里是一本筆記本和一支筆。筆記本是他一年來的數學筆記,里面記錄了大大小小難易程度不一的題,印得不清晰的地方看得出還用心填寫過。
而那筆是一支橘色的熒光筆,筆芯滲著少許閃光的金粉。那支筆我見過,是他一直用來畫重點的。熒光筆的筆帽上夾了一張小紙條,上面有一排橘紅色的小字:我們好像畏懼著同一件事,但我為此感到高興。
我們都畏懼著什么呢?那我們不約而同地止步,又算什么呢?是對青春的妥協,還是一種對自我不堅定的表達呢?然而無論是什么,我都感激那一年。那支熒光筆寫出的橘紅,為我的十七歲染上了亮麗的顏色。那種青澀的小期待,是此后人生里再難擁有的了。
(張甫卿摘自《中學生百科·悅青春》 圖/槿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