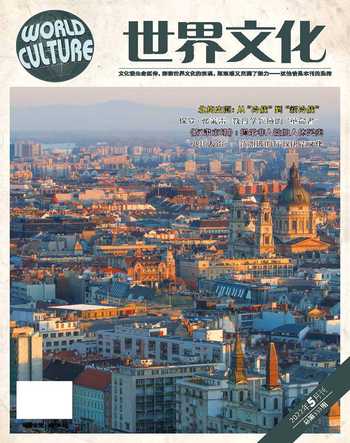讀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上)
賴某深
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官曾紀澤所著出使日記有多種版本,其中最為學界熟知、引用最廣泛的應該是岳麓書社《走向世界叢書》所收《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鐘叔河先生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論《曾紀澤在外交上的貢獻》中,專門有一節《他的出使日記》,告知讀者岳麓書社出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底本是原來保存在湖南湘鄉富厚堂曾國藩故居的曾紀澤日記原件,臺灣影印出版,分裝八大冊,名為《曾惠敏公手寫日記》。鐘先生還將手寫日記與通行節本(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曾紀澤出使日記《使西日記》)分年對比,列表作了統計,證明手寫日記近五十萬字,而通行節本只有五萬字。而將兩者逐日進行對比以后,更是發現“節掉的重要內容確實不少”。因此通行節本不能算作“一個比較完善的本子”。一般人讀到此處,可能以為《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是很完善的版本,其實不然。
曾紀澤所著出使日記的版本眾多,筆者所見到的主要有:
1. 《使西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起光緒三年(1877年)秋,止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約五萬字。
2. 《曾紀澤集·日記》,岳麓書社1983年版。據光緒十九年江南制造總局刊印《曾惠敏公遺集》整理。起光緒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止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約五萬字,二卷。
3. 《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岳麓書社1985年《走向世界叢書》版,2008年重印。起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止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約五十六萬字(包括人名、譯名索引)。
4. 《曾紀澤日記》,岳麓書社1998年版。起同治九年正月,止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即1870年到1890年共20年的日記,是曾紀澤全部手寫日記的匯集。
在以上各種版本中,最完整、較完善的是《曾紀澤日記》。那是因為點校者劉志惠對所見到的各種版本進行了鑒別,而且作了輯注。以光緒四年曾紀澤日記為例:
九月初一日。寫西字函致裴式楷,借其電報書一觀。蓋就英國字典,去其甚僻者,取有用之語,以數紀之。中國電報書,字不滿萬,故以四位碼號紀數;西字較少,以五位碼號紀數也。(《曾紀澤集·日記》第336頁,《曾紀澤日記》779頁)
這段文字非常重要,是曾紀澤自編電報號碼(后文有詳細敘述)的紀錄。因為那時電報費很貴,用漢字編寫電報號碼字數少費用省,而且西方人編的電報號碼不便于保密,所以曾紀澤下決心自編電報號碼。而這樣重要的內容在《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寫西字函致裴式楷”之下文字全部沒有(117頁)。
初二日。法國公使白羅呢來久談。西人男女并重,故于親串稱謂,最易混淆。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同稱,曰父之父母,與母之父母無異也。伯叔父與舅氏、姑丈、姨丈同稱;伯叔母與妗氏、姑母、姨母同稱;表兄弟、表姊妹、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同稱。皆由于男女并重,故親疏不甚分別。白公使詢余親屬,其翻譯官德微理亞不能轉達,余自以英語譯而答之。白、德二君聞親串名目之細,差等之殊,瞿然以為異焉。(《曾紀澤集?日記》第336、337頁,《曾紀澤日記》780頁)
《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則記作 “白羅呢來,久談”(118頁),以下討論中外親屬稱謂的內容全部不見。這段文字可見曾紀澤對中西親屬稱謂的深刻認識,而且從中可看出法國駐華使館翻譯德微理亞在翻譯時辭不達意,曾紀澤自己用英語翻譯,起到了較好的溝通效果。但是《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另外記載了試制新衣數件,張之洞、李善蘭先后來拜訪,中午到英國公使傅磊斯處赴宴等情況,這些內容都是《曾紀澤集?日記》沒有的。由此可見,《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雖然源自《曾惠敏公手寫日記》,文字大大多于《使西日記》《曾紀澤集·日記》,但也不完整和完善。相反,《使西日記》《曾紀澤集?日記》雖然文字較少,但有的內容《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卻沒有。原因可能是曾紀澤經常對自己的日記進行修改和增刪,加之其在國外時有人未經其同意即翻刻其日記,導致各個版本文字詳略不同。筆者不能理解的是,《使西日記》《曾紀澤集·日記》《曾紀澤日記》均為鐘先生能看到的版本,為何沒有在2008年再版《走向世界叢書》時將幾種版本對勘,增補相關的文字,使《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更臻完善?
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素稱難讀,這不僅因為該書卷帙浩繁,正文近一千頁,將近60萬字,而且因為日記像流水帳,枯燥乏味,每天照例記載何時起床,何時睡覺,做了什么事,讀了什么書,下了幾盤棋,寫了幾副對聯,見了什么人,但都一筆帶過,不知其詳,不像有些出使日記那樣內容豐富多彩,讀來興味盎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曾紀澤記日記非常刻板,深受父親影響。
1965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十巨冊《湘鄉曾氏文獻》,第六冊為《綿綿穆穆之室日記》,從中可看出曾國藩是如何記日記的。他記日記的格式很特別,合兩頁為一日,每頁四欄,各有標題(即日課),依次為讀書、靜坐、屬文、作字、辦公、課子、對客與回信。有事則記,無則從缺。幾乎無日不記者有讀書、辦公、課子、對客四項。
《出使英法俄國日記》正是如此記日記的,試看光緒四年八月初二日記:
晴雨互見。辰初二刻起,批字典,飯后,復批良久。寫一函寄劉伯固,又片緘致鄧洪芳。至上房一坐。批字典。飯后,惲小山來,一談。其友裕朗西后來,同談。入城,拜白羅尼、德微理亞,久坐。拜壁利南、傅磊斯,坐極久。傍夕,拜夏子松,一談。至總理衙門。因從前交涉事件,須調案牘考求,故移寓署中也。閱《使西紀程》良久。夜飯后,寫西字函答阿恩德。閱江寧李小池(奎)所著《東行日記》極久。子初睡。
曾紀澤這天的主要活動是學英語、批字典;對客,中外友人都有;寫信,包括英文信件;因上月二十七日獲悉派充駐英、法公使,所以到總理衙門查閱往年交涉事件,甚至干脆住到總理衙門查閱案卷;閱讀郭嵩燾的出使日記《使西紀程》及李奎訪美的《東行日記》。和曾國藩的“日課”沒有兩樣。
曾紀澤日記中,經常記載與使館同僚下圍棋,有時看人下圍棋看半天。曾國藩日記中,下圍棋的記載比比皆是,如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早飯后見客一次,旋清理文件。與筱泉圍棋一局,又觀筱泉與石洲圍棋一局……

還有,曾紀澤對于出國前蒙兩宮皇太后召見時的問話詳盡記載,各種曾紀澤出使日記均一字未刪,甚至連自己在對話時的表情、動作均一一記錄,如“免冠碰頭,未對”,“肅然未對”,“退至原位”,充分表明了曾紀澤對朝廷的感恩心情。而這在其他出使日記中很少看到。曾國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面見同治帝與兩宮太后,十五日、十六日連續接受帝后召見,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第四次陛見,均作了詳細的記載,這充分說明了曾國藩記日記的習慣對曾紀澤的影響。
“與民同樂, 則民不怨”。曾紀澤注意考求西方 “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日記中多有記載:
中國人來歐洲者,有二事最難習慣,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價太貴。西人地基價值極昂,故好樓居,高者達八九層,又穴地一二層為廚室、酒房之屬,可謂愛惜地面矣。然至其建筑苑圃林園, 則規模務為廣遠,局勢務求空曠。游觀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無絲毫茍簡遷就之規。與民同樂,則民不怨。”(5,1,20。表示光緒五年一月二十日。下同)
從房屋建筑談到城市建設,歸結到社會政治制度,“與民同樂, 則民不怨”,這樣的結論很有見地。
駁斥中國刑法過嚴之說。西方往往認為中國刑法過于嚴酷,曾紀澤盡量做耐心、細致的解釋。一次是與萬國公法會會員土愛師(另處譯為屠愛士)談話,土愛師問:“大辟之刑,一死足矣,何以有凌遲、斬、絞之分?”曾紀澤答道:“罪有輕重,則刑有等差,非獨以處犯者,亦欲使齊民知所儆畏也。”另一次是和稅務司葛德立討論左宗棠奏請朝廷將俘獲的侵占新疆的雅古貝(即阿古柏)子孫“閹割為奴”,西方輿論嘩然,曾紀澤解釋說:“宮刑究竟下于大辟一等”,畢竟不是死刑。況且“雅古貝稱兵作亂,戰斗多年,殺人無算,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其子孫孑遺,不坐殊死之典,而科以應得之刑,西人乃羼入而袒庇焉,名為好仁,實多事耳。”痛斥西方人假仁假義,多管閑事。還有一次則是看到英國報紙議論中國刑罰過嚴,語涉侮辱,令人憤懣,與使館翻譯、英國人馬格里討論宮刑,馬格里說:“歐洲各國,最不以宮刑為然。謂叛逆子孫,若于戰斗之際,或于俘獲之頃,遽蒙誅戮,西人必不譏為殘忍。今事定而科以穢辱之刑,是以嘩噪不休。”曾紀澤笑對道:“性命總算第一要緊,英人之論,若謂與其宮之,無寧殺之者,此說終不圓足。”可謂義正辭嚴。
介紹法國超級大市場。光緒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至琫馬舍大店,縱觀極久。巨細器物,無所不備。使工匠暨男女隸役二千馀人。每日送貨之車,用馬二百馀匹。庖廚鍋甑,大逾等倫,炊炮之事,皆以火輪機器運動升降。店面聯數十號合為一家,冬夏嘗擇日設樂肆筵,以宴賓客。平日游觀者,肩摩于堂,轂擊于市。茶、酒、果、餌,皆精潔豐腆,陳設于大廳,任游客飲啖,不索值也。入其店市物者,視他處散店,貨精而值廉。是以晝夜出入男女,或市器具、衣飾,或專事游覽,喧闐絡繹,如蟻如蜂。司帳目者百馀人,算不停籌,簿不輟書。又用伙友數人,導客巡視樓閣數重,廚室、畜圈,磨不周至。復有大廳,陳設圖籍、書畫、小說、新聞,以供游客與店友之分班休息者,偃息而觀賞焉,蓋雜貨店之偉觀。而問其資本,出于一人,則其家之富亦可想矣。嘗遣店友至中國京師、天津一帶,采買瓷器、銅器之屬,挈銀數萬兩,遇有適用之物,輒闔一店而收買之,運載以來,陳為一類。局面之開展,于此亦見一斑。
之所以不厭其煩詳細引錄這段話,是因為今天人們習以為常的超市,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就有了。從日記中可看出,這家大超市貨物巨細無遺,琳瑯滿目,價廉物美,貨物全球采購,還有免費飲料,有導購,有休息區,吃喝玩樂一應俱全,無怪乎曾紀澤這天從午飯后一直逛到黃昏,并津津樂道。
主張面向洋人子弟,在西方設立中國學校,傳授中國文化,此為設立孔子學院之先聲。光緒五年四月五日記,使館翻譯、英國人馬格里提出,中國人流落到英法兩國的時時有之,應當仿照西洋各國之例,由本國籌款交給公使,隨時收留而遣送回國。曾紀澤認為這個設想很好,但因使館經費不敷,不易舉行。進而聯想到:
中國辦洋務,必須多得通達外國情形之人,并于中國設立學塾,聘洋人以教中國子弟之好西學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國設立學塾,擇中華積學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華學者,久則聲氣相孚,可以抉幽洞微,暗獲助益。而所費僅塾師之束脩,賃屋之價值耳,其效甚速而遠。然當此經費不敷之際,亦只能托諸空言。
晚清最早在海外創辦華人中西學堂的是第三任駐美公使張蔭桓(任期為1886—1889),他在舊金山、古巴、秘魯等地興辦華人中西學堂,是倡導和興辦海外華僑教育的第一人。筆者在《“絕域使才”張蔭桓寫的<三洲日記>》一文中已詳述。而倡導面向歐洲洋人子弟設立中文學校,曾紀澤則是第一人。
不遺余力宣傳中國文化。馬格里向他請教中國好龍起于何時?他答以史事可考者,以龍紀官與黃龍負舟為最早而有據。馬格里又說,華人所稱龍德,能大能小,能飛能潛,西人以為無據。答以古代有豢龍御龍之官,必是確有其物。《周易》以龍為陽氣取象,則然,不必定有其物。還說海里的生物億萬種,“不可以西人未嘗見龍,遂以為無是物也”。他與英國著名漢學家、牛津大學教授理雅各討論《周易》。理雅各曾將四書五經翻譯成英文,他表示諸經都能通曉大意,唯獨《周易》難懂。曾紀澤說,《周易》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精神所注,文字不多,卻包含宇宙萬物之理,當然深奧難懂。理雅各又說,《周易》為卜筮之書,無關學問。答以西洋人近日的發明創造,幾千年前編寫《周易》的中國圣人即已道破:“云雷經綸”,圣人預言電線之理;“出入無疾,七日來復”,圣人預存西醫之說;即使是七日一禮拜,火車汽機,也都是中國圣人幾千年前就預見到的。總之,《周易》于中國學問,“仰觀天文,俯觀地理”,無所不包,即使西學,亦不能出其范圍。曾紀澤是“西學中源說”的典型代表,所舉證難免有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的成分。日記說:“理雅各心折”,約定今后經常來拜訪,“剖問疑義”。理雅各是否心服口服只有天知道,日記記錄與理雅各的討論就只有這一次。

曾紀澤“西學中源說”,最集中體現在下文中:
余謂歐羅巴洲昔時皆為野人,其有文學政術,大抵皆從亞細亞洲逐漸西來,是以風俗文物,與吾華上古之世為近。嘗笑語法蘭亭云:中國皇帝圣明者,史不絕書,至伯理璽天德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堯舜而已。此雖戲語,然亦可見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國于古曾有之,不為罕也(5,2,23)。
弘揚中國文化是對的,但是什么風俗文物乃至發明創造都是中國“古已有之”,那就不是文化自信,而是牽強附會了。
為使館建章立制。晚清外交史的研究,歷來注重外交思想和外交交涉,而對于駐外使館建設,極少有人關注。為使館建章立制的鼻祖當然是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他為屬員規定了五戒:一戒吸食洋煙;二戒嫖;三戒賭;四戒外出游蕩;五戒口角喧嚷。作為第二任駐英公使,曾紀澤主要做了以下建章立制工作:商定使館醫藥章程,因有人用藥太多,有人無病也喜歡服用補藥,導致從國內帶去的藥物都已用盡,所以制訂一個用藥章程,加以限制而昭公允;使館經費不足,如何辦理?因使館公事繁多,隨行人員不少,尤其是有大量半公半私之開支,如捐款、獎賞之類,沒有報銷名目,因此曾紀澤出國之前,即與總理衙門商定,變通辦理,即各人扣發應得之薪水,貼補那些候補武弁及難以明文規定報銷的費用,到倫敦后,曾紀澤見到郭嵩燾,才知郭正是如此辦理的;使館陳設器具,要精美還是實用?依曾紀澤之見,但求堅固,不須精美。中國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和使館翻譯馬格里則認為,要從中國運去精美器具,使外國稱羨,以廣貿易;此外曾紀澤非常重視使館官員的文化教育,親自命題考試、閱卷、評定等次,這在晚清外交官中是很少見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效法的。

曾紀澤深刻認識到國際法的重要性,“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
對巴黎的繁華綺麗不以為然:“巴黎為西國著名富麗之所,各國富人巨室,往往游觀于此,好虛靡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盡能專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
對于西方文化、科學,他記載了參觀倫敦畫報社、名畫展、蠟像館、植物園、動物園、圖書館、醫學院;觀看顯微鏡、雙筒望遠鏡;登格林威治天文臺觀天文望遠鏡;到倫敦大書院輿地會聽學術報告、參觀德國著名的西門子電器局等等,這些參觀考察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豐富了他的頭腦。
在法國,他得知“新任下議院首領剛必達,人甚公平,不肯袒庇教士”,因此想到“宜與結交,則以后遇事牽涉教堂者,易于了結”,反映了他作為外交官的敏銳性。
但他的政治觀點,有的也較為保守,如評論英國婦女爭取選舉權:“英國敬重婦女,相習成俗,他國視之已為怪詫,而婦人猶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議院預聞國政為恨。甚矣,人心之難饜也!”
日記中有一些對人、事、書的獨特評論,耐人尋味。對正留學英國學習海軍的嚴復這樣評價:
宗光才質甚美,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以郭筠丈(指郭嵩燾)褒獎太過,頗長其狂傲矜張之氣。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華文字,未甚通順,而自負頗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勵之,愛其稟賦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不知道嚴復是否看到過這段文字,作何感想?
對商人胡雪巖代左宗棠借外債營私舞弊,則評論說:
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指胡雪巖)開報公項則一分五厘。奸商明目張膽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壟斷而登,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而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今則聲勢日隆,方見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挾私如此,良可慨已。
日記對于有些重要內容記載太簡略甚至失載,像赴俄談判時的唇槍舌劍就沒有具體記載。另外,在離英歸國前夕,在倫敦《亞洲季刊》上用英文發表《中國先睡后醒論》,日記中無只言片語談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