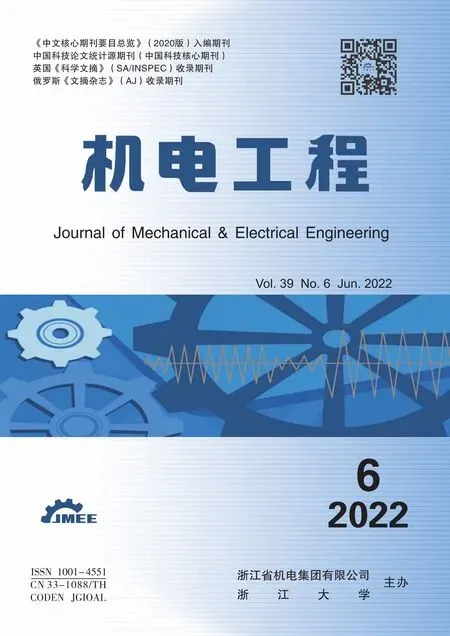表面硬化對地鐵輪軌磨耗性能影響的實驗研究*
孫培文,朱愛華,張 帆,楊建偉,馬潮潮
(北京建筑大學 城市軌道交通車輛服役性能保障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44)
0 引 言
在地鐵列車運行過程中,輪軌之間的各種相互作用力均通過輪軌摩擦副之間的滾動接觸得以實現,因此,輪軌之間的損傷主要以磨損和滾動接觸疲勞為主。
常崇義等人[1]采用輪軌滾動接觸磨損的小比例實驗臺,研究了不同硬度輪軌匹配下的車輪試樣多邊形磨耗問題。周韶博等人[2]利用雙輪對滾的方式,研究了ER8和ER8C 2種高速車輪材料與U71MnG鋼軌材料的滾動摩擦磨損情況。張關震等人[3]對時速250 km等級動車組自主化D1車輪進行了耐磨性能實驗,并將其與進口ER8車輪的耐磨性能進行了對比。張銀花等人[4]在實驗室進行了3種硬度車輪與3種硬度鋼軌的對磨實驗,對比分析了硬度不同的車輪與鋼軌對磨時輪軌的損傷情況。ZHANG Ning等人[5]將3種強度等級和1種奧氏體球墨鑄鐵(ADI)車輪鋼與傳統鋼軌鋼相匹配,進行了滾動滑動磨損實驗。王文健等人[6]利用滾動磨損實驗機,研究了車輪鋼與U71Mn熱軋鋼軌的硬度匹配性能,分析了不同硬度車輪與U71Mn鋼軌匹配時的摩擦磨損與表面損傷行為。李英奇等人[7]通過對磨實驗,研究了接觸應力相同時貝氏體鋼軌的磨損率、表面粗糙度、硬度,并結合掃描電鏡觀測了磨損表面和剖面的形貌特征,分析了不同滑差條件下貝氏體鋼軌的磨損行為特征和變化規律。MOLYNEUX-BERRY P等人[8]利用動態模型,研究了車輪/鋼軌接觸處的應力以及其硬度和微觀結構的變化規律。HUANG Y B等人[9]對輪軌材料滾動接觸疲勞和表面裂紋的形成進行了實驗研究。為了研究輪軌表面硬度變化問題,LEWIS R等人[10]對實驗室和現場輪軌表面的相關數據進行了調查研究。為了研究磨損行為與硬度的關系,LEE K M等人[11]利用實際服役中的輪軌樣品,在不同尺寸上測量了其微維氏硬度和洛氏硬度。SEO J W等人[12]通過實驗,對普通鋼軌和熱處理鋼軌因車輪硬度增加而產生的RCF和磨損特性進行了評價。
以上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運營前的輪軌硬度比方面,且大多是有關硬度與表面疲勞裂紋之間的關系研究,而對運營過程中,表面硬化程度與輪軌磨耗間的關系研究較少。
研究車輪和鋼軌的磨損特性,不僅要考慮車輪的初始硬度,還應該考慮表面硬化效應的影響。研究輪軌初始硬度不同與表面硬化程度共同作用下的輪軌磨耗規律,可以為進一步降低輪軌磨耗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
因此,筆者依據赫茲模擬準則,通過模擬地鐵輪軌的實際接觸工況,使用GPM-60摩擦磨損實驗機,對兩種現役的不同車輪鋼試樣和U75V鋼軌試樣進行雙輪試樣對滾實驗,研究輪軌表面硬化對輪軌磨耗規律的影響。
1 輪軌接觸模擬實驗
1.1 模擬實驗設計
此處實驗采用GPM-60摩擦磨損實驗機,并采用試樣雙輪對滾的實驗形式,來模擬輪軌的接觸條件。
實驗時,要保證模擬狀態下的輪軌接觸應力和接觸斑橢圓長短軸的比與實際線路保持一致,同時實驗車輪試樣應具有與實際車輛運行條件下的車輪相同的角速度(均忽略輪軌間蠕滑)。
模擬實驗試樣尺寸、施加的載荷及轉速均依照赫茲模擬法則確定[13],即:
σlab=σfield
(1)
(a/b)lab=(a/b)field
(2)
ωlab=ωfield
(3)
式中:σlab—實驗條件下輪軌材料間的最大接觸應力;σfield—實際線路運行條件下輪軌材料間最大接觸應力;(a/b)lab—實驗條件下輪軌接觸斑長短軸的比值;(a/b)field—實際線路運行條件下輪軌接觸斑長短軸的比值;ωlab—實驗條件下車輪的旋轉速度;ωfield—實際運行條件下車輪試樣的旋轉速度。
實驗分為A、B兩組,微合金鋼輪與U75V鋼軌為A組,CL60鋼輪與U75V鋼軌為B組;實驗運轉周期為2×105轉。
實驗過程中,每4×104轉拆卸一次輪軌試樣,使用JA30003精密電子天平(精度:0.001 g)稱重計算磨耗量,采用HBE-3000電子布氏硬度計測量輪軌接觸面的表面硬度數據。
GPM-60滾動接觸磨損實驗機主要由主機、操控與監測系統、冷卻循環系統、轉速和壓力傳感器等組成;通過操作面板設置既定的載荷及轉速工況,將穩定的循環應力施加在上下試樣的接觸表面。
GPM-60滾動接觸磨損實驗機實物如圖1所示。
實驗模擬現實中地鐵車輛在14 t軸重、70 km/h的工況,設備主、陪試軸的固定轉動滑差率為5%,計算得到實驗機所需的垂向加載載荷為223 N;運轉速度為443 r/min,輪軌試樣直徑均為60 mm,輪試樣接觸表面為21 mm半徑的圓弧段。
輪軌試樣的結構尺寸和實物照片如圖2所示。

圖2 輪軌試樣尺寸及實物圖
1.2 實驗材料確定
實驗所需的輪軌材料均采集自某實際運營線路中的輪軌,該線路中長期使用CL60鋼制地鐵車輪,并在近期部分換裝了同廠生產的微合金化新型鋼制車輪。
微合金化地鐵車輪鋼相較于CL60鋼優化了材料成分比例,具有更高C、Cr含量,同時添加了V元素(V元素的適量添加可以顯著增強鋼的屈服比,降低其脫碳敏感性,對于改善其冶金表面質量具有明顯效果)。
車輪試樣從車輪名義滾動圓處踏面10 mm以下位置水平取樣,鋼軌試樣從U75V鋼軌軌道頂10 mm以下水平位置取樣。
輪軌取樣位置如圖3所示。

圖3 輪軌試樣取樣位置示意圖
微合金鋼材料的成分是在原有CL60鋼的基礎上通過對材料成分的調整,提高熱處理參數控制精度以及采用分步淬火工藝制成的,微合金化鋼的材料硬度和機械性能得到了提高。
兩種車輪鋼及鋼軌材料的機械性能和實驗分組如表1所示。

表1 兩種車輪鋼及鋼軌材料機械性能及實驗分組
1.3 實驗過程
在確認輪軌試樣安裝到位后,筆者首先啟動設備,對傳感器進行校正調零,并通過控制面板輸入實驗機所需的參數,主要包括垂向加載載荷223 N,以及運轉速度443 r/min等。
實驗中的輪軌試樣如圖4所示。

圖4 實驗中的輪軌試樣
實驗運轉周期為2×105轉,實驗過程中每4×104轉拆卸一次輪軌試樣。
2 試樣硬度測量
筆者將拆下的實驗試樣卸下后,完全浸沒在裝有表面活性清洗劑的超聲波清洗儀中進行清洗、烘干;使用JA30003精密電子天平(精度:0.001 g)對輪軌試樣分別進行稱重,待其讀數穩定時進行記錄,每個試樣需要反復稱量3次,然后計算取平均值;沿接觸位置等間距選定5個點,通過HBE-3000電子布氏硬度計測量輪軌試樣的表面硬度,取平均值并做好記錄。
實驗試樣硬度的測量過程如圖5所示。

圖5 實驗試樣硬度測量過程
在完成上述試樣的磨損量與硬度數據測量后,筆者記錄下相關數據,重新安裝試樣繼續進行實驗。
3 實驗結果和討論
3.1 磨耗量分析
實驗運轉周期為2×105轉,實驗過程中每4×104轉拆卸一次輪軌試樣,并記錄數據;使用超聲波清洗儀,配合表面活性劑,去除試樣表面的氧化物、碎屑和油污后烘干;使用精密電子天平(精度:0.001 g)進行稱重,計算得到每次輪軌試樣的質量損失,即磨耗量。
在不同運轉周期下,輪軌試樣的累積磨耗量如圖6所示。

圖6 輪軌試樣不同階段的累積磨耗量
隨著運轉次數的增加,兩組車輪和鋼軌試樣的總磨耗量均呈現增長的趨勢,同時A組車輪試樣磨耗量明顯低于B組,而A組鋼軌試樣的磨耗量卻要多于B組。
在實驗初期,輪軌試樣表面處于磨合狀態,此時質量損失速度較快,而隨著輪軌試樣表面接觸狀態逐漸趨于穩定,輪軌試樣質量損失速度逐漸降低,輪軌試樣由磨合期的快速磨損階段轉變為穩定磨損狀態。
完成2×105次運轉后,輪軌試樣各自的磨耗值如圖7所示。

圖7 輪軌試樣2×105萬轉的累積磨耗量
由圖7可知:微合金化地鐵車輪鋼在模擬實際運行路線的情況下,比傳統的CL60鋼車輪鋼更具有耐磨性;在模擬運轉2×105轉的情況下,相較于CL60鋼,微合金化地鐵車輪鋼的磨耗率降低了35.1%,但與之相對的是其鋼軌磨耗量增大,磨耗率提高了7.8%。
A、B兩組各自輪軌磨耗值的總和如圖8所示。

圖8 輪軌總磨耗量
綜合考慮輪軌的磨耗,由圖8可知,微合金化地鐵車輪試樣的輪軌總磨耗量比CL60鋼車輪試樣降低了1.47 g,總磨耗率降低了1.6%。由此可見,初始硬度較高的微合金化地鐵車輪新材料體現出了較好的耐磨性、較低的輪軌總磨耗量。
3.2 表面硬化分析
輪軌磨耗性能和材料本身的硬度相關,在一定范圍內隨著材料本身硬度的提高,輪軌材料的總磨耗量會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4]。
筆者使用布式硬度計,對輪軌試樣表面磨痕中心位置按圓周選取3個點,然后計算得到硬度的平均值,如圖9所示。

圖9 不同階段輪軌試樣表面硬度
相較于傳統的CL60鋼車輪鋼,微合金化地鐵車輪鋼具有更高的初始硬度,輪軌材料在實驗初期的磨合階段均經歷了表面硬度快速增長的過程,然后車輪硬度穩定增長,但增長速度大大放緩;同時,初始硬度高的材料硬度一直穩定地高于初始硬度低的材料,但兩者的硬度值隨著實驗的進行有趨近的跡象。
鋼軌材料則在經歷了初始的表面硬度快速增長后,在后期基本保持了表面硬度的穩定;同時,A組與硬度較高的車輪相匹配的鋼軌表面硬度一直高于B組與低硬度車輪匹配的實驗組。
輪軌試樣在對磨的過程中,由于試樣間的接觸應力關系,會發生表面的塑性變形,同時試樣間的相對滑動會產生大量的熱。表面塑性變形會導致冷作硬化,即輪軌試樣表層硬度變高的現象。在接觸應力的作用下,金屬材料接觸區產生塑性變形,會導致金屬晶格間的滑動和晶格的扭曲,相應的晶粒組織被拉長,硬度在變形初期快速提高,材料塑性和韌性進一步下降。同時,塑性變形導致的晶格錯位塞積將會引起馬氏體相變,且變形量越大,馬氏體產生量越多[15]。
馬氏體相變的產生會進一步導致材料表面的硬度和脆性提高,在進一步的塑性變形前,硬脆性會導致脆性開裂。同時,相對滑動產生了大量的熱量,使得試樣內外產生溫度梯度現象,由塑性變形做功和相對滑動摩擦產生的大量熱量會導致晶粒位錯密度的降低,使得表層硬度出現回軟現象;兩者在運行過程中相互競爭,隨著運轉周期的增加,最終輪軌試樣表面會處于塑性變形與磨損的平衡狀態,表面硬度呈現較穩定狀態。
3.3 表面硬化與磨耗分析
輪軌磨耐性和材料本身的硬度相關。一般隨著材料硬度的上升,其本身磨耗量會下降。
材料磨耗率ξ如下:
(4)
式中:H—輪軌試樣的歷次重量,g;i—實驗次數(i=0,1,2,3,4);ξ—磨耗率,g/104r。
A、B兩組車輪試樣硬度與磨耗率階段變化如圖10所示。

圖10 A、B兩組車輪試樣硬度與磨耗率階段變化
由圖10可知:在實驗的第一階段,車輪鋼試樣在運行初期經歷了快速的表面硬化過程,此時輪軌試樣處于初期的磨合階段,車輪磨耗率同步陡增;
第二階段,隨著初期磨合過程的結束,車輪試樣表面硬度增長速度放緩,A組新型鋼車輪試樣磨耗率隨車輪表面硬度增加而下降,B組CL60鋼車輪試樣磨耗率同樣開始下降,但磨耗率的最大值超過A組,并且磨耗率一直高于A組,兩組試樣表面硬度均呈現穩定上升趨勢。由此可見,車輪試樣磨耗率隨車輪表面硬化程度的提高呈現明顯下降趨勢。
A、B兩組車輪試樣磨耗率變化如圖11所示。

圖11 A、B兩組車輪試樣磨耗率變化
由圖(10,11)可知:A、B兩組車輪試樣表現出了相同的趨勢,即在經歷了初期磨合時磨耗率的快速增長后,車輪試樣磨耗率隨車輪表面硬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漸降低,A組車輪試樣的表面硬度一直高于B組車輪試樣,一般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16];同時,A組車輪試樣的磨耗率始終低于B組,且磨耗率下降速度較快。[17]
A、B兩組鋼軌試樣硬度與磨耗率階段變化如圖12所示。

圖12 A、B兩組鋼軌試樣硬度與磨耗率階段變化
由圖12可知:在實驗開始階段,鋼軌試樣呈現出和車輪試樣相似的趨勢,伴隨著磨合初期過程的快速表面硬化,鋼軌磨耗率同時快速增高,磨耗速度較快;磨合后,鋼軌磨耗率基本處于穩定狀態;A組鋼軌硬度一直高于B組鋼軌試樣,其磨耗率也一直高于B組鋼軌試樣。
A、B兩組鋼軌試樣磨耗率變化如圖13所示。

圖13 A、B兩組鋼軌試樣磨耗率變化
鋼軌表面的硬度變化情況,將直接影響其本身的磨耗性能。從圖(12,13)可知,A、B兩種鋼軌的磨耗率差異不大,且隨著時間的增加,其表面硬度逐漸不再增加,而兩者的磨耗率也逐漸趨于一致。
4 結束語
為了對輪軌初始硬度不同與表面硬化程度共同作用下的輪軌磨耗規律進行研究,進一步降低輪軌的磨耗,通過對某實際運營線路中的鋼軌和兩種不同車輪鋼的摩擦磨損進行實驗研究,筆者探討了材料表面硬化對輪軌耐磨性的影響。
研究結論如下:
(1)兩種地鐵車輪鋼在運行中均出現了表面硬化現象,并且經歷了磨合期的快速硬化和穩定期的平穩硬化階段;鋼軌在磨合期表面硬度快速增加,在穩定期的表面硬度基本保持不變;
(2)微合金化地鐵車輪鋼比CL60鋼具有更高的初始硬度和表面硬化程度,并且在實驗后期兩者的表面硬度數值表現出了逐漸趨近的現象;
(3)相較于CL60車輪鋼,微合金化地鐵車輪鋼在2×105轉時磨耗率降低了35.1%,與之匹配的鋼軌磨耗率增加了7.8%,輪軌總磨耗率降低了1.6%;初始硬度較高的微合金化地鐵車輪新材料具有較好的耐磨性和較低的輪軌總磨耗量;
(4)在磨合后的穩定期,輪軌磨耗率均隨材料表面硬化程度增高而降低;
(5)實驗結果表明,輪軌磨耗量、輪軌磨耗率、表面硬化速度在運行初期均最大,此時試樣主要處于磨合階段;
考慮到輪軌磨耗和表面硬化在運行初期較大的特點,筆者建議在新輪軌使用前、車輪鏇修和鋼軌打磨后通過適當的表面噴丸強化處理,以提高輪軌表面硬度,縮短其表面硬化過程,降低輪軌磨合期的磨耗速度,減少輪軌的磨損。
在后續的工作中,筆者將更多地從微觀角度出發,對輪軌表面硬化行為進行研究;同時,深入研究表面硬化對于表面損傷的影響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