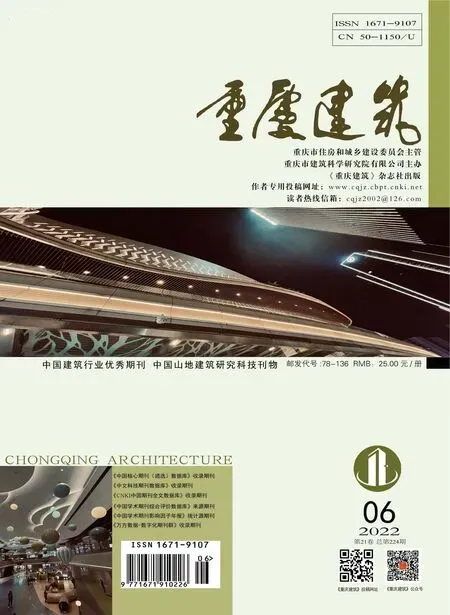綠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計算實踐與探討
——以重慶市設計院建研樓工程為例
蔣超,謝崇實,黎昆
(重慶市設計院有限公司,重慶 400015)
0 引言
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75 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將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1]。 這一目標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 《中國建筑能耗研究報告2020》指出,2018年全國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總量為49.3 億tCO2,占全國能源碳排放的比重為51.2%[3]。 因此,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要路徑。
綠色建筑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內,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為人們提供健康、適用、高效的使用空間,最大限度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質量建筑[4]。 綠色建筑提倡在提供健康、舒適的室內環境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建筑運行階段能耗,提倡綠色施工,使用綠色建材,從而形成一條全生命周期降低建筑碳排放的有效路徑,這是建筑業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于2019年發布了 《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GB/T 51366—2019),規范了建筑碳排放計算方法[5]。 結合近年來相關研究和標準,本文以重慶市設計院建研樓工程為例,探索適用于重慶的新建綠色建筑碳排放計算的路徑和方法,計算出該項目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可為后續節能減排研究提供基礎數據。
1 項目概況
重慶市設計院建研樓(圖1)總用地面積1762.4m2,地上建筑面積2978.10m2,地 下 建 筑 面 積2075.36m2,總 建 筑 面 積5053.46 m2,包括3 層地下車庫與5 層地面建筑。 項目采用的主要綠色建筑措施有: 利用被動設計加強自然通風、 自然采光;采用可智能調光、調節色溫的智能照明系統;利用可再生能源,配備光伏發電系統;從設計到施工的全過程BIM 設計; 地上主體結構采用預制裝配式鋼結構,實現土建裝修一體化設計; 高效的多聯機系統及獨立的新風系統。項目于2022年3月獲得LEED v4 BD+C 金級認證,于2020年獲得重慶市綠色建筑金級設計認證、綠色建筑二星級設計認證。

圖1 項目效果圖
2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計算
2.1 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計算
項目處于夏熱冬冷地區,建筑使用階段碳排放應為建筑工程規劃許可證范圍內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量和可再生能源及碳匯系統的減碳量[5]。 該項目為新建建筑,無建筑運行相關數據,因此,筆者采用了建筑能耗模擬的方法,計算了建筑年能耗,采用了國家機關公布的區域平均碳排放因子計算因電力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 本文采用由生態環境部公布的2019年度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6]作為計算依據,如表1 所示。 根據電量碳排放因子計算公式[7],重慶市(華中電網)2019年電力排放因子為0.5721kgCO2/kW·h。

表1 2019年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6]
2.1.1 建筑能耗模擬及可再生能源計算
建筑能耗模擬采用的能耗模擬軟件eQuest 是由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和J.J. Hirsch 及其聯盟共同開發的一款建筑能耗模擬軟件,可進行建筑逐時能耗模擬,其計算內核DOE-2 是目前世界上應用最廣泛的能源模擬程序。
項目圍護結構采用自保溫體系,砌體采用250mm 蒸壓加氣混凝土砌塊,熱橋采用垂直纖維巖棉板;項目空調系統采用了多聯機及獨立的新風系統;項目照明系統采用了可智能調光、調節色溫的智能照明系統;項目無集中生活熱水需求,冬季盥洗用熱水采用局部電加熱設備。 項目消耗終端能源類型僅有電力,無其他能源。
項目照明功率密度、設備密度、新風量、空調設計溫度等運行特征,均按照項目實際設計值進行模擬。 項目空調、照明、設備運行時間表和人員在室率等參照《公共建筑節能設計標準》附錄B中表B.0.4-1、表B.0.4-4、表B.0.4-6、表B.0.4-10[8]設定。
模擬得出的建筑各系統全年能耗數據如表2 所示。

表2 建筑各系統年能耗模擬值
項目可再生能源采用光伏發電系統,光伏系統共1 個光伏面板安裝區,位于已建辦公樓屋頂。 光伏系統供電負荷為車庫及辦公一般照明,接入一般照明箱0.4kV 低壓配電母線。 項目共安裝光伏發電板136 塊,總面積為126.5m2。
光伏系統發電量根據《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式4.5.5 計算。其中,年太陽輻射照度取886kW·h/m2,根據廠家提供的系統參數,光伏電池轉換效率取20%,光伏系統損失效率取40%,計算出的光伏系統年發電量為13447kW·h。該工程光伏發電系統采用自發自用未接入電網的運營方式,因此光伏發電量可直接減扣建筑年用電量,得到項目年用電情況如表3 所示。

表3 項目年用電情況統計表
2.1.2 綠化碳匯
目前國內外對綠化碳匯相關研究還比較少,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也未對相關的計算進行規定。 因此,筆者比較了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根據該項目綠化的實際情況,決定采用陰世超[9]研究的相關結果進行綠化碳匯計算。 適用于該項目的不同綠植類型的碳匯量如表4 所示。

表4 適用于本項目的不同綠植種類的年固定碳量
根據不同類型綠化的面積,可計算出本項目年綠化碳匯量為1.11tCO2,可降低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8.8%,具體數據如表5 所示。

表5 年綠化碳匯量計算表
2.1.3 運行階段碳排放
根據上述計算,取建筑運行年限為50年,電力排放因子取0.5721kgCO2/kW·h,可計算出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量為6243.60 tCO2,具體數據如表6 所示。

表6 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
2.2 建材生產和運輸階段碳排放計算
2.2.1 建材生產階段碳排放
建材生產階段的碳排放根據《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式6.2.1計算,主要建材碳排放因子可按標準附錄D 取值。 附錄D 中未給出的建材碳排放因子,筆者參考東南大學的相關研究[7]進行取值。
由項目采用BIM 設計模型,可直接導出項目各主要建材用量。 整理得出項目主要建材及碳排放因子清單如表7 所示。 由此計算出項目建材生產階段的碳排放量為4677.63 tCO2。

表7 項目主要建材用量及碳排放因子清單
2.2.2 建材運輸階段碳排放
建材運輸階段碳排放根據《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式6.3.1 計算,筆者統計了項目主要建材用量及材料生產地,并根據附錄E選擇合適的運輸方式,可得項目主要建材運輸距離及運輸方式碳排放因子清單(表8)。 由此計算出項目建材運輸階段的碳排放量為64.28 tCO2。

表8 項目主要建材運輸距離及運輸方式碳排放因子清單
綜上可得項目建材生產和運輸階段碳排放總量為4677.63+87.28=4764.91 tCO2。
2.3 建筑建造及拆除階段的碳排放計算
2.3.1 建筑建造階段碳排放
建筑建造階段碳排放計算可從機械設備臺班、施工工藝和建造流程幾個方面來進行計算[7]。 在計算時,筆者主要從施工工藝的不同,將施工碳排放分為耗電及耗油兩種情況進行計算。 耗電量可根據項目工地逐月用電量統計得出,從而通過電力碳排放因子得出碳排放量。 施工耗油主要由于現場機械設備運轉引起,建造階段的主要耗油工藝為開挖移除土方、平整土方和水平運輸[7],這部分耗油可以根據工程土方量進行計算。
該項目施工期為2019年6月—2021年8月,共27 個月,項目工地逐月用電量如圖2 所示。 可以看出,項目施工階段用電量受現場工藝的影響,用電量大致在4000~7000kW·h/月,平均每月用電量為5019 kW·h。 同時,用電量也受到春節假期、疫情停工(2020年2—3月)及土建和精裝施工轉換(2021年1月)等因素影響。 項目施工期內,總用電量為135533kW·h,碳排放量為77.54 tCO2。

圖2 施工逐月用電量
根據項目工程量決算清單,項目總土石方開挖量為11750m3,場地回填平整量為1655.8m3,余方外運量為10011.08m3,外運距離按20km 估算,計算可得項目耗油工藝產生的碳排放量如表9所示。

表9 耗油工藝碳排放量
綜上,項目建造階段碳排放量為77.54+59.63=137.17 tCO2。
2.3.2 建筑拆除階段碳排放
建筑拆除階段的計算不確定因素較多,可按照現有研究合理估算其碳排放。 筆者根據相關研究結論[7],建筑拆除階段碳排放量按照建筑總建材生產階段到建造施工階段產生的碳排放量的10%[7]來估算,其碳排放量為0.1×(4741.91+137.17)=487.91 tCO2。
綜上,建筑建造及拆除階段的碳排放總量為487.91+137.17=625.08 tCO2。
2.4 項目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綜上,該項目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為11633.59 tCO2,單位面積碳排放量為3906.38kgCO2/m2。其中運行階段碳排放量占比53.67%,建材生產與運輸階段占比40.96%,建造及拆除階段占比5.37%,具體數據如表10 所示。

表10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3 碳排放計算標準及減碳措施探討
3.1 計算標準尚待補充及完善
筆者在計算過程中發現,《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下文簡稱《標準》)中尚有部分計算方式需進一步完善,一些基礎數據還需要補充,下文舉例說明。
(1) 《標準》中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計算未納入辦公設備的能耗。 《標準》條文說明中認為這部分碳排放不確定性大,碳排放量占比不高,不影響對設計階段建筑方案碳排放強度優劣的判斷,因此建筑碳排放計算不納入家用電器、辦公電器、炊事等的碳排放量[5]。 但筆者在能耗模擬中發現,設備能耗需參與能耗模擬計算,其直接影響項目冷負荷計算,且該項目辦公設備能耗占總能耗比例為23%,占比較大。因此在本次計算中,筆者考慮了項目辦公電器能耗引起的碳排放量。 筆者建議,計算此部分碳排放時,設備功率密度可參照《公共建筑節能設計標準》附錄B 中表B.0.4-9設置。
(2) 《標準》對綠化碳匯的計算無相關規定。 筆者通過查閱文獻,選取了適用于該項目的綠化碳匯研究結果,計算得該項目綠化碳匯可降低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量8.8%,說明綠化碳匯是不可忽視的減碳方式。 在后續的標準修訂中,建議增加綠化碳匯計算方法。
(3) 《標準》中部分常用建材的碳排放因子欠缺,如建筑卷材等。 筆者采用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計算發現,該項目建筑卷材的碳排放量比保溫材料、外飾面材料等更大。 在后續的標準修訂中,建議逐步補充完善各種建材的碳排放數據。
(4) 《標準》中建筑拆除階段碳排放計算辦法可操作性不強。《標準》 中采用了與建造階段相似的方法計算拆除階段的能源用量,但拆除階段不確定性較大,不同拆除項目的工程量難以確定,拆除項目每計量單位的能耗系數無相關規定,造成計算較為困難。 筆者查閱文獻發現,我國對建筑拆除階段碳排放研究的數據較少。 通過比較不同文獻的計算方法和數據,筆者采用了一種較為普遍的方式來對這部分碳排放進行估算,以保證計算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在后續的標準修訂中,建議完善建筑拆除階段的相關計算方法和基礎數據。
3.2 對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探討
(1) 從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來看,建筑運行階段碳排放量最大,主要原因是其時間長、跨度大。 如果從年碳排放量來看,可呈現出“U”形分布(圖3),即建材的生產和運輸、建筑拆除碳排放量較大,運行階段較為平穩。 在現有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下,從舊建筑拆除到新建筑建成的3~5年,是碳排放量最大的階段。 綜上可知,在“雙碳”目標背景下,想要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就必須改變大拆大建的舊發展模式。

圖3 建筑全生命周期年碳排放量
(2) 建材生產與運輸階段的碳排放比例如圖4 所示,建材生產碳排放占98%,其中建筑主體結構材料生產碳排放比例高達77.4%,占建筑總排放量的31.7%。 建材生產引起的碳排放有排放量大、排放強度大等特點。 降低建材生產階段碳排放,可大幅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因此,采購碳排放量更低的綠色建材,抑或從源頭上減少建筑材料的使用,如利用既有建筑主體結構進行改造,采用可循環或可再利用的建材,可大幅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圖4 建材生產與運輸階段碳排放比例
(3) 土石方開挖、外運及建材運輸環節都是運輸過程中涉及的碳排放,這部分碳排放隨著運輸距離的增加,碳排放量將顯著增大。 由于該項目99%(按重量計)的建材均在本地采購,運輸距離不超過200km,且土石方外運的距離不大,運輸過程產生的碳排放僅占總碳排放量的1%。 因此,盡量采購本地建材,設計階段注意土石方平衡,施工階段合理控制土石方外運距離可降低運輸過程產生的碳排放。
(4) 在建筑運行階段,空調和照明用能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占比分別為48%和28%,是最主要的碳排放來源 (圖5)。 在后續的運營階段,項目的管理方可利用智慧化樓宇控制系統,在保證室內物理環境的同時,充分利用自然通風、 自然采光等措施,降低照明和空調的使用頻率,還可利用能耗監測系統,對樓宇的各分項能耗進行監控和分析,挖掘進一步降低能耗的可能性。

圖5 建筑運營階段各系統碳排放比例
4 結語
本文依據《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GB/T 51366—2019),以綠色建筑重慶市設計院建研樓工程為例,計算了項目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通過總結計算過程,從設備能耗的計算、綠化碳匯的計算、建材的碳排放因子欠缺、建筑拆除階段碳排放計算等方面對《建筑碳排放計算標準》的完善提出了建議。 通過碳排放計算數據的分析,對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路徑進行了探討。 隨著國家標準 《建筑節能與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規范》(GB 55015—2021)的發布,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建設方案和初步設計文件將包含建筑碳排放分析報告[10],建筑碳排放計算將隨著標準的執行迅速得到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