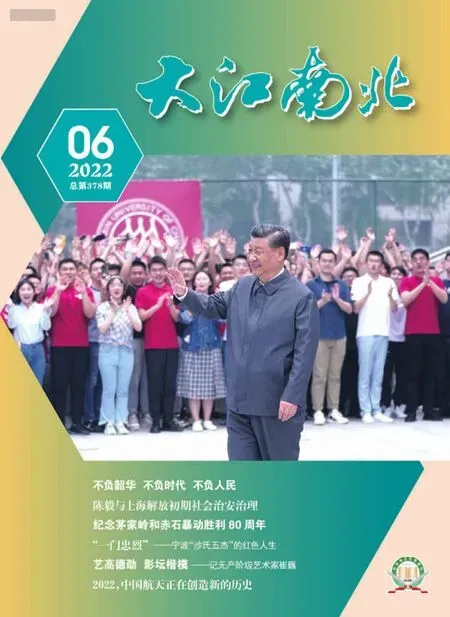張愛萍將軍與《揚(yáng)州日?qǐng)?bào)》
我從事新聞工作60多年,閑暇之余喜歡翻閱報(bào)刊,特別是過去的報(bào)紙。每當(dāng)這些泛黃的紙張?jiān)谖沂种猩成匙黜憰r(shí),總有一種特殊的情緒在心頭涌動(dòng),那些刊登在報(bào)紙上的人和事好像在這一刻突然鮮活起來,仿佛就發(fā)生在昨日一般。
《揚(yáng)州日?qǐng)?bào)》,這份誕生在新中國(guó)激情歲月的報(bào)刊,經(jīng)歷了篳路藍(lán)縷,最終玉汝于成。這份黨報(bào)與時(shí)代同行,穿越歷史風(fēng)云,從創(chuàng)刊伊始的八開二版小報(bào)到對(duì)開大報(bào),成為了江蘇省十強(qiáng)報(bào)紙,躋身于江蘇報(bào)業(yè)第一方陣。作為老報(bào)人,我感到無比激動(dòng)、無尚欣慰。更令我難忘的是,當(dāng)年,“揚(yáng)州日?qǐng)?bào)”這四個(gè)字還是由時(shí)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zhǎng)的張愛萍上將親筆題寫的呢。這背后發(fā)生的故事,還得從1965年說起……
《揚(yáng)州日?qǐng)?bào)》,先名《揚(yáng)州市報(bào)》,是揚(yáng)州市委機(jī)關(guān)報(bào)。當(dāng)年記者、編輯只有十人,都是來自黨政部門的骨干,我也有幸成為其中一員。社址設(shè)在永勝街40號(hào),借用市圖書館倉(cāng)庫(kù)的五間房屋辦公。夏天沒有電扇,冬天沒有火爐。我們每天收錄新華社電訊稿,靠收音機(jī)記錄新聞,后來使用老式模寫機(jī)收錄電訊稿。早上記者們出去采訪,晚上編輯部燈火通明,看稿、編稿、寫稿、畫版樣,無一人叫累,個(gè)個(gè)朝氣蓬勃,雖苦猶榮。當(dāng)時(shí),報(bào)社沒有專職校對(duì),都是記者、編輯兼職校對(duì)。有時(shí)新華社有重要新聞,到凌晨才能截稿。同志們風(fēng)趣地寫了一首打油詩(shī):“黃昏去校對(duì),黎明迎日歸。為了辦好報(bào),無怨又無悔。”
1965年9月2日至1966年4月27日,時(shí)任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zhǎng)的張愛萍上將,蹲點(diǎn)在揚(yáng)州地區(qū)邗江縣方巷公社方巷大隊(duì),開展轟轟烈烈的社會(huì)主義思想教育工作,向農(nóng)民宣傳毛澤東思想。得知這一消息后,報(bào)社派我常駐方巷采訪報(bào)道。當(dāng)時(shí)我是報(bào)社記者組長(zhǎng)、編委,同時(shí)來方巷蹲點(diǎn)的還有新華社記者鄭震孫。那天,大隊(duì)支書侯玉蘭領(lǐng)我和鄭震孫見張愛萍上將時(shí),張將軍伸出雙手握住我們兩人的手,連說:“歡迎,歡迎!歡迎二位記者來采訪報(bào)道,用你們手上的筆和相機(jī),多寫農(nóng)民,多拍農(nóng)民,多宣傳農(nóng)民,民以食為天啊!”

我們和張將軍同住在大隊(duì),同吃一鍋飯,同做力所能及的農(nóng)活。張將軍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日子一長(zhǎng),我們也就不拘束了。我們稱張將軍為首長(zhǎng),稱他的夫人李又蘭為李大姐。張將軍和李大姐稱我倆為“小姜”、“小孫”,我們都感到非常親切。一次,張將軍和我們閑聊,談到對(duì)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認(rèn)識(shí)。講到1933年,國(guó)民黨蔣介石發(fā)動(dòng)對(duì)革命根據(jù)地的第五次“圍剿”,調(diào)動(dòng)100萬軍隊(duì)向各地紅軍進(jìn)攻。他說:“這時(shí),博古把軍事指揮權(quán)交給共產(chǎn)國(guó)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們不了解中國(guó)實(shí)際情況,搬用了正規(guī)的陣地戰(zhàn)經(jīng)驗(yàn),指揮失誤,使紅軍多次受挫,日益陷于被動(dòng)。紅軍被迫離開蘇區(qū)進(jìn)行長(zhǎng)征,從出發(fā)時(shí)的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jǐn)U大會(huì)議,確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從此革命節(jié)節(jié)勝利。”
張將軍講到二萬五千里長(zhǎng)征時(shí),豪氣油然而生。他說:“英勇的紅軍將士和敵人進(jìn)行600余次戰(zhàn)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40座高山險(xiǎn)峰。長(zhǎng)征路上的苦難、曲折、死亡,檢驗(yàn)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理想信念,創(chuàng)造了氣吞河山的人間奇跡。長(zhǎng)征精神為中國(guó)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qiáng)大的精神動(dòng)力。1949年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我站在黃浦江邊,感慨萬千啊,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搞反革命政變,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殺的慘狀浮現(xiàn)在眼前。今天,上海回到了人民懷抱,可歌可泣,我不禁仰天高呼:‘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偉大啊!’”他講得深入淺出,活靈活現(xiàn),生動(dòng)感人,就像給我們上了一堂特殊黨課。我當(dāng)時(shí)脫口而出說道:“聽君一席話,勝上十堂課!首長(zhǎng),如果報(bào)社的全體編輯記者能聽到您的精彩講話,大家將會(huì)有多么的自豪啊!相信一定會(huì)提高思想覺悟,增強(qiáng)責(zé)任感和使命感,在新聞戰(zhàn)線上發(fā)光發(fā)熱!”張將軍立即說:“好啊!你安排時(shí)間,我到報(bào)社講講。”隨后,我便向報(bào)社領(lǐng)導(dǎo)匯報(bào)了這一喜訊。
那天由我?guī)罚瑥垖④姅y夫人李又蘭,加上新華社記者鄭震孫,從甘泉路邗江人武部駐地步行到當(dāng)時(shí)位于廣陵路86號(hào)的揚(yáng)州日?qǐng)?bào)社。張將軍身著褪色的軍便服,頭戴舊軍帽,腳穿解放鞋,李又蘭大姐衣著也很樸素。兩人一路上邊走邊看街景,偶爾問我這條街名、那家商號(hào)的來龍去脈,既無警察開路,又無地方黨政領(lǐng)導(dǎo)陪同,就像平常人逛街,一路走到報(bào)社來。

張將軍在報(bào)社做報(bào)告時(shí),除編輯部全體人員參加外,時(shí)任揚(yáng)州地委第一書記的胡宏和揚(yáng)州市市長(zhǎng)錢承芳也到場(chǎng)聆聽。張將軍在報(bào)告中講了方巷農(nóng)民如何學(xué)習(xí)毛主席著作,并結(jié)合自己追求真理、投筆從戎參加革命的親身經(jīng)歷,談共產(chǎn)主義人生觀,談革命理想,講得生動(dòng)形象、親切幽默。在報(bào)告中,他希望《揚(yáng)州日?qǐng)?bào)》辦得既要有指導(dǎo)性,又要有戰(zhàn)斗性,既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又要把人民群眾的心聲呼聲反映出來;要向默默無聞、艱苦奮斗的人們敞開真誠(chéng)的胸懷,傾注熾熱的情感為他們鼓與呼,做黨和人民之間的連心橋。張將軍就像一名教師對(duì)學(xué)生講課那樣既嚴(yán)肅又活潑,和我們這些年輕的記者、編輯交流,諄諄教導(dǎo)我們要努力成為又紅又專的黨的新聞工作者。他沒有講稿,娓娓道來,言淺意深,催人奮進(jìn),講了兩個(gè)多小時(shí),會(huì)場(chǎng)上的掌聲笑聲此起彼伏。
報(bào)告結(jié)束后,時(shí)任揚(yáng)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zhǎng)、主持報(bào)社工作的副總編輯鄭正請(qǐng)張將軍題詞,他欣然在四尺宣紙上揮毫,寫下“揚(yáng)州日?qǐng)?bào)”四個(gè)大字。1966年2月11日,《揚(yáng)州日?qǐng)?bào)》的報(bào)頭換上張?bào)w,在《揚(yáng)州日?qǐng)?bào)》發(fā)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編輯 盧天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