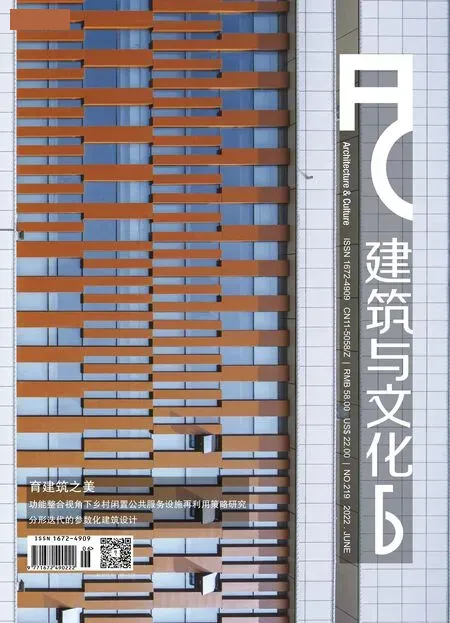建筑中的“巨構”與裝置藝術中的“巨物”
——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研究
文/葉洪圖 大連理工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副教授
羅 瑩 大連理工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碩士研究生
樂雷亞敏 大連理工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碩士研究生
1“巨構”與“巨物”沿革及衍化
1.1 建筑中的“巨構”沿革及衍化
“巨構”作為一種建筑學領域的思想概念,于20 世紀后由日本建筑師楨文彥明確闡述其定義。楨文彥在出版的理論專著《集合形態筆記》一書中,闡明了何為“巨構”——即“巨構”是指戰后時代的一種建筑和城市的概念,作為一種城市形式的設想,認為一個城市可以包裹在一個巨大且單一的人造結構或相對較少互相連接的結構中,運用大規模的建造方式與大量復合和集約化的布置方式的所建造的建筑體。巨構的典型特點便為一個“大型架構”且具有相對被壓迫感,極度關注在垂直和水平上皆進行擴展及演變,并考慮群眾使用的便利性。在城市發展速度愈來愈快的時代,解決城市與建筑之間在發展速度上的抵牾,成為了城市建造者們的目標。巨構的特點正可將其實現,成為當下城市建設合理的解決方案,突破傳統呈現新城市結構。
“巨構”的前提是以人的行為方式為根本,其形制與思想源于生活的自身結構且不再局限于建筑領域解決建筑與城市之間的脫節問題。在當代藝術中,逐漸被藝術家們引用其概念與思想作為藝術創作方法展開多樣化的應用,可以被當做“創造”的形式與思想途徑出現在藝術創作中,提出作為創作方法的新角度來服務當代藝術的作品呈現。在多元化語境中,“巨構”進行不斷的衍化,作為一種手法便于當代藝術家探討深層次的藝術本質,從而拉近藝術作品與大眾之間的距離,讓觀眾倍受感染并產生共鳴。
1.2 裝置藝術中的“巨物”的沿革及衍化
裝置藝術始于20 世紀60 年代,自杜尚的現成品藝術后不斷進行演進,堪稱當代藝術中占據主流位置的藝術形式,也有“環境藝術”之稱。從傳統藝術到現代藝術再到當代藝術中,裝置藝術作為當代藝術中一支強有力的分支,是一種把規律化強加給無規律變化的藝術現象,否定了不同形式的創作方法,限定了對各門類藝術手段的自由使用,且妨礙了藝術家對思想觀念的順暢表達。所以,裝置藝術始終呼吁并踐行著提高審美經驗與美感洞察力,從被忽視的邊緣角色逐漸充當為以多元化的藝術語言形態來代表當代藝術的重要角色。由此,巨大沉默物體即巨物形式的裝置藝術逐漸對傳統藝術界定產生巨大挑戰和反擊。
在如今的當代藝術中,超乎生活經驗的、巨型結構的裝置藝術作品正以高密度的頻率呈現。藝術家的巨型作品喚醒了人格結構最底層的潛意識——對巨物寄托崇拜、權力、恐懼等復雜表達。日日更新的藝術中,越來越多的當代藝術家利用此創作方法表達不同的情感寄托及語義指向,而這些巨物裝置作品成為當代藝術追求表現廣領域、深層次的必然產物。在巨型藝術作品與觀者無論是情感的互動還是行為再創造的交流的互動體驗下,激發更多可能性并超越創作目的。
2 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研究
2.1 基于跨領域概念——“巨構”的當代性轉化
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方法日益多元化,打破傳統的藝術形式與表達手法,不斷地進行多領域延伸。“巨構”作為建筑領域中的概念——試圖通過增強內部組織的流暢性與結構功能的雜交性來凸顯“巨構建筑”的城市性——將城市功能包裹在一個巨型的構成中。從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到磯崎新的“空中城市”,再從朗·赫倫的“行走城市”到庫哈斯的“成為建筑的志愿囚徒”,均是同一時期巨構建筑的典型構想,但在實踐中存在眾多局限使其變成烏托邦式的未來世界。如今,當代藝術家把“巨構”作為創作方法,將昨日的烏托邦視為早產的真理,挖掘思想角度及表現特征引入藝術創作中,實現跨領域的合理化表達。
于振立,中國當代藝術家。在輝煌時期選擇逃離喧囂嘈雜的“名利場”,退隱于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大黑山,重建藝術家內心的烏托邦,一味苦行地自我放逐27 年。在這27 年里,于振立建造了屬于自己的“巨構”工作室(圖1),與其說是“巨構”,不如說是“精神巨構”更為準確。

圖1 于振立工作室(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藝術批評家栗憲庭曾一針見血地說“他為自己修了座墳墓”,與其說墳墓,不如說是藝術家精神與觀念巨大的永恒沉默之物。對藝術家而言,這是最好的褒獎與贊美。工作室搭建在大黑山的半山坡處,綿延范圍達數千平方米,建筑材料基本均以廢物的重新利用來建造,試圖變廢為寶,化腐朽為神奇。以將近三十年如一日的持續創作與勞作,用撿拾來的垃圾材料、破磚爛瓦、空酒瓶、廢車輪、破電視、碎石頭等統統鑲嵌在墻上或地面,更有幾座“塔”型的雕塑用大量酒瓶有規則地相互排列鑲嵌而成(圖2),整個的建筑約使用了十幾萬個。于振立盡可能地用他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描述”這個巨型的空間結構,靠自己的雙手打造極具藝術性的建筑群體,并將自己的全部生命即生存本身用以介入,從而以藝術家個人工作室的建立為媒介連通了個體創造與社會公眾的橋梁,用獨特的“自囚”方式完成了自己烏托邦式的幻想。此番修行不但形成了空間中的巨構,更是將精神的巨構體現得淋漓盡致。正如他今天所為,如愿找到了卡夫卡小說中所講到的,人在死之前,找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于振立工作室為跨領域概念“巨構”的當代性合理轉換進行了完美的表達,巨構在當代藝術中不再只局限于結構形態和功能體系的展現,更需擁有一種作為龐大的精神載體上下貫通的意識形態——承載時間的體量和生命的厚度。

圖2 于振立工作室外的塔型雕塑(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跨媒介巨構是巨構當代性轉化的形式之一,是由當代藝術家牟森所開創的一種媒介創作品類。跨媒介巨構,在一定的情景設置中,以各種裝置媒介或與表演形式相結合講演一種敘事性的存在。跨媒介:Intermedia,指媒介物、萬事萬物在媒介之間。跨媒介巨構可以穿插在不同學科之間,依然能夠形成交融的鏈接感,在結構特點上繼承了“巨構”的大形式與大體量,并混合多種媒介。企圖在策展與演出中找到平衡點,相互影響、相互呈現。在2016 上海雙年展中,《存在巨鏈——行星三部曲》作為牟森的跨媒介巨構參展作品(圖2、圖3),名字來源于諾夫喬伊的同名著作,將“存在”作為一種連續不斷的巨大鏈環的觀點,以三部曲的結構呈現:無限視角、時間盡頭和黑暗深處。所有觀者都自動充當為作品中演員的角色,與場景融為一體。在這個展覽中共集合了四十八件作品,并在媒介的選擇中,囊括聲光電等多種類別,使這件跨媒介巨構作品在藝術語言中發揮出更具技術性的表達與當代性轉化。

圖3 《存在巨鏈——行星三部曲》展覽現場(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圖4 《存在巨鏈——行星三部曲》展覽現場(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2.2 裝置藝術中“巨物”形式的合理應用助于彰顯藝術作品的意義
裝置藝術作為當代藝術中的重要角色,在界定范圍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借助多元化的藝術形式,以單一個體或復數群體形式,融入當代藝術語境且獨具意蘊。“巨物”作為當代藝術家在裝置藝術中愈來愈頻繁使用的創作方法,有利于凸顯作品的特征并對作品與觀者的互動影響更強烈。但是,在高密度的當代藝術“巨物”作品中,此方法的運用變成為了藝術而藝術的“便捷渠道”,止步于形式化表達,顯然這種渠道是非良性的,誤讀了方法的根本目的。所以,裝置藝術中“巨物”形式的合理應用是藝術創作的基本前提,且對彰顯藝術作品的意義更為有效。
2021 年11 月6 日,“徐冰:藝術卡門線”在紅磚美術館順利展出。這場獨特的展覽圍繞的重點是徐冰的“巨物”裝置藝術作品——“徐冰天書號”(圖5)藝術火箭展開。雖然基本元素來源于35年前的舊作,基于文字字形的解構創作,現采用與科技結合的藝術手段將符號化的文字創作置于全新的載體與環境中,并且以全新的視覺感受所呈現時,便賦予了全新的意義及思想空間。徐冰認為,文字作為文化之根本,對文字的解構與創造便是對本質思維產生強烈的沖擊。而“徐冰天書號”將這些無所指的文字發射至太空,是對藝術創作打開更多的思想空間并與科技進行結合的鋪墊。其作品也通過“巨物”形式的表達增進了觀者的當下性、互動性、在場性,做出合理化表達。

圖5 《天書號》展覽現場(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在經濟文化占主體的今天,眾多購物中心都望通過載體的呈現凸顯全部項目,并促使消費者形成快速記憶。而載體通常是選用裝置作品為代表,體現商業空間下藝術裝置的更多功能性。于是“巨物”作為藝術家創作的方法,巨型裝置就演變成了最好用的一種手段。較具代表性的成都IFS,在商場的外立面上以巨型裝置——一只代表成都城市名片的熊貓形象以爬墻的姿態,贏得交口稱譽。藝術家Lawrence Argent 為其取名為:“I Am Here”(圖6)。設計初衷為望通過此作品的展示引發人們在城市飛速繁榮的背景下,關注自身存在的內外變化,并提醒人們對待地球上的生靈都應像關愛熊貓一樣去用心保護。這件“巨物”裝置不但吸引了流量、提升了商業效益,更凸顯了藝術家更直觀、有效合理應用創作方法的影響意義。

圖6 《I Am Here》(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當代藝術家達明安·赫斯特在籌備近十年的《難以置信的殘骸珍寶》中,其中一件約19 米的巨型裝置雕像《拿著碗的惡魔》(圖7)尤為突出,其原型來自18 世紀藝術家、詩人William Blake 的手稿。在這場巨大規模和歷經超長時間跨度的展覽中,這件作品以巨大的體量和十足的勇氣劃分開傳統美學的權威分類與結構,堪稱赫斯特藝術生涯中絕無僅有的突破。

圖7 《拿著碗的惡魔》(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3作為當代藝術家創作方法——建筑中的“巨構”與裝置藝術中的“巨物”的區別
當代藝術家運用“巨構”與“巨物”作為創作方法,在藝術作品的表達中存在界限模糊、充滿交集的現象。由于在概念的解釋上均具有結構復雜且意識形態巨大的共通性,所以在初步了解的背景下并不好直接劃分,但深入探究“巨構”與“巨物”這兩種創作方法的藝術形式與思想內涵后,兩者之間具有鮮明的區別展現。
3.1“巨構”與“巨物”的形式區別
在“巨構”與“巨物”的表現形式上,當代藝術中的“巨構”偏向于利用巨型的空間結構集合多類媒介抑或是巨大體量的復數元素在限定場域內進行充分表達;而“巨物”偏向于以單一的巨型個體裝置,將材料進行獨具藝術性施展的同時,給予觀者較具沖擊及反差的視覺感受,打破固化的交流形式。
3.2“巨構”與“巨物”的思想區別
在“巨構”與“巨物”的思想中,當代藝術中的“巨構”思想指向性在于以人性的自由、社會的擔當、科技的發展、愛為創造,對理想化的想象給予烏托邦式幻想的滿足,并且注重解決心理訴求與“新世界”的探索;而“巨物”思想則著重于探索以新的視覺呈現方式來獲取人們的視線與思考,以單一的巨型裝置收獲大群體在多角度的精神啟迪。
結語
綜上,在模糊學科邊際的當下,學術研究還是勿糾結于學術概念借用的同一性。“巨構”與“巨物”異同,正是探究裝置藝術家創作方法的解鎖密碼。借用“巨構”所做的創作以建筑學巨型構造承載其當下之觀念,“巨物”亦是如此。外化之物皆為觀念載體。
隨著當代藝術的發展與概念延伸,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也隨時代變遷而變化。傳統藝術對人們的視覺感受的刺激逐漸降低,時常給人呆板、乏味的感覺,失去了現代人應有的知覺敏感度。人們更希望看到超出原有認知、更具突破性的作品。由此,建筑中“巨構”與裝置藝術中“巨物”的表達范疇在當代藝術家的吸納與轉述下,更具開放性和多元化,滿足了藝術家與觀者的需求。使用“巨構”與“巨物”作為創作方法均是當代藝術家主觀的有意為之,而非被動的模仿或者偶然的出現,甚至可以把其作為藝術家自身或藝術作品獨特語言的存在。不同藝術家通過對兩種方法注入不同的含義,使得創作在意義上變得豐富、活潑起來,并且引發人們的深入思考,以此來揭示人類自身或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及美好期待,賦予作品特殊意義。
當代藝術家藝術作品紛繁蕪雜,但值得肯定的是,無論觀念如何轉變,何種藝術創作思想的產生都依賴于精準的創作方法得以實現,所以外在的表現形式充當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當今藝術創作方法多樣化,藝術家將“巨構”與“巨物”作為跨學科領域概念引入、雜糅甚至再創造,皆為創作方法提供可能,區分度模糊也成為一種必要。將兩個概念只看共同點便定義為同義,并非一種十分理性的界定和認識。無須糾結同一性,關注差異性和多元性,結合當代人的觀念,進行當代性轉化是為正確的認知方法。對“巨構”與“巨物”進行深入理解不但有助于藝術作品的合理化與創新性地表達,更對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邁出了重要一步,開拓了全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