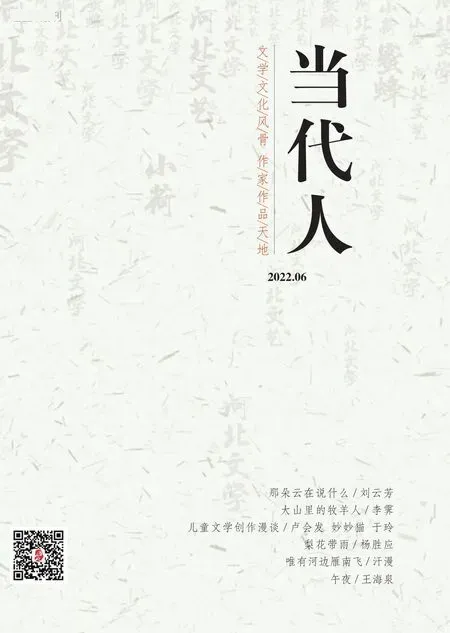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漫談
盧會(huì)發(fā) 妙妙貓 于玲
盧會(huì)發(fā),現(xiàn)就職于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huì)。致力于兒童文學(xué)研究,在《文藝報(bào)》《河北日?qǐng)?bào)》等發(fā)表兒童文學(xué)評(píng)論作品多篇。
妙妙貓,本名張娟,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兒童文學(xué)研究會(huì)會(huì)員。曾獲冰心兒童文學(xué)新作獎(jiǎng)、香港青年文學(xué)獎(jiǎng)兒童文學(xué)組冠軍、石家莊市精神文明建設(shè)“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上海市作協(xié)幼兒文學(xué)獎(jiǎng)、謝璞兒童文學(xué)獎(jiǎng)等。著有《失物旅行箱》《琥珀,琥珀》《風(fēng)先生郵局》等。
于玲,中國(guó)戲劇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曾獲河北文藝貢獻(xiàn)獎(jiǎng)、“大白鯨”原創(chuàng)幻想兒童文學(xué)獎(jiǎng)、《東方少年》年度重點(diǎn)作品扶持項(xiàng)目?jī)?yōu)秀獎(jiǎng)等。出版有長(zhǎng)篇兒童小說(shuō)《第十場(chǎng)戲》。
作為主流文學(xué)的一個(gè)分支,兒童文學(xué)發(fā)展出了自己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路徑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談?wù)搩和膶W(xué)有多個(gè)維度,比如創(chuàng)作的維度、閱讀的維度、兒童視角的維度、成人視角的維度,乃至地域的維度等。受《當(dāng)代人》編輯部邀約,與妙妙貓、于玲兩位作家一起聊聊兒童文學(xué)相關(guān)話題。我除了關(guān)注、研究?jī)和膶W(xué),還是一個(gè)孩子的父親,算是兒童文學(xué)的讀者,雖沒(méi)經(jīng)過(guò)授權(quán),但我同時(shí)以讀者代表的身份,與兩位作家一起,談?wù)効捶ā?/p>
向光生長(zhǎng)——關(guān)于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
盧會(huì)發(fā):我們先從個(gè)人創(chuàng)作談起吧,二位從事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一段時(shí)間了,寫出了很多深受孩子們喜歡的作品。我有些好奇,當(dāng)初是怎樣的機(jī)緣,令你們走上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條路?
妙妙貓:從小到大,我就非常喜歡看一些有趣的兒童讀物,有了女兒之后,在給她講故事的同時(shí),也激發(fā)了自己想為孩子創(chuàng)作故事的欲望。此外,我的本職工作是一名編輯,在平日的組稿、審稿過(guò)程中,也希望用自己的語(yǔ)言構(gòu)建一方獨(dú)特的天地。在一番思考之后,我開(kāi)始嘗試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幸運(yùn)的是,在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條路上,許多有經(jīng)驗(yàn)的編輯老師給予了我莫大的鼓勵(lì),這讓我堅(jiān)定了繼續(xù)創(chuàng)作下去的信心。
于玲:說(shuō)來(lái)慚愧,其實(shí)現(xiàn)在我還是一名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新兵,走上這條路,或許是天意使然。我在省戲劇家協(xié)會(huì)工作,主攻劇本創(chuàng)作,我對(duì)兒童題材比較敏感,也一直關(guān)注,所以自覺(jué)地寫了不少兒童劇作品。說(shuō)實(shí)話,把劇本搬上舞臺(tái)是個(gè)繁雜的大工程,于是我想,干脆把那些不能在舞臺(tái)上呈現(xiàn)的創(chuàng)意以文學(xué)作品的形式展示出來(lái),就這樣開(kāi)始了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大概有一年的時(shí)間,我自己沉浸在純粹的寫作中,根本沒(méi)有考慮過(guò)其他的問(wèn)題。經(jīng)過(guò)那段磨礪,我感覺(jué)寫東西流暢自如了許多。
盧會(huì)發(fā):兩位老師的創(chuàng)作緣起,在我看來(lái)都是來(lái)自工作中閃現(xiàn)的靈感,也可以理解為對(duì)本職工作和個(gè)人愛(ài)好的延伸。在我的理解中,兒童文學(xué)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但是一點(diǎn)也不簡(jiǎn)單,是一種非常復(fù)雜的文體,甚至比寫給成年人閱讀的作品更有難度,也牽涉更為復(fù)雜的創(chuàng)作和閱讀倫理。從“難”或“易”的程度上,二位怎么理解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
妙妙貓:相比于成人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兒童文學(xué)要求創(chuàng)作者具有一顆純粹向上的童心,同時(shí)還要用孩子感興趣的語(yǔ)言去貼近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好的兒童文學(xué)作品應(yīng)該是一座溝通成人和孩子心靈的橋梁,應(yīng)該是富有正能量的,而且應(yīng)該是具有時(shí)代性的。我個(gè)人認(rèn)為,這也是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的難點(diǎn)所在,如何讓孩子看到真善美,懂得真善美,學(xué)會(huì)真善美,也是身為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的我在不停思考的問(wèn)題。
于玲:文學(xué)作品的難易程度很難用一個(gè)清晰的標(biāo)碼去界定,就我個(gè)人來(lái)說(shuō),之前我也嘗試過(guò)寫散文、小說(shuō),但轉(zhuǎn)向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后,我感覺(jué)自己寫得更加順暢。因?yàn)閺氖逻^(guò)舞臺(tái)劇編劇,我比較擅長(zhǎng)構(gòu)架故事。在寫故事的過(guò)程中,我的腦海中自然而然就生發(fā)出相應(yīng)的場(chǎng)景和人物。他們?cè)谖业哪X海中對(duì)話,并自己推動(dòng)劇情發(fā)展,而我更像是一個(gè)旁觀者,記錄下這個(gè)故事而已。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方式,每個(gè)人也都有自己適應(yīng)的領(lǐng)域。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會(huì)覺(jué)得寫起來(lái)容易很多。
盧會(huì)發(fā):不得不說(shuō),有很多創(chuàng)作者在寫作的過(guò)程中極易因?qū)ψ髌冯y易的理解不同而走入“低幼化”的誤區(qū),“低幼化”是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易犯的一種毛病,如何處理兒童文學(xué)寫作過(guò)程中“低幼化”與直面生活復(fù)雜性的關(guān)系,從而達(dá)到藝術(shù)上的平衡?
妙妙貓:兒童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很廣闊,幼兒文學(xué)也是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一個(gè)非常重要的體裁,就像著名兒童文學(xué)作家林良所言,好的幼兒文學(xué)就像是一門淺語(yǔ)的藝術(shù)。從我個(gè)人創(chuàng)作上來(lái)講,幼兒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同較為深刻的兒童小說(shuō)相比,無(wú)論是字?jǐn)?shù)還是主題呈現(xiàn)方式都是對(duì)語(yǔ)言創(chuàng)新能力的考驗(yàn),好的幼兒文學(xué)更需要?jiǎng)?chuàng)作者展示出與眾不同的靈動(dòng)性和美感。當(dāng)然,如果跳出幼兒文學(xué)創(chuàng)作,面對(duì)受眾年齡層更高的兒童文學(xué)體裁時(shí),在語(yǔ)言和主題的深入挖掘上,該如何觀照現(xiàn)實(shí)、折射現(xiàn)實(shí)、呈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要求就更上了一個(gè)層次,語(yǔ)言的表達(dá)上也更向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語(yǔ)言靠攏。
于玲:現(xiàn)在兒童文學(xué)作品實(shí)行分齡制,一些低幼讀物的存在是合理且十分必要的。但在一些作品中,作者在寫作時(shí)是故作“低態(tài)”,在內(nèi)容和表達(dá)方式上呈現(xiàn)一種不正常的“低幼化”。那些創(chuàng)作者的初衷可能是想保護(hù)兒童的純真,把這世界最美好的事物展示給他們。但世界也有陽(yáng)光暫時(shí)照不到的地方,小讀者成長(zhǎng)到一定階段,會(huì)或多或少接觸到這些問(wèn)題,比如學(xué)校的霸凌問(wèn)題,家庭矛盾問(wèn)題,財(cái)富與面子問(wèn)題等等,如果一味回避這些,反而讓小讀者產(chǎn)生疏離感。我覺(jué)得沒(méi)有必要回避,在作品中提出合理的辦法,帶著孩子們穿過(guò)迷霧尋找到光,這也是作品的向光性,同時(shí)是兒童文學(xué)很重要的特性。
盧會(huì)發(fā):藝術(shù)上的絕對(duì)平衡是不存在的,在兒童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中,可以說(shuō)“兒童本位”觀被視作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金科玉律,這也是在創(chuàng)作中可能產(chǎn)生“低幼化”的原因之一,但兒童文學(xué)所期待的“理想讀者”實(shí)際上有兩種,一是孩子,一是家長(zhǎng),所以也會(huì)產(chǎn)生過(guò)于成人化的問(wèn)題。二位在創(chuàng)作中是否會(huì)考慮這些因素?讀者在哪些方面的潛在需求會(huì)影響你們的創(chuàng)作?
妙妙貓:一部好的兒童文學(xué)不應(yīng)該只是孩子喜歡看,成人也應(yīng)該喜歡讀。就像《小王子》《柳林風(fēng)聲》這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經(jīng)典讀物,它們的魅力在于常讀常新。當(dāng)下兒童文學(xué)作品的閱讀更強(qiáng)調(diào)親子共讀,我的創(chuàng)作之中也在思考融入更多的現(xiàn)實(shí)主題,比如親子教育、親子陪伴、課業(yè)壓力等等,當(dāng)然這些主題的融入不應(yīng)該是枯燥的、說(shuō)教式的。對(duì)此我在努力嘗試用童話特有的語(yǔ)言和表達(dá)方式,希望孩子們看了會(huì)有不一樣的收獲,家長(zhǎng)看了也會(huì)產(chǎn)生情感上的共鳴。在平時(shí)的創(chuàng)作中,讀者的潛在要求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重要的參照點(diǎn),比如對(duì)故事趣味性的要求和對(duì)當(dāng)下熱點(diǎn)主題的觀照程度,這些我都會(huì)思考,然后盡可能地融入到作品中。C7C46967-FEBA-473C-8AAF-0FC956033F0D
于玲:我在創(chuàng)作的過(guò)程中其實(shí)是非常自我的,首先會(huì)把自己的想法都融入到作品中來(lái)。而修改階段,就是約束自我意志的時(shí)刻,這時(shí)候我會(huì)充分考慮閱讀者的感受。其實(shí)我認(rèn)為作者就是自己作品最好的讀者,沒(méi)有誰(shuí)比你更在乎自己的作品。我寫完?yáng)|西后,都會(huì)放一放,適當(dāng)“發(fā)酵”,多改幾次,修改的過(guò)程可以算作是個(gè)性向社會(huì)性的妥協(xié)。關(guān)于讀者對(duì)創(chuàng)作的影響問(wèn)題,我想談一個(gè)社會(huì)現(xiàn)象,就是有些出版機(jī)構(gòu)中存在的跟風(fēng)問(wèn)題,看到熱門圖書便立刻策劃類似選題。這其實(shí)就是市場(chǎng)對(duì)閱讀行為的反饋,也可以說(shuō)是讀者對(duì)創(chuàng)作者的影響。創(chuàng)作者可以迎合讀者的需求,但一定要寫出自己的特色,切忌一味模仿,還是要堅(jiān)定自己的創(chuàng)作初心。
盧會(huì)發(fā):正如于老師所提到的圖書出版現(xiàn)象,其本質(zhì)也是讀者對(duì)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產(chǎn)生的間接影響。變遷中的童年文化、商業(yè)消費(fèi)文化和新媒介文化不可避免地滲入到兒童文學(xué)的藝術(shù)肌體中,同時(shí)也帶來(lái)了兒童圖書消費(fèi)量的急劇攀升。在極大推動(dòng)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同時(shí),也給創(chuàng)作帶來(lái)一些干擾。你們有沒(méi)有受到過(guò)市場(chǎng)因素的影響?又是如何處理創(chuàng)作與市場(chǎng)關(guān)系的?
于玲:我曾經(jīng)被某文化公司約稿,參與“山海經(jīng)”主題童書創(chuàng)作。說(shuō)實(shí)話,市面上已經(jīng)有很多類似的作品,而邀約方并沒(méi)有提出新的創(chuàng)意,而是照搬市場(chǎng)上的暢銷書形式,我拒絕了。我更希望寫一些有新意、有自我個(gè)性的東西。一味地模仿,制造出大量的雷同品,是對(duì)讀者的不負(fù)責(zé)任,我們應(yīng)該懂得其中的取舍。
妙妙貓:作者寫出的作品終歸是要面向市場(chǎng)的,當(dāng)然也會(huì)受到市場(chǎng)因素的影響。我個(gè)人有同樣的感受,當(dāng)一類兒童文學(xué)讀物成為熱點(diǎn),市面上就會(huì)出現(xiàn)跟風(fēng)的熱潮,編輯們渴望多出熱點(diǎn)書、現(xiàn)象書,這對(duì)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來(lái)說(shuō),在寫作形式和主題上無(wú)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或多或少會(huì)存在為了模仿熱點(diǎn)書而寫作的現(xiàn)象。在創(chuàng)作中,我個(gè)人還是希望多寫從內(nèi)心里流淌出來(lái)的好句子、好故事,它應(yīng)該是足夠真誠(chéng)的,也應(yīng)該是經(jīng)得起時(shí)間考驗(yàn)的。
盧會(huì)發(fā):兒童類圖書出版火熱現(xiàn)象的另一個(gè)重要表現(xiàn),就是大量外國(guó)兒童文學(xué)作品的引進(jìn)和譯介,其作品在消費(fèi)者接受度和評(píng)價(jià)上,似乎超過(guò)本土原創(chuàng)作品。而在本土的創(chuàng)作中,長(zhǎng)盛不衰的題材是神話和民間傳說(shuō),但面對(duì)新的時(shí)代背景,傳統(tǒng)題材如何出新是個(gè)大問(wèn)題。
于玲:我們需要用創(chuàng)新手段去傳承和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文化,其與兒童文學(xué)相結(jié)合就是一種非常好的形式。近年來(lái),故宮、敦煌以及戲曲、傳統(tǒng)技藝等有著獨(dú)特民族文化背景的題材紛紛登上兒童文學(xué)的舞臺(tái),有許多作品都既叫好又叫座。如伍劍的《鋦瓷》《老錦春》,張忠誠(chéng)的《米罐》等。那些離我們很遠(yuǎn)的制作工藝,隨著這些鮮活的故事一一展現(xiàn),讀者不僅能記住一個(gè)故事,同時(shí)還能了解一門技藝。還有虛構(gòu)題材的作品,比如常怡的《故宮里的大怪獸》《敦煌奇幻旅行記》,以及以漫畫形式對(duì)傳統(tǒng)故事進(jìn)行重新演繹的作品,也非常受讀者歡迎。其實(shí)對(duì)創(chuàng)作者來(lái)說(shuō),更愿意親近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文化,從中挖掘出優(yōu)秀寫作選題。
妙妙貓:我小時(shí)候就非常喜歡看神話傳說(shuō)和民間故事,這些故事不但富有趣味而且給人以啟迪,同國(guó)外引進(jìn)的翻譯作品相比,富有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元素,更接地氣。如何將傳統(tǒng)文化與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深度融合,以童話創(chuàng)作為例子,童話本身以天馬行空的想象為基礎(chǔ),這其實(shí)和神話傳說(shuō)、民間故事中的想象色彩是相通的,在某種程度上,古今的故事是可以借助無(wú)限的想象相融合的。我曾經(jīng)嘗試將《山海經(jīng)》中的想象元素融入到幻想小說(shuō)《失物旅行箱》中,我發(fā)現(xiàn),當(dāng)一些中國(guó)元素融入到童話世界中時(shí),整個(gè)故事也有了不一樣的趣味性。
盧會(huì)發(fā):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確實(shí)為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資源,但不容忽視的一個(gè)問(wèn)題是時(shí)代的更迭所帶來(lái)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jià)值觀念、審美趣味的改變。少年兒童視野的擴(kuò)大、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和觀念結(jié)構(gòu)的更新,看待事物的眼光、審美趣味的不斷變化等,使少年兒童的精神世界更加復(fù)雜、多元,代溝在這個(gè)時(shí)代加速形成。
于玲:的確如此,現(xiàn)在接收信息無(wú)比便利,兒童與少年的視野開(kāi)闊度也已今非昔比。這是一個(gè)很大的挑戰(zhàn)。我們應(yīng)該與時(shí)俱進(jìn),去深入了解少年兒童的生活,盡量貼近他們的語(yǔ)言和思維,用他們接受并認(rèn)可的敘述方式講故事。但我想無(wú)論社會(huì)怎樣發(fā)展,人性之美永恒不變。作為寫作者,抓住這點(diǎn)也可以以不變應(yīng)萬(wàn)變。
妙妙貓:每個(gè)時(shí)代有每個(gè)時(shí)代的特點(diǎn),每個(gè)時(shí)代的孩子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就要求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除了觀照自己的童年故事,還需要細(xì)膩地觀察、刻畫當(dāng)下孩子們的童年故事。一個(gè)孩子的世界其實(shí)是大有寫頭的,從家庭到學(xué)校,從親人到身邊的伙伴,從突然而至的喜悅到不可言說(shuō)的煩惱……孩子的世界就像一個(gè)五彩斑斕的萬(wàn)花筒,需要我們肯花時(shí)間,靜下心來(lái)觀察,細(xì)細(xì)思考,細(xì)細(xì)描摹。
生生不息——關(guān)于河北兒童文學(xué)的地域熱點(diǎn)
盧會(huì)發(fā):時(shí)代變遷積淀了濃厚的文化傳統(tǒng),也產(chǎn)生了眾多優(yōu)秀的經(jīng)典作品。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河北的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成績(jī)斐然,特別是軍事題材、戰(zhàn)爭(zhēng)題材兒童文學(xué)作品,諸如徐光耀的《小兵張嘎》、邢野的《王二小的故事》等。這些經(jīng)典佳作揭示出一個(gè)問(wèn)題,就是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地域文化和時(shí)代生活的緊密關(guān)系,當(dāng)下的創(chuàng)作中這種情況似乎有些弱化。二位怎么看待這個(gè)問(wèn)題?
妙妙貓:河北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全國(guó)的成績(jī)是十分卓著的,徐光耀前輩的《小兵張嘎》等經(jīng)典兒童文學(xué)作品堪稱河北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地域文化融合相對(duì)弱化這個(gè)問(wèn)題,我想部分緣于科技的高速發(fā)展,特別是網(wǎng)絡(luò)、手機(jī)的廣泛使用,人們接觸的文學(xué)體裁更為寬泛,可以閱讀到的作品數(shù)量也劇增。特別是近年來(lái)幻想小說(shuō)和科幻小說(shuō)在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所占的比例進(jìn)一步加大。個(gè)人創(chuàng)作方面,作品中如何巧妙地融入河北地域文化也是我近期一直在嘗試和渴望突破的。地域文化與時(shí)代生活如何融合得生動(dòng)有趣,讓孩子們?cè)敢庖蛔x再讀,這考驗(yàn)的其實(shí)是一位創(chuàng)作者的筆力和腦力,需要花大量的時(shí)間不斷學(xué)習(xí),再學(xué)習(xí)。
于玲:您提到的這些經(jīng)典作品都跟時(shí)代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是時(shí)代造就了這些作品,形成經(jīng)典的流行。當(dāng)今文化產(chǎn)品很豐富,信息資訊繽紛繚亂,對(duì)閱讀行為形成了強(qiáng)有力的干擾,很難再有一部作品會(huì)像那個(gè)時(shí)代一樣產(chǎn)生全民轟動(dòng)的效應(yīng)。但任何事物都有利弊,網(wǎng)絡(luò)及新媒體的應(yīng)用同樣拓寬了文學(xué)作品的展現(xiàn)形式,一部有影響力的作品可以改編成漫畫或影視作品,人們可以多角度了解它。我們逃離不了時(shí)代,也無(wú)法干涉時(shí)代,順應(yīng)它,提高自己的創(chuàng)作水平,才可吸引更多讀者的關(guān)注。地域文化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影響可以說(shuō)是一直存在的。曹文軒、彭學(xué)軍、王勇英、小河丁丁等,他們大部分的作品里都帶有很顯著的地域特色,那些獨(dú)特的人文和地理風(fēng)貌帶給讀者非常新奇的閱讀體驗(yàn)。這種獨(dú)特性是他人模仿不來(lái)的,我們?cè)趯懝枢l(xiāng)和童年的時(shí)候,也總會(huì)帶入那種時(shí)代、地域的風(fēng)情。結(jié)合自己的真實(shí)體會(huì)深入挖掘,每個(gè)創(chuàng)作者都具備寫出獨(dú)特作品的可能性。
盧會(huì)發(fā):經(jīng)典作品持久的生命力和其深遠(yuǎn)的影響力無(wú)不受益于文學(xué)潮流,從文學(xué)潮流論,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整個(gè)文壇的氣象是一致的。比如,在傳統(tǒng)文學(xué)中,河北文壇現(xiàn)實(shí)主義是主流傳統(tǒng),在這一點(diǎn)上,表現(xiàn)非常明顯。
妙妙貓: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其實(shí)和成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大氛圍是一致的,兒童文學(xué)也需要多出經(jīng)典作品,多出富有時(shí)代意義和歷史價(jià)值的作品。現(xiàn)在,對(duì)現(xiàn)實(shí)主義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呼聲越來(lái)越高,現(xiàn)實(shí)兒童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也成為一大熱潮,這其實(shí)也是廣大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文化自信的體現(xiàn)。
于玲:兒童文學(xué)市場(chǎng)上,以童話、幻想文學(xué)為代表的虛構(gòu)類作品占據(jù)了相當(dāng)比例,但現(xiàn)實(shí)題材作品依然是當(dāng)下童書市場(chǎng)的主力軍。現(xiàn)實(shí)題材作品所涉及的內(nèi)容范圍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比如體育題材、科研題材、校園題材等等。相對(duì)于虛構(gòu)類作品,它們有了“現(xiàn)實(shí)”的基礎(chǔ),更加有“真實(shí)”的力量,也更易引發(fā)共情。我對(duì)去年剛讀過(guò)的兩本書印象特別深刻,《烏蘭牧騎的孩子》和《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二者描摹的都是宏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本來(lái)嚴(yán)肅的主題通過(guò)兒童的視角,一下子變得輕靈起來(lái),讓人更覺(jué)親近。
盧會(huì)發(fā):兒童文學(xué)是文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經(jīng)過(guò)與兩位老師的探討,對(duì)二位的創(chuàng)作近況有了進(jìn)一步了解,同時(shí)感謝分享寫作的經(jīng)驗(yàn)。燕趙大地有著深厚悠遠(yuǎn)的人文歷史和獨(dú)特的風(fēng)土人情,為我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扎實(shí)的根基。相信我們河北的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會(huì)有進(jìn)一步長(zhǎng)足的發(fā)展。再次致謝二位。
編輯:王瑜C7C46967-FEBA-473C-8AAF-0FC956033F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