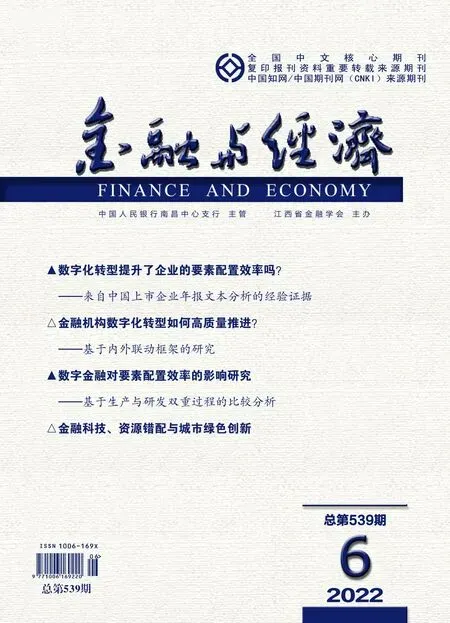數字金融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研究
——基于生產與研發雙重過程的比較分析
■童 燕,靳來群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儼然已經不適應我國當下經濟增長的實際需要,我國經濟增長模式也正在朝著依靠全要素生產率(TFP)為動能的“集約型”增長模式切換和實踐(程名望等,2019)。除了技術進步創新外,要素的配置優化過程對提高TFP 至關重要。中央工作會議多次強調“通過糾正結構性扭曲,優化要素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加完善的金融體系為優化要素配置提供著重要的支撐,這也是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和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原因所在。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興起和發展,使得傳統金融與數字技術能夠深度融合,數字金融應運而生(黃益平和黃卓,2018)。那么數字金融能否優化要素配置?
關于數字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主要從經濟規模擴張的角度展開了分析,如居民消費、中小企業成長、創業等方面。其中,張勛等(2020)研究發現數字金融顯著地促進了居民消費,且對收入較低家庭的作用更加明顯。汪洋等(2020)發現數字金融通過緩解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顯著地驅動了企業成長。謝絢麗等(2018)指出數字金融發展將顯著促進創業,尤其是城鎮化率較低的省份和注冊資本較少的微型企業,并且張勛等(2019)進一步指出數字金融發展也將顯著地促進農村居民創業。錢海章等(2020)在總結前期研究的基礎上,以人均GDP 增長作為被解釋變量,進一步佐證了數字金融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貢獻。不僅如此,部分研究也進一步從生產效率提升的角度對數字金融的作用展開了實證檢驗。如唐松等(2020)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發展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顯著地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陳中飛和江康奇(2021)指出數字金融發展將顯著地提升企業TFP,且對民營企業、成長型企業及中西部地區企業作用更加明顯。
要素配置優化對于提升生產效率至關重要。Hsieh & Klenow(2009)在開創性地提出企業間要素錯配評估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我國工業企業數據測算指出,企業間生產要素錯配導致我國總體TFP 損失了80%左右。邵宜航等(2013)在Hsieh & Klenow(2009)測算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測算發現,若實現企業之間生產要素配置優化將使我國TFP 提高200%以上,足以見得我國生產要素錯配非常嚴重。除了生產過程中的要素錯配問題外,我國研發過程中的要素錯配也非常嚴重。近年來,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國研發支出快速增加,且規模也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然而我國TFP增速及相對水平卻都依然較低,粗放式的研發投入并沒能有效地轉化為TFP,其中研發投入錯配是重要原因之一(靳來群等,2019)。為此本文從生產與研發雙重視角來解答數字金融如何影響要素配置效率。
廣義上資源配置效率分為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組織之間的資源配置效率,而狹義上組織內部資源配置效率主要指利用效率,所用評估方法多是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為此本文主要基于組織之間資源配置效率的概念,外在扭曲因素使得各類要素投入利用效率較高的部門或企業無法得到相應投入,如果實現這些要素從利用效率低的部門向利用效率高的部門流動,則會帶來國家總生產能力或研發能力的提高(Restuccia &Rogerson,2008)。可以看到此概念下的資源配置效率反映的是要素投入規模與利用效率的相關程度,如何對資源配置效率進行評估,也將直接影響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在狹義資源配置效率的概念下,更加客觀地評估了要素錯配程度,并進一步在劃分生產和研發過程的基礎上,比較兩類要素錯配的差異。二是在比較結果的基礎上,從生產和研發兩個過程展開綜合分析,更加全面地認識數字金融發展如何作用于我國要素配置效率,并分析我國數字金融發展的貢獻和不足。
二、機制分析
近年來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通道,而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動力將由粗放型的要素投入擴張向TFP 提高轉變。根據二分法,TFP增長途徑可劃分為部門或企業自身技術進步下的TFP 提高和部門或企業之間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優化。部門或企業自身TFP 的提高又可分為研發要素投入規模的增加與利用效率的提高。參考TFP增長二分法,其中利用效率的提高既可以來自部門或企業自身的提高,又可來自部門或企業之間研發要素配置的優化,具體路徑分解如圖1。同時,基于對區域間要素錯配程度的測算,研發要素錯配比生產要素錯配更為嚴重。因此,從生產要素與研發要素兩類要素來深入分析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優化的作用,將是重要的研究議題。

圖1 TFP提高路徑分解
造成生產和研發要素錯配的重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和金融市場摩擦(David &Venkateswaran,2019)。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使企業在貸款利率上存在差異,再加上發展中國家因金融體系不完善、所有制和規模歧視等問題,將造成生產率相對較高的部門或創新質量較高的項目未能獲得資源支持,進而造成資源錯配,導致TFP 的損失(靳來群等,2015)。數字金融是數字技術與金融體系深度融合的產物,其在降低資源錯配,提高生產率方面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首先,數字金融憑借數字技術和大數據等優勢緩解信息不對稱,進而能夠將有限的金融資源分配給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和創新質量更高的項目。這不僅提高了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也緩解了生產端和研發端的資源約束,有助于提高企業生產率(田杰等,2021)。其次,數字金融拓寬了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門檻。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帶動了銀行等傳統正規金融的發展,同時也催生出了一批非正規金融。融資渠道的拓寬和金融產品的多樣性,將更加容易匹配多元融資主體的需求。同時,數字金融依靠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技術突破了傳統金融依靠物理網點和營業時間的限制,降低了信息收集和處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而融資門檻的降低又使得規模相對較小,而生產率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有款可貸,有資可融,激勵了其創新(謝雪燕和朱曉陽,2021)。另外,數字技術的使用也加速了金融資源的流轉速度,從而惠及更多的企業和創新主體。綜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設1。
H1:數字金融能優化生產和研發過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
從生產端和研發端的特點看,研發端需要的資金更大,風險也更高。普適性的數字金融在為企業緩解融資約束的同時,通過深入了解企業的融資需求,將為投入不足的企業或部門提供更多的資金,而相應地為投入過度的企業或部門提供更少的資金,最終帶來國家整體金融資源的配置優化。不僅如此,相較于生產層面,研發層面所需要的軟信息更多,比如不僅要對企業的專利數量有充分了解,還要對專利的質量和價值有一定評估。只有數字金融或數字技術的深入發展及對創新主體信息的深入挖掘,才能更加準確地將稀缺的金融資源配置到那些雖然面臨融資約束,但未來能夠帶來更大價值的企業和創新項目中。這些均要求數字金融應朝縱向深度發展。
數字金融的深度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數字與金融之間的融合深度,也就是數字技術除了主要與銀行融合以外,還進一步與資本市場或非正規金融機構融合;二是數字金融與資金需求方之間的深度融合,數字金融更深度地了解企業的運營情況。從第一個層面來講,資本市場或非正規金融在對待風險創新尤其是中小企業風險創新上,相對于正規金融機構有著更強的動機,數字金融與此類金融機構的融合將更多地緩解創新類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進而優化研發要素的配置效率。從第二個層面來講,數字金融的深度發展相對于傳統金融能提供更多金融創新產品,并更好地與創新類企業對接,深入獲取創新類企業的硬信息和軟信息,利用數字技術識別更需要風險資金的創新類企業。綜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設2。
H2:實現研發要素的配置優化更需要數字金融的深度發展。
三、模型設計與指標選取
參考Restuccia & Rogerson(2013)所提出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計算方法,用企業或部門之間生產要素錯配所致全要素生產率損失程度衡量(即資源錯配程度)。在實證分析數字金融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時將要素錯配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構建計量模型(1):

其中,被解釋變量mis即為要素錯配程度,解釋變量dfin 為數字金融發展程度。控制變量X主要包括:人均GDP所度量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gdp,第二、三產業產值占比所度量的地方產業結構ind,在學學生數量占比所度量的地方人力資本發展水平edu,進出口總額占比所度量的地方對外開放水平ope。參考張勛等(2020)的研究,使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度量數字金融。
要素錯配程度的度量十分重要。在部分分析數字金融對資源配置效率影響的文獻中,如封思賢和徐卓(2021)采用投資關于產值的彈性系數,田杰等(2021)采用要素投入比例與產值份額相關程度所反映的要素價格扭曲系數來衡量。然而考慮到要素投入也是產值的重要來源,筆者主要利用要素與生產率的相關程度來衡量(這也是狹義資源配置效率的定義)。Brandt et al.(2013)提出了地區之間生產要素錯配程度度量方法,靳來群等(2019)利用該方法對我國部門之間的研發要素錯配問題展開了分析。但是如果使用該方法去度量要素錯配程度,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局限是,該方法度量的是錯配所致全國整體生產率損失程度,其僅是一時間序列數據,但地方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是一地區面板數據,數據維度并不匹配。為彌補要素錯配程度指標的不足,使用要素投入偏離度指標dev 作為替代。在Brandt et al.(2013)的框架下,首先得到要素配置扭曲狀態下的部門要素投入力度input(即實際狀態下的要素投入力度)以及有效狀態下的部門要素投入力度input,那么指標dev=|input/input-1|度量實際要素投入相對于有效狀態的偏離程度,該指標越大表明偏離程度越嚴重。鑒于本文主要分析了資本K 和勞動L 的配置效率問題,為此,該指標具體包括了資本投入偏離度devk=|k/k-1|和勞動投入偏離度devl=|l/l-1|。



鑒于本文既關注了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問題,又關注了研發要素的配置效率問題,因此,相應的產值、資本和勞動,也將分為生產和研發兩個過程,包括了生產產值PY、研發產值RY,生產勞動PL、研發勞動RL,生產資本PK、研發資本RK。相應的要素投入偏離度包括了生產勞動偏離度devpl、研發勞動偏離度devrl、生產資本偏離度devpk、研發資本偏離度devrk。在測算要素投入偏離度時,用各城市GDP 來衡量生產產值PY。而考慮到不同專利類型價值的差異性,研發產值RY 用寇宗來和劉學悅(2017)測算的各城市創新力指數衡量。生產勞動PL用各地從業人員數衡量,研發勞動RL 用研發人員全時當量衡量。對于生產資本PK,參考田友春(2016)采用永續盤存法,PK=(1-η)PK+I/P,折舊率η設為9.6%,I、P為固定資產投資及其相應價格指數。同時利用公式PK=I/(g+η)得到基期1993年的生產資本存量,g為投資年均增長率。對于研發資本RK,參考陳鈺芬等(2020)采用BEA 方法,RK=(1-η)RK+(1-η/2)E/P,折舊率η設為15%,E為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其相應價格指數P參考朱平芳和徐偉民(2003)采用成本法得到,同時利用公式RK=E/(g+η)得到基期2001年的研發資本存量,此時g為研發支出年均增長率。
因官方統計年鑒從2001年起披露研發投入的相關數據,為此本文分析了2001年之后的研發要素配置效率。而衡量研發成果的創新力指數數據來自寇宗來和劉學悅(2017)提出的《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該報告數據截至2016年,本文所得研發要素配置效率也僅到2016年,其中研發投入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同時,在進一步實證檢驗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時,所用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從2011年開始披露,因此,針對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實證分析部分時間跨度為2011—2019年,針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的實證分析時間跨度為2011—2016年。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生產函數與研發函數估計結果
為評估要素投入的偏離度,首先分別估計了生產與研發過程中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系數(α和β)。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假定下,其對數化后的計量模型為:lnY=c+αlnK+βlnL+u+λ+ε,加入u以控制個體效應、λ以控制時間效應。為了緩解內生性問題,利用滯后一期的資本和勞動作為工具變量,并使用兩階段最小二乘(2SLS)進行了估計,包括固定效應模型(FMM)和隨機效應模型(RMM)。同時,進一步利用隨機前沿模型展開估計,結果如表1 所示。在沒有控制內生性問題下的Hausman 檢驗表明,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此外,列(4)和列(8)都顯示η顯著不為零,表明時變技術效率模型SFA2 相比不變技術效率模型SFA1 更合適。因此,選擇FMM模型和SFA2模型估計結果的平均值作為最終要素彈性的取值,生產過程中α為0.39、β為0.30;研發過程中α為0.20、β為0.55。從測算的偏離度指標來看,就研發要素和生產要素比較而言,研發要素偏離度高于生產要素偏離度。

表1 產出彈性估計
(二)基礎結果
使用前文測算得到的要素投入偏離度dev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計量模型(1),實證檢驗了數字金融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如表2 所示。在實證分析時既采用了固定效應模型(FE)又采用了隨機效應模型(RE),可以看到,兩類模型得到的回歸結果都基本保持一致,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實證結果的穩健性。表2 的列(1)—(4)顯示,數字金融發展程度變量dfin 對生產資本錯配與生產勞動錯配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負,表明數字金融顯著降低了生產資本與生產勞動錯配,與前文假設1 是一致的,數字金融將優化我國要素配置。列(5)—(8)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程度變量dfin并不顯著,也就是說數字金融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并沒有顯著的作用。但基于表3的分位數回歸結果可以看到,數字金融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仍有著顯著的優化作用。鑒于表2 的回歸結果是基于均值回歸方法得到,極端異常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較大,為此本文認為表3的實證結果將更為可靠。

表2 數字普惠金融對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礎作用
進一步基于分位數回歸方法,實證檢驗了被解釋變量的不同分位數下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優化的作用差異,結果如表3所示。隨著分位數的不斷增加,數字金融發展變量dfin的回歸系數的絕對值都在逐漸增加。表明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優化的作用隨著要素錯配程度的加重逐漸加強,也就是說,要素錯配程度越高的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的要素配置優化作用越明顯。同時也可以看到,對于生產要素而言,中位數的回歸結果也表明數字金融仍有著顯著的配置優化作用,這也進一步驗證了表2實證結果的穩健性,說明數字金融發展對我國要素配置優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表3 分位數回歸
為進一步驗證數字金融發展是否對我國的資本配置效率存在著非線性的影響,在計量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數字金融發展變量的平方項dfin,構建計量模型(5)。如果變量dfin顯著為負,則表明存在強化作用;如果為正,則表明存在弱化作用。不僅如此,進一步對變量dfin和變量dfin進行了聯合顯著性檢驗(原假設為β=0且β=0),檢驗結果顯著拒絕了原假設,這也佐證了前文分析,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效率存在著顯著的影響。

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列(1)和列(3)結果顯示,盡管變量dfin 回歸系數為正,但變量dfin顯著為負,即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效率存在著U型影響。經計算,U型最低點處數字金融發展指數的取值分別為109和81,而樣本期內80%的省份都要高于該值,并且從2013年開始所有省份的數字金融發展指數也都要高于該值,即數字金融對資本要素配置效率的影響大部分處于U型曲線的右半邊。這也表明,隨著數字金融的發展,其對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將逐漸增強,存在著顯著的強化作用。對于勞動要素而言,數字金融的強化作用并不顯著(如列(2)和列(4)所示)。從我國現在數字金融的發展狀況看,這表明未來需要進一步推進數字金融發展,充分發揮數字金融在優化要素配置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對于資本要素。

表4 數字金融的強化作用
(三)分層面數字金融發展對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
進一步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分為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三個方面,接下來就數字金融的這三類子指標對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展開了實證分析。其中數字金融覆蓋廣度用符號dfgd表示,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用符號dfsd表示,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用符號dfhd表示。表5列示了數字金融分指數對生產要素配置的回歸結果,列(1)—(3)顯示,變量dfgd、變量dfsd、變量dfhd 對生產資本錯配的影響都顯著為負,這表明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三類子指標都顯著地降低了生產資本錯配,優化了生產資本配置。就生產勞動而言,列(4)—(6)的回歸結果也進一步顯示,數字金融發展的三類子指標都起到了糾正生產勞動錯配的作用。說明對于生產要素配置效率而言,數字金融各層面的發展都有著顯著的優化作用。

表5 數字金融分指數對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
針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作用的實證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于研發資本還是研發勞動的配置效率,僅數字金融使用深度變量dfsd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如列(2)和列(5)所示),表明僅數字金融使用深度在優化研發要素配置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而數字金融覆蓋廣度dfgd 和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dfhd 的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同時考慮到極端異常值的影響,仿照上文進行了中位數回歸,結果仍然顯示僅數字金融使用深度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在此不再贅列。這也進一步證明了研究假設2,實現研發要素的配置優化更需要數字金融的深度發展。

表6 數字金融分指數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
(四)地區異質性分析
為實證檢驗數字金融對要素配置效率影響的地區異質性,構造計量模型(6)進行分析:

其中,東部地區虛擬變量D 取值為1,中西部地區取值為0。那么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數字金融的影響系數為β,東部地區系數則為β+β。
數字金融對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地區異質性作用結果如表7所示。列(1)—(3)顯示,地區虛擬變量與數字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及數字化程度的交互項D×dfgd、D×dfhd、D×dfhd都顯著為負,表明數字金融發展對生產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區異質性,對東部地區的作用效果要強于中西部。同時,表8報告了數字金融分指數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影響的地區異質性。可以看出,僅數字金融發展中的使用深度dfhd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存在顯著的作用,且地區虛擬變量與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交互項D×dfhd顯著為負。這與前文實證結果相同,對于生產要素而言,數字金融發展的三個層面都有顯著的配置優化作用,而對于研發要素,僅數字金融的使用深度有著顯著的配置優化作用。其作用的地區差異也與預期一致:一方面,東部地區存在著地理區位上的沿海優勢,更容易接入海外市場,使數字金融有更廣的應用空間和機會,同時從海外市場獲得的新技術和理念也更容易與數字金融產生進一步的融合。另一方面,東部地區無論是數字金融賴以發揮作用所需要的人力資本結構,還是數字信息硬件設施都要好于中西部地區,也就更容易與東部地區產生強化作用。

表7 數字金融對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影響的地區異質性

表8 數字金融對研發要素配置效率影響的地區異質性
五、結論與啟示
要素錯配問題嚴重制約著我國TFP的提高,伴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金融也應運而生。那么數字技術在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優勢,能否使得數字金融實現要素配置優化的功能,本文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對這一問題展開了實證檢驗,研究結論表明:第一,基于TFP增長二分法,對1993—2019年的生產要素錯配程度和研發要素錯配程度的測算顯示,盡管生產要素錯配程度近年來出現了快速的反彈趨勢,但是研發要素錯配要比生產要素錯配嚴重很多。第二,無論是生產要素還是研發要素,數字金融都有著顯著的配置優化作用,而且要素錯配程度越嚴重的地方,數字金融的要素配置優化作用越明顯,并且這樣的配置優化作用會隨著數字金融自身的發展,呈現出逐漸增強的作用。第三,分層面看,無論是數字金融的廣度、深度,還是數字化程度都對生產要素配置有著顯著優化作用,而僅數字金融深度對研發要素有著顯著優化作用。同時,分地區看,數字金融對生產和研發要素配置的優化作用,東部地區都要強于中西部地區。
本文研究結論相應的啟示為:第一,在未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除了要加快生產要素流動、遏制錯配加重趨勢外,更要大力消除研發要素錯配問題。第二,在肯定我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應繼續深化數字技術與金融的廣泛且深度的融合。同時,對于那些要素錯配程度相對嚴重的地方,更應加快數字金融的發展。第三,為加快糾正研發要素錯配問題,在繼續強化數字金融發展深度的同時,也要進一步發揮數字金融廣度和數字化程度的作用。并且也要在充分發揮東部地區優質軟硬件設施的同時,進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配套設施及數字金融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