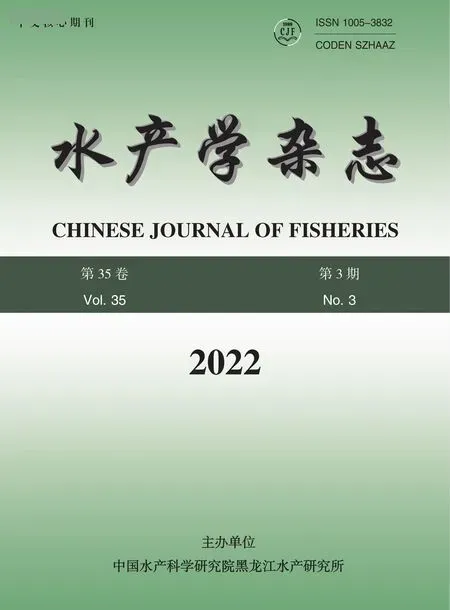CRISPR/Cas9 基因編輯原理、發展及應用
董樂,楊笑星,佟廣香,閆婷,孫志鵬,徐歡,劉天奇,匡友誼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黑龍江水產研究所,黑龍江 哈爾濱150070 2.上海海洋大學水產與生命學院,上海 201306)
自20 世紀70 年代重組DNA 技術發展以來,有關位點特異性核酸酶(Site-specific nuclease,SSN)的基礎理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使精準基因編輯技術快速普遍應用于各個領域。SSN 為目的基因的精準編輯提供了有效的特異性編輯方法[1,2]。較早被廣泛應用于基因工程技術中的兩種基因編輯技術是鋅指核酸酶(Zine finger endonuclease,ZFN)和轉錄激活因子樣效應物核酸酶(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TALENs)。這兩種編輯方法原理相同,皆是DNA 結合蛋白與核酸內切酶FokⅠ兩個模塊的融合,之后對特定靶序列雙鏈進行切割。然而這兩種核酸酶存在結構復雜、不易操作、耗時長、易脫靶[3-6]等缺點,阻礙了其發展。隨著2012年Jinek[7]等根據細菌的一種獲得性免疫系統改造而成的成簇規律間隔的短回文重復序列(Clustered regulator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CRISPR)介導的位點特異性人工核酸內切酶Cas9系統,在原核、真核生物的基因組編輯中取得成功而正式走進科研人員的視野[8]。CRISPR/Cas9 作為一種全新的技術具有在基因組中定點編輯的能力,具有精準、高效、制備簡單等優勢而被廣泛發展和應用[9]。本文綜述了CRISPR/Cas9 的歷史來源、結構組成、作用機理、技術發展和應用等最新研究成果,旨在為初學者提供CRISPR/Cas9 基因組編輯系統的基礎知識。
1 CRISPR/Cas9 的來源
CRISPR/Cas9 自發現到在哺乳動物中應用經歷了近30 年的漫長研究過程(圖1)。1987 年Ishino等在研究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的堿性磷酸酶基因時,首先發現CRISPR 下游有被間隔序列間隔的重復序列。后來大量的細菌基因組測序,發現這種序列廣泛存在于細菌與古細菌中[10]。2002 年Mojica 等[11]和Jansen 等[12]將間隔排列的串聯重復序列命名為成簇規律間隔的短回文重復序列(CRISPR),同時也發現了Ⅰ型、Ⅱ型和Ⅲ型3 種類型的CRISPR 簇相關的Cas 蛋白,但其生物學功能未知。2005 年經過深入研究發現,間隔序列來源于外源入侵的DNA,推測CRISPR/Cas 可能與細菌自我保護不被外源遺傳物質影響的免疫系統有關[13-15];2007 年,Barrangou R 等[16]在嗜熱鏈球菌(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中證實了CRISPR/Cas 具有獲得抵抗外源噬菌體侵入的能力;2008 年Marraffini 等[17]在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spp.)中證明了這種獲得性抵抗外源菌體的能力。Deveau 等[18]發現了原間隔序列鄰近基序(protospacer adjacent motif,PAM)為CRISPR/Cas 發揮作用提供了靶標。這一防御系統的發現引起了科學家對其在基因組中定點編輯的濃厚興趣。2012 年,Sternberg 等[19]發現II 型CRISPR中僅需一個Cas9 蛋白即可完成靶序列的編輯,在體外使用RNA 實現了DNA 目的序列的識別和剪切;2013 年Cong 等[20]和Mail 等[21]首次在真核生物中成功應用CRISPR/Cas9 進行了基因編輯。目前,CRISPR/Cas9 已逐步應用到了包括原核生物、真菌以及動植物的基因組精準編輯,成了基因組編輯中的“明星”技術。

圖1 CRISPR/Cas 系統研究進展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RISPR/Cas system
2 CRISPR/Cas 結構
從最初發現CRISPR/Cas 間隔排列的串聯重復序列[10],并證明其廣泛存在于細菌(40%)與古細菌(90%)中[22],到將帶有回文結構的重復序列命名為CRISPR 序列[11,12],無一不在逐步揭開其神秘面紗。CRISPR/Cas 由CRISPR 簇和Cas 蛋白組成,CRISPR簇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圖2):一個前導序列(Leader)、數個高度保守的重復序列(Repeat)和多段間隔序列(Spacer)組成[23,24]。其中Leader 序列位于CRISPR簇的上游,是CRISPR 簇的啟動子序列[23];Repeat 序列一般為21~48 bp,含有回文序列,故能形成發卡結構;Spacer 區是入侵的外源DNA 序列[25]。

圖2 CRISPR 位點結構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CRISPR structure
CRISPR 簇側翼附近是系列CRISPR 相關蛋白基因座(CRISPR-associated),即Cas 蛋白基因[22,25],其編碼產物均含有與核酸作用的功能結構,目前已發現有Cas1-Cas14 等多種類型[26-28]。Cas 蛋白基因與CRISPR 共同作用組成CRISPR/Cas 系統,完成基因的精準高效編輯。根據Cas 蛋白的種類和序列,CRISPR/Cas 可分二類六型[26-31](Ⅰ-Ⅵ),Ⅰ型、Ⅲ型和Ⅳ型需要幾個Cas 效應蛋白組成的復合體,Ⅱ型、Ⅴ型和Ⅵ型僅需單個Cas 效應蛋白;其中Ⅱ型CRISPR/Cas 只需一個Cas9 蛋白,便可有效切割雙鏈DNA。正是這種簡單高效的優點給予了Ⅱ型CRISPR/Cas9 強有力的發展空間。
3 Ⅱ型CRISPR/Cas9 在細菌中的作用原理
Ⅱ型CRISPR/Cas9 與Ⅰ型和Ⅲ型兩種系統在轉錄、加工以及與核酸酶在剪切特定目的序列的協同作用上截然不同[16],目前Ⅱ型系統的研究最為廣泛和深入。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編輯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圖3):首先獲取外源DNA,其次CRISPR位點的轉錄與加工,最后是CRISPR/Cas9 切割外源DNA[32]。

圖3 II 型CRISPR-Cas9 抵御外源噬菌體的獲得性免疫機制,引自吳言等[39]Fig.3 The process of adaptive immune mechanism of CRISPR-Cas9's II against foreign phages,from Wu Yan et al[39]
第一階段為獲取外源DNA 序列,將外源基因的原間隔序列(protospacers)整合到宿主染色體的CRISPR 序列前導區的近端(如第一個spacer),實現標記功能。當質粒或噬菌體首次入侵攜有CRISPR的個體時,在Cas1 和Cas2 的幫助下宿主首先識別入侵核酸的PAM序列,切割臨近PAM 序列的外源DNA 作為原間隔序列。臨近間隔序列3’端的3 nt較保守,稱為PAM 序列,通常為5’-NGG-3’[33,34],同時PAM區也是該系統的剪切位點。第二階段,當外源DNA 再次入侵時,在Leader 的調控下,CRISPR 位點被轉錄成RNA 前體(Pre-CRISPR RNA,pre-crRNA),同時重復序列(repeats)被轉錄成反式激活RNA(Trans-activating crRNA,tracrRNA),并由Cas9 和雙鏈RNA 特異性RNase III 核酸酶對pre-crRNA 進行加工[35],生成僅含有一個間隔序列(入侵的外源序列)的成熟crRNA,該階段Cas9 基因也被轉錄和表達。在crRNA、tracrRNA 和Cas9 核酸酶形成復合體crRNP 的作用下對入侵的外源DNA 進行剪切編輯[21,36],起到自我免疫防護。第三階段是對外源DNA 的免疫編輯,復合體crRNP 識別并通過堿基互補配對結合到與間隔序列(crRNA)互補的DNA 鏈上,使互補鏈與crRNA 雜交,然后由Cas9中的HNH 核酸酶結構域剪切crRNA 的互補鏈,Cas9 的另一個RuvC 活性位點剪切非互補鏈,從而產生雙鏈DNA 斷裂(Double strand breaks,DSBs)[7],經細胞的非同源末端連接(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或同源介導的雙鏈修復(homology directed repair,HDR)對DNA 進行修復[32,37],實現對外源DNA 的切割。
綜上,當使用CRISPR/Cas9 對組織、細胞或者胚胎進行基因組編輯時(圖4),可通過體外合成單引導RNA(Single guide RNA,sgRNA),混合Cas9 mRNA 或蛋白直接轉染到細胞系或組織中[38],對目標序列進行雙鏈切割,經NHEJ 和HDR 機制修復,即可實現基因組靶向編輯。

圖4 CRISPR/Cas9 系統介導的基因組編輯,引自沈陽坤等[ 40]和Alexander Hruscha 等[41]Fig.4 Genome editing mediated by CRISPR/Cas9 system,from Shen Yangkun,et al[ 40] and Alexander Hruscha et al[41]
4 CRISPR/Cas9 的技術發展
2012 年Jinek 等[7]將crRNA 和tracrRNA 兩者連接在一起,形成新的單引導RNA(Single guide RNA,sgRNA),且打靶效率與雙引導RNA 并無顯著改變。與野生型CRISPR/Cas9 相比,這個新型的CRISPR/Cas9 更加容易構建,只需一個引導RNA 和Cas9 核酸酶mRNA 同時注入受精卵,便可快速獲得定向突變個體。該系統不僅可以靶向編輯單個基因,還可以多個sgRNA 共同使用完成多個位點的靶向突變,這在Yin 等[42]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驗證。Yin 等[42]應用多個sgRNA 在斑馬魚(Danio rerio)上獲得了酪氨酸酶和胰島素受體a 和b 的多重雙等位基因失活,得到了色素沉著和葡萄糖穩態的缺陷表型。自2013 年成功將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應用到真核生物和細胞以來[20,21],該技術取得了顯著進展。
4.1 提高CRISPR/Cas9 特異性
相比于TALEN,CRISPR/Cas9 提高了靶向編輯特異性,但仍存在一定比率的脫靶效應,這將妨礙其在疾病治療、基因功能研究上的應用。主要從改進sgRNA 和Cas9 核酸酶兩方面著手以降低其脫靶率、提高特異性。在sgRNA 的改進上,Kim 等[43]和Fu 等[44]的研究分別顯示延長或截短2~3 個nt 的sgRNA 能降低堿基錯配率,提高靶向修飾的特異性。John 等[45,46]分析了1 841 個sgRNA 的基因編輯結果,構建了sgRNA 活性的預測模型[45]。根據該模型創建了人類和小鼠全基因組CRISPR/Cas9 sgRNA文庫,在分析了數千個sgRNA 非靶標活性的基礎上,開發了非靶標位點預測模型[46],改進了人類和小鼠sgRNA 的設計,以提高其活性和靶點修飾的專一性。
除了sgRNA,Cas9 核酸酶的結構也顯著影響基因編輯的準確性。Cas9 蛋白通過HNH 和RuvC 兩個功能結構域實現雙鏈DNA 的切割,增加脫靶風險,因此學者對Cas9 進行了修飾。突變Cas9 兩個核酸酶結構域中的一個會產生缺刻Cas9(Nickase Cas9,nCas9),該核酸酶只切割一條DNA 鏈[7,33]。兩個nCas9 可以靶向相鄰的DNA 位點而引起DSBs[47];因該過程中靶位點長度增加,產生的單個缺口將由高保真堿基切除修復機制修復,從而在不犧牲靶位點切割效率的前提下,將非靶標活性降低了50~1 000 倍[47,48]。與單結構域的失活相比,2013 年Qi 等[49]突變了Cas9 核酸酶中的兩個功能結構域,讓其缺乏核酸酶活性而保留其DNA 結合活性,形成了Dead Cas9(dCas9)。在不切割目標DNA 的情況下dCas9 介導特定位點的遺傳和表觀遺傳調控,dCas9與sgRNA 共同作用時將會抑制靶基因的轉錄[49,50],進而大幅降低脫靶率。2014 年,在dCas9 的基礎上開發的新型基因編輯工具提高了對目的位點編輯修飾的特異性。Guilinger 等[51]將dCas9 與Fok I 限制酶融合形成二聚體fCas9,經一對sgRNA 引導進行基因組修飾,其特異性要比野生型Cas9 高140倍以上,與雙nCas9[47]效率相似。
4.2 CRISPR/Cas9 PAM 序列修飾
與入侵DNA 序列中同crRNA 靶序列連接臨近2~5 nt 的PAM 序列決定著CRISPR/Cas9 靶點的識別,也可影響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組編輯的特異性[52]。現已知存在多種PAM序列,如化膿性鏈球菌(Pyogeniccoccus spp.)的NGG PAM[7],嗜熱鏈球菌(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的NGGNG 和NNAGAAW PAM[32,33]及腦膜炎奈瑟菌(Neisseria meningitidis)的NNNNGATT PAM[53]等。CRISPR/Cas9 介導的DNA 切割依賴于PAM 的方式限制了基因組中靶位點的頻率,NGG PAM 和NAG PAM[54]在基因組中每8 個核苷酸可以找到一個靶位點,NGGNG PAM和NNAGAAW PAM,每32 個和256 個核苷酸才能找到一個靶位點。
為擴充靶位點的數量,Nishimasu 等[55]通過基因工程方法創造了spCas9-NG 基因編輯器,將spCas9的PAM區序列從NGG 擴充至NG;Hu 等[56]采用人工進化方法,創建出xCas9,將spCas9 的PAM 區從NGG 擴充至NGN、GAA 和GAT。Kim 等[57]通過大規模的靶位點評估了野生型spCas9、xCas9 和sp-Cas9-NG PAM區靶位點的兼容性、脫靶率和編輯效率,發現xCas9 對靶位點的錯配容忍性最低,而sp-Cas9-NG 具有最廣泛的PAM區兼容性,相對于sp-Cas9,xCas9 和spCas9-NG 可以編輯前者不能編輯的基因。他們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化并建立了xCas9和spCas9-NG 靶位點序列活性預測模型。Walton等[58]開發了SpRY 基因編輯器,將spCas9 的PAM區進一步擴充至NRN 和NYN,做到了幾乎不依賴于PAM區序列進行基因編輯。
4.3 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敲入
CRISPR/Cas9 不僅介導基因敲除,同樣可以介導基因定向插入,CRISPR/Cas9 在產生DSB 后,可通過同源重組修復來精準且理想的達到基因修飾等目的,因此可根據需要設計sgRNA 和同源供體,以實現供體的精準敲入(圖4)。例如鐮刀型細胞貧血癥(Sickle-cell disease,SCD)是由于單堿基突變造成。Dewitt 等[59]結合了Cas9 與sgRNA 組成的RNP復合物和單鏈DNA 寡核苷酸供體(ssODN),替換了SCD 患者造血干細胞HBB 突變基因中的單堿基,并將體外培養的單堿基替換的細胞植入小鼠體內存活了16 周。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敲入不僅可以定點插入單堿基和小片段,還可進行大片段的精準敲入。Bai 等[60]報道了一種斑馬魚長單鏈DNA 模板(zLOST)。將300 nt 的zLOST 經HDR 途徑敲入酪氨酸酶(Tyr)位點,結果顯示98%的白化胚中至少有一個色素沉著,超一半出現少量色素沉著。該方法精準有效地修復了白化病癥。Shy 等[61]在小鼠胚胎干細胞Lef1 位點介導插入了1 974 bp 的片段,盡管只有0.4%的插入效率,但也為大片段的敲入提供了案例。CRISPR/Cas9 系統介導的基因敲入同樣存在脫靶問題,為了提高其精度和外源DNA 的整合效率,有研究者將sgRNA 靶位點序列加在800 bp 的同源臂兩端(圖5),建立了同源臂介導的末端連接(HMEJ)技術,并在小鼠胚胎及成體肝細胞中進行同源重組修復,結果顯示HMEJ 介導的同源重組修復效率顯著提高[62]。

圖5 HMEJ 介導的基因敲入示意圖,引自Yao[62]等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HMEJ -mediated gene knock-in,from Yao et al[62]
雖然CRISPR/Cas9 可采用同源重組的方式實現基因的定點敲入,但較低的同源重組效率和DNA雙鏈斷裂引起染色體易位、重排等風險阻礙了該技術的應用。2019 年Strecker J 等[63]在藍細菌中發現了一種Tn7 轉座酶,它的三個亞基(tnsB,tnsC,tniQ)可以與CRISPR 效應物Cas12k 關聯,形成CRISPR-associated transposase(CAST),開發了shCAST 系統,在大腸桿菌中實現了2.5kb 的DNA片段插入,且成功率高達80%,遠超基于同源重組的CRISPR 方法。同時Klompe S E 等[64]也報道了CRISPR/Cas 與類Tn7 轉座子聯合介導的基因插入系統(Cascade),評估了將其應用于基因組編輯的潛力。兩個系統相比,shCAST 系統更小并具有方向性,而Cascade 系統更加特異但插入是隨機的,在疾病和癌癥的治療中產生了不確定性。基于轉座的定向插入系統進行基因修復與現有的利用同源重組的編輯方式相比,在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更具優勢。
4.4 CRISPR/Cas9 介導的單堿基編輯
基于CRISPR/Cas9 可實現基因的敲除和轉入及基因的單堿基編輯。2016 年David Liu 實驗室用具有單一切割活性的nCas9 蛋白與胞嘧啶脫氨酶構建了單堿基編輯器CBE(Cytosine base editors,CBE);2017 年構建了ABE(Adenine base editor,ABE)單堿基編輯器,CBE 和ABE 可分別利用胞嘧啶脫氨酶或經過改造的腺嘌呤脫氨酶對靶位點上一定范圍的胞嘧啶(C)或腺嘌呤(A)進行脫氨基反應,經DNA 修復和復制,從而在不產生DNA 雙鏈斷裂的情況下完成C>T(G>A)和A>G(T>C)堿基的自由轉換[65,66]。哺乳動物細胞中存在尿嘧啶DNA 糖基化酶(Uracil DNA glycosylase,UDG),導致細胞內的堿基錯配修復途徑(Base excision repair,BER)逆轉U·G 中間產物返回到C·G 堿基對(圖6)。為此,該實驗室將尿嘧啶DNA 糖基化酶抑制劑(Uracil DNA glycosylase inhibitor,UGI)加在了CBE 系統上,以此來提高CBE 編輯器在哺乳動物中的編輯效率。在實際應用中,Chadwick 等[67]利用CBE 編輯器在成年小鼠肝臟的PCSK9 基因中提前產生了終止密碼子,編輯后小鼠的PCSK9 和膽固醇水平顯著降低。隨后Ryu 等[68]將ABE mRNA 和sgRNA 顯微注射到小鼠胚胎中,在Try 基因中引入了白化病點突變,獲得了具有白化病表型的Try 突變小鼠。這兩種單堿基編輯系統的問世不僅是精準基因編輯領域的重大突破,同時對治療許多點突變的遺傳病有重要的意義,為眾多遺傳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

圖6 CBE 和ABE 工作示意圖,引自宗媛和高彩霞[69]Fig.6 Working diagram of CBE and ABE,from Zong Yuan and Gao Caixia[69]
ABE 和CBE 單堿基編輯器雖然能進行A>G(T>C)和C>T(G>A)的替換,但不能同時進行這2種類型堿基的修飾。為解決這一問題,Zhang 等[70]將人類胞嘧啶脫氨酶hAID-腺嘌呤脫氨酶-Cas9n(SpCas9 D10A 突變體)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型雙堿基編輯器A&C-BEmax。它可以在靶序列上實現C>T 和A>G 的高效轉換,同時RNA 脫靶水平大幅降低,提高了C>T 的編輯效率,而A>G 的效率略有降低。隨后Sakata 等[71]將來源于七鰓鰻(Petromyzon marinus)的胞嘧啶脫氨酶PmCDA1 和鼠源的胞嘧啶脫氨酶rAPOBEC1 分別與腺苷脫氨酶(TadA)融合到nCas9 的C 端和N 端,開發了雙堿基堿基編輯器,成功在哺乳動物細胞中實現了A 和C 的同時突變,A 和C 的編輯效率分別高達40%和50%。最后Grünewald 等[72]采用了更短的腺苷脫氨酶(TadA)融合在N 端,將來源于七鰓鰻的胞嘧啶脫氨酶Pm-CDA1 融合到nCas9 C 端,開發了能同時編輯A 和C 的SPACE 系統。該堿基編輯器C>T 平均編輯效率和單個CBE 效率相當,A>G 平均編輯效率與單個ABE 效率相比略有下降,但是SPACE 雙堿基編輯效率明顯高于ABE+CBE 的共同作用,與Sakata等[71]的研究結果一致。
雖然采用CRISPR/Cas 可方便、高效地進行基因敲除、敲入和單堿基編輯,但仍不能采用單一的工具同時實現上述功能。2019 年哈佛大學David Liu實驗室通過將M-MLV 逆轉錄酶融合到nCas9,開發了Prime Edit 基因編輯工具[73],可實現12 種單堿基替換,最多44 bp 的插入和80 bp 的刪除;該系統通過在sgRNA 3’端加上一段用于逆轉錄的模板DNA,形成可編程的pegRNA。由pegRNA 引導融合蛋白結合到靶位點,nCas9 切割pegRNA 的非互補鏈,通過逆轉錄酶將pegRNA 3’模板DNA 逆轉錄到基因組中,實現無需供體DNA 的堿基替換、插入和刪除。與其他基因編輯工具相比,對目的基因進行堿基替換、小片段插入和刪除更有優勢,該工具能使基因編輯更加高效精準。
5 CRISPR/Cas9 基因編輯的應用
CRISPR/Cas9 組成簡單、易操作和編輯精準高效,使其在功能基因研究、種質培育、生物模型構建和基因治療等研究領域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5.1 CRISPR/Cas9 在功能基因研究中的應用
隨著模式生物基因組測序的逐漸完善健全,利用CRISPR/Cas9 在基因組中同時進行多靶位點的編輯成為可能,能通過全基因組功能篩選鑒定在目標表型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有研究顯示:將功能缺失突變引入不同基因的編碼外顯子中,能夠在人細胞中執行強大的陰性和陽性篩選能力[74,75]。相比于早期使用RNAi 的修飾效率低下、脫靶嚴重以及僅限于轉錄而言,Cas9 和sgRNA 聯合介導的篩選可提供更高的篩選敏感性和專一性,并可設計為靶向幾乎任何DNA 序列[74]。Cas9-sgRNA 方法在靶基因位點產生Indels,能導致基因功能的完全喪失,而RNAi 方法只導致基因表達抑制。因此,當靶向基因相同時,CRISPR/Cas9 系統可產生比RNAi 更明顯的表型,這更容易鑒定相關基因[76]。
現已證明CRISPR 介導的轉錄抑制(CRISPRinterference,CRISPRi)和激活(CRISPR-activation,CRISPRa)是篩選功能基因組的強大工具[77,78]。通過突變使Cas9 的HNH 和RuvC 結構域失活,形成只擁有DNA 結合活性,而無核酸酶活性的缺陷Cas9(dCas9),dCas9 和sgRNA 組成的CRISPRi 并非通過在DNA 雙鏈斷裂后引入插入缺失來使基因失活,而是特異性地靶向啟動子區域抑制基因的轉錄[49,79,80];而CRISPRa 采用dCas9 與不同轉錄激活域進行融合,通過化膿性鏈球菌sgRNA 或募集額外轉錄激活域以上調靶基因表達的特殊sgRNA 定向至啟動子區域[77,81,82],以此激活基因的表達,進而研究基因的功能。
5.2 CRISPR/Cas9 在生物育種中的應用
基因編輯已廣泛運用于水產動物、畜禽和植物的種質創制上。Wargelius 等[83]通過CRISPR/Cas9技術成功突變了大西洋鮭(Salmo salar)中脊椎動物生殖細胞存活的必需因子Dnd,獲得了不育的大西洋鮭,解決了鮭魚養殖中逃逸對野生種群遺傳干擾的問題。Ma 等[84]通過基因編輯突變了感染草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a)出血病毒GCRV 的必需基因gcJAM-A,從而使草魚獲得了抗GCRV 的能力。基因編輯也在農牧產品的育種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肌肉生長抑制素(MSTN)基因對肌肉生長發育具有重要調控作用。Crispo[85]和Wang[86]兩個課題組分別利用CRISPR/Cas9 技術,獲得了高產肉性能的MSTN 缺失羊和表現出“雙肌”表型的MSTN 雙等位基因敲除豬。MSTN 的基因編輯也在團頭魴(Megalobrama amblycephala)[87]、溝鯰(Ictalurus punctatus)[88]和黃顙魚(Pelteobagrus fulvidraco)[89]中得到應用,獲得了具有雙肌表型的新種質。CRISPR/Cas9系統也被廣泛應用于植物領域的煙草(Nicotiana tabacum)、擬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水稻(Oryza sativa)、小麥(Triticum aestivum L.)、玉米(Zea mays)和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等多種植物。Shimatani 等[90]通過將Cas9 與胞苷脫氨酶(Target-AID)進行融合,再由sgRNA 進行引導,從而在水稻中獲得多個除草劑抗性位點突變,并在番茄中形成了純合可遺傳的植株。Li 等[91]將nCas9 與tRNA 腺苷脫氨酶融合開發了植物腺嘌呤堿基編輯器,在水稻中進行點突變產生耐除草劑的水稻。這兩項研究同樣證明了CRISPR/Cas9 編輯對作物改良的可行性,擴展了植物中基因育種的工具。
5.3 CRISPR/Cas9 在動物模型構建和基因治療中的應用
動物模型是了解人類疾病發病機制和開發新型基因治療的有效工具。CRISPR/Cas9 具有效率高、速度快、可遺傳能力強以及簡單經濟等優點,在動物模型和基因治療中有著廣闊發展空間。Li 等[92]通過CRISPR/Cas9 系統構建了Uhrf2 基因缺失小鼠和雙基因缺失大鼠、小鼠模型。Xue 等[93]研究表明CRISPR/Cas9 可以直接用于修飾體細胞組織中的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為疾病模型的快速開發提供了一種新方法。2019 年Xu[94]等利用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編輯修飾了人成體造血干細胞中CCR5基因,修飾后的成體造血干細胞成功重建了人體的造血系統,且未發現脫靶效應和副作用。2020 年Stadtmauer 等[95]領導的一項多重CRISPR/Cas9 編輯改造的T 細胞治療癌癥的臨床試驗。結果表明,該療法在治療癌癥患者中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也為基于CRISPR/Cas9 系統在基因治療中的作用添加了又一例證。2020 年4 月Lu[96]研究團隊在《Nature Medicine》報道了使用CRISPR/Cas9 系統編輯非小細胞肺癌患者T 細胞PD-1 基因用以治療肺癌的首個人類I 期臨床試驗結果,表明CRISPR/Cas9基因編輯的T 細胞的臨床應用安全可行。這三項研究均在成體T 細胞上進行,并未在體內直接進行編輯修飾,因此并不會對其他組織器官及生殖系統產生影響。
6 總結與展望
迅速發展的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編輯技術正在現代生命科學中產生巨大的作用。該技術可以高效、通用和簡單地進行精確的基因組編輯、轉錄調控和表觀遺傳修飾。毫無疑問,CRISPR 系統具有革新基因和醫學領域的潛力,最近已有CRISPR/Cas9 基因編輯技術的相關的臨床試驗[94,95]。然而,在CRISPR/Cas9 潛在的脫靶效應、CRISPR 組分毒性作用以及Cas9 核酸酶的免疫原性上還需要更多的科學驗證。盡管可以通過不斷優化改進sgRNA 長度[43,44]、使用變體Cas9(nCas9[7,33]、dCas9[49]、xCas9[56]和spCas9-NG[55])以及開發新的單堿基[65,66]和雙堿基編輯器[71-73]來提高基因修飾的效率和特異性,但是還有很多基因編輯問題有待改進。因此,需深入研究CRISPR/Cas9 系統介導基因編輯的細胞內分子機制,以便其在各領域上得到適當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