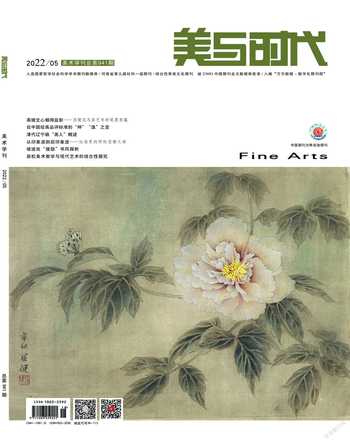細微處見真性情
馮道剛 吳敏
摘 要:莫蘭迪與阿利卡都是具象表現繪畫的代表人物,二者都融合了具象和表現特征,也都受到了東方藝術思想的影響。對莫蘭迪與阿利卡的具象表現繪畫從形式語言、內容題材及創作方法三方面進行比較,對研究當下中國繪畫藝術有著重要啟示。
關鍵詞:具象表現;靜物繪畫;莫蘭迪;阿利卡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一般課題“鄉村振興背景下寧波傳統村落文化景觀的再生設計研究”(Y201941500)研究成果。
莫蘭迪與阿利卡繪畫代表了20世紀具象表現繪畫發展的兩個階段,他們的作品都不是客觀地再現物的形態,而是將表現對象、視覺感受和繪畫語言共同融入繪畫,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對現實的事物進行表現。他們在藝術思想方面存在著某種認知上的相似點,但又各具特色。莫蘭迪雖以細小的靜物題材入畫,但反映的卻是整個宇宙的狀態,作品中的平面性和幾何造型是其繪畫創作的突出特征。阿利卡同樣熱衷于對靜物的描繪,但他卻運用一種即興的繪畫方式,依靠自我靈感的爆發,即通過興趣點去把握整個畫面的協調關系。
一、形式語言
形式語言是藝術家對客觀物象的表達方式,包括畫家創作的形式法則和思想觀念等。莫蘭迪的繪畫具有獨特的形式語言和表達方式,他通過對生活中常見的靜物的描繪,來尋找生活的真實意義,賦予靜物一種生命感[1]。巧妙的構圖、平視的畫面以及大面積灰色塊的運用,創造出一種靜謐且悠長的意境美。莫蘭迪作品中的主體往往出現在居中的位置,上下左右空間保持基本一致,畫面四周留有較大的空間。這樣的布局使人第一眼看過去感覺是物體真實地擺放在大家的面前,伸手就能夠輕易觸碰到,能產生一種對話的感覺。再者,瓶子垂直擺放,沒有傾斜,物體的重心直接平穩地落在橫向平面上,從縱向上也取得了平衡的視覺效果。另外,我們可以在畫面中看到許多平直線,這些平穩的線條給人以穩定和協調的感受。莫蘭迪運用這種構圖,和畫面中的形體、色調等其他元素相互結合,通過不斷磨合和嘗試達到了最完美的統一,取得了畫面的整體平衡。莫蘭迪的靜物畫不像倫勃朗那樣追求光影效果、明暗關系和立體效果,也不像阿利卡的靜物畫那樣,靜物擺放高低錯落,色彩富有層次變化。例如在莫蘭迪的《靜物》中,整個畫面構圖趨于平面化,以一種近乎平視的角度塑造豐富的形體,幾個瓶罐呈一字形在桌面上擺開,瓶子、罐子相互依靠,前后重疊。這些物體在畫面正中央的位置,并且左右留存的空間基本一致。為了強化畫面的表達效果,畫家特意拉長了瓶罐的形狀,在幾個藍白色的瓶罐后面以重疊、擠壓所產生的底圖正負形關系,突出后面帶把手以及帶條紋的罐子,以此變化來重構空間關系,減弱輪廓線和物體的空間透視感。如果畫面有所偏差,如物體比較偏向左邊擺放,那么在其右側,則會有與左側空間相互對應的物體陰影,作為空間上面的視覺壓縮。另外,莫蘭迪很少使用鮮艷亮麗的色彩,其大多數作品使用的是灰色調。灰色調給人一種沉穩和成熟感,含蓄而樸素,寧靜而又豐富。飽和度降低的目的其實就是在削減色彩對人情緒的強烈影響,讓人們觀看時能達到一種情緒上的舒緩和平衡。這些本來包含著各種情緒的顏色,比如危險或激烈的紅色、神秘的紫色、憂郁的藍色等,降低飽和度后就減少了給人帶來的視覺沖擊力,能營造平和、寧靜、神秘和深遠的氛圍,使人感到舒適,情緒激動的人看到之后會覺得舒緩,情緒失落的人看到之后會覺得治愈。莫蘭迪將三維的空間進行二維平面的壓縮,給人一種純粹的真實感受,這種平面性更加顯現了畫面中保持幾何形態的物象造型。
阿利卡以推陳出新的獨特繪畫語言活躍于藝術界,成為最具影響的當代藝術家之一。在觀察阿利卡的繪畫時,人們往往認為他的構圖很隨性,但仔細研究可以發現,他的每一幅具象繪畫作品都經過了仔細推敲,有很強的主觀意識和審美習慣。他有時將繪畫對象置于畫面的中間,有時偏于一角,有時采用高視點的構圖和抽象性元素。例如在他的作品《山姆的勺》中,一把銀制的勺子孤零零地躺在桌布上,簡單的幾個褶皺構成了兩個三角形的畫面,這種構圖既使畫面穩定,又形成了穩定的投影和素描般的明暗關系。光從上方側著進入畫面,一只勺子處于布的中間,光線似乎從上方照著勺子,從勺子的高光方向中可看到窗戶的投影,光在勺子上顫動,似乎還殘存著用過的溫度。這種寫生方式的形成,使如此平常的場景被畫下來。由此可見他一直追尋光的變化,以光塑形,以光設色。阿利卡將物象的固有色彩盡可能擴大化,追求其固有色,如其《在餐具柜上放著的兩個蘋果和三個梨》中,人們就能看到阿利卡對色彩運用的獨到之處。畫面中的兩個蘋果與三個梨是靜物本身的固有色,自然的光線照射在真實而平凡的物體之上,依靠忠實的觀察來挖掘自然的本真色彩,單純的色彩關系和對比協調關系使畫面給人一種簡潔明快之感,靜物的質感和造型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另外,在《毛巾與被單》和《三件襯衫》作品中,我們又能明顯看到其對大面積高純度色彩的運用,這一形式增強了畫面的視覺表現力,加上對光感的追求,畫家極力創作出一種主觀真實的存在感。除了固有色和高純度色彩的運用之外,阿利卡也喜歡用大面積的灰色和黑色來協調畫面,四類色彩之間相互促進與協調,共同形成了阿利卡繪畫的色彩特質。
莫蘭迪與阿利卡分屬于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家,其作品形式及語言存在一定的差異,尤其在構圖形式、色彩運用上存在著不同之處,但從具象表現角度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二者的作品又具有相似性,都通過各自的藝術語言去認識、感受和理解真實的存在。
二、內容題材
題材的選擇在藝術家的創作中具有重要地位,畫家的審美情趣往往都是通過題材表現出來的。莫蘭迪一生所畫的主題幾乎離不開我們生活中常見的那些瓶子、盒子以及杯盤罐碗等,這些日常生活中無足輕重的物品在他的油畫、版畫、水彩和素描里被反復呈現。莫蘭迪意識到對事物同與異探尋的重要性,以及這種題材限制所帶來的重復性,力圖找到這些純粹而單一的形體帶給我們的單純的審美愉悅感。莫蘭迪最初深受塞尚風景畫和靜物畫的影響,但經過興奮、茫然、探尋后,他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創作道路,開始了屬于自己的藝術語言探索。從莫蘭迪對靜物的描繪上,我們能夠看出畫面中只有幾個簡單擺放的瓶罐,沒有襯布、水果和其他形狀復雜的物體。這種題材的表現或許對于大多數藝術家來講都是一個難題,如何把握靜物之間的形體特征和空間關系,如何控制畫面的色彩關系和光影效果,都需要畫家用敏銳的眼光觀察物體的各種細節,只有這樣,才能發現它們的真實特征。為了表現物體真正的樣子,莫蘭迪選擇了這些最簡單、平凡的物體和形狀,故意舍棄了多余的表達,打破常規的對事物的認知和理解。莫蘭迪的繪畫空間呈現出一種更為純粹的感性,其隨著物體的聚集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事物與繪畫的關系如同光線與塵埃同時出現,讓我們意識到時間的流動性和空間的永恒性,以簡單而真誠的態度感受物象中的變化。
與莫蘭迪始終如一追求靜物主題不同,阿利卡的具象繪畫題材涉及多方面,尤其是他孜孜追求的肖像、風景和靜物。雖然阿利卡經歷過二戰,但他卻從來沒有畫過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品,他熱衷于人物肖像畫,熱衷于對熟悉的人的描繪,畫面中幾乎都是他的朋友、女兒、妻子和自己。他對人物主體的生動描繪喚起了人們對日常生活環境中的美的深刻認識。自畫像是藝術家內心精神世界的現實表達,是表現自我與探索自我的一種獨特的繪畫形式,阿利卡從各種角度的自畫像中展現個人的魅力,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種強烈的精神力量,傳遞著藝術家在短暫的時刻經歷的瞬間變化。除了肖像畫和靜物畫外,他經常描繪生活中的某些片段,例如《工作室的窗戶》表現的便是阿利卡工作的空間,掛在墻上的油畫、木質的樓梯和看似隨意擺放的畫布構成了飽滿的畫面。阿利卡的創作題材比較廣泛,即便是他熱衷的靜物,也與莫蘭迪有著不同,但二者又都來源于生活的片段。通過觀察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器物,有意識地截取生活空間中任何一個細微處,都有可能描繪出一個完整的世界。正是這種對待日常生活的情感,使得他們的繪畫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永恒感。
三、創作方式
觀察莫蘭迪的繪畫可以發現,其對靜物的觀察視角和畫面所呈現出的空間幾乎都是平視視角,這一獨特的觀察角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現物象的完整外形[2]。平視視角比仰視和俯視更能夠讓人獲得進入這一空間的感受。平視角度反映出畫家的一種世界觀,即平等、近距離地看待萬物。在水平畫面中固定使用一定數量的靜物,并根據畫面的需要適當增加或減少靜物的數量,調整或置換靜物的位置和朝向,改變或調整畫面的尺幅,靜物本身未變,但整個畫面卻呈現出不同的審美特征。平視角度能弱化距離感,使主體和靜物變得親近,甚至將自己的特性和靜物的特性相融合,并不是將客體與世界分離開來。空間、物象、光色都是趨于單純與概括,不追求豐富的細節,呈現出簡約的畫面感,單一而純粹的靜物通過秩序的變化而顯現出豐富多彩的畫面。莫蘭迪極力尋求這種簡約的創作方式,舍棄真實世界中物象的復雜層次以及表面的紋理特征、光澤反射和其他物理特征,將所看到的物體提取和概括成基本的形體和色彩,不再追求靜物之間的空間縱深感和立體感。莫蘭迪模糊了靜物的現實空間,削弱空間和物象的現實身份,即模糊了實在地面、桌面、室內或是曠野的現實特征[3]。同時,他的畫面質樸、簡約,極具東方意蘊。其繪畫觀念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的藝術是一致的,畫面中的靜物是作者內心感情的外化,畫面深處體現著中國藝術的審美精神。
阿利卡的繪畫從抽象轉向具象后,他一直思考繪畫方式和觀察方法的重要性。從阿利卡1965年以后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出,他試圖打破傳統的視覺模式,努力創作一種生活瞬間的記憶。在他看來,繪畫就是一種對生活中形狀不同的物體進行抽象轉化的過程。嚴謹的觀察使阿利卡慢慢放棄了以往創作中使用的繪畫語言,而逐漸以獨特的觀察方法與具象繪畫方式認識世界,這是他在對抽象繪畫的創作體驗后做出的新選擇。阿利卡的創作方式是獨特的,不需要提前在畫布上預設草圖,也沒有任何形式的底圖,而只需要找到他繪畫的興趣點,由這個點開始輻射到整個畫面[4]。阿利卡的繪畫作品大都依靠這種興趣點的創作方法來完成。將阿利卡的靜物畫與莫蘭迪的作品進行比較,可以發現莫蘭迪形而上式的畫面所傳達出的永恒性,阿利卡的寫生更傾向于記錄瞬間的視覺印象。阿利卡的繪畫形式不同于莫蘭迪那種較為平整的用筆,而是用一種“流動”的筆觸,使畫面用筆自由而隨性,快速捕捉事物的精彩瞬間。這樣的畫面效果給人一種粗糙而有力的書寫感,類似于中國畫的皴擦筆法,能產生生動的體積和質感,形成虛實相間的紋理效果。阿利卡的作品畫面中顏料處理得很薄,這樣的處理方法讓畫面的色彩有一種純凈的感覺,表達出一種純真、自然的效果。在色彩運用上,他一直堅持避免光源色對物體固有色造成影響,且在色彩選擇上傾向于一種簡約美,調色板上的顏料越少越好。阿利卡從抽象返回寫實時,繪畫方式的轉變并沒有給他帶來限制,而是將之前抽象繪畫所訓練出的形式感與自己對于“真實”和“存在”的理解運用到具象繪畫中,繪畫作品不僅是客觀上的寫實,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內在真實感受。
比較莫蘭迪與阿利卡的具象表現繪畫,我們能夠大致看出莫蘭迪的靜物繪畫首先是他要畫的東西,是一個選擇、認識和理解對象的過程[5]。而阿利卡選擇一種“即興”的創作方式,繪畫不在于記憶、理解和重構,而在于觀察。由此可見,他們的具象繪畫作品在形式法則、觀察方式和創作方法上存在著細微差異,各具特色,但在藝術思想方面又存在著某種認知上的相似點。
四、結語
莫蘭迪從生活的細微處著手,始終以靜物為創作的題材,熱衷于從平凡的世界中探討生命的意義,其作品從造型語言、形式法則、創作題材以及色彩的運用等方面都反映出莫蘭迪與眾不同的藝術審美觀。人們從他的畫面中可以感受到淡泊平和、寧靜致遠的氣氛,作品本身也達到了物我相融之境。阿利卡從抽象繪畫的思想中解放出來,感悟到繪畫的意義不在于記憶和想象,而在于平時的觀察,通過視知覺的方式去理解和表現世界。他們的兩種對世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豐富和發展了20世紀的具象表現繪畫藝術,也對當代的繪畫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啟示,使人們重新思考從平凡生活中探尋生命真諦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魯三妹.淺析莫蘭迪繪畫語言的生命感[J].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51-53,57.
[2]李秋.靜觀純粹:喬治·莫蘭迪繪畫淺析[J].藝術評鑒,2020(4):45-46.
[3]王羲.論《喬爾喬·莫蘭迪寫意油畫》[J].文藝生活·文藝理論,2011(6):193-194.
[4]湯寧容.可見之詩:阿利卡的具象表現繪畫[J].中國油畫,2021(5):77-78.
[5]康樂.重新理解與反思觀看:莫蘭迪與阿利卡具象表現繪畫的意義[J].美術界,2018(4):86-87.
作者簡介:
馮道剛,碩士,浙江萬里學院設計藝術與建筑學院教師。研究方向:人居環境設計。
吳敏,碩士,浙江萬里學院設計藝術與建筑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油畫藝術創作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