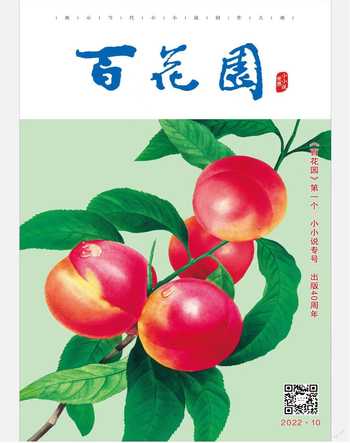竹園舊事(二題)
程韜光

賣煙記
一望無際的綠,蔥蘢厚實,令人絕望。沒有風吹來,悶熱,令人心躁。在夏日陽光的照耀下,少年弓著腰,在煙田里采摘著煙葉,順便拔掉雜草……
當我有意和無意地思鄉時,腦海里總是瞬間閃出這幅畫面。
我的故鄉是豫西南的一個煙葉大縣,竹園村的煙葉尤其出名。從兒時記事起,最辛苦的農活便是全家一起侍弄煙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煙葉是當地農家唯一的經濟來源和生活希望。
為了種出上好的煙葉,父親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去照看煙田,整地施肥、防病治蟲。采摘煙葉的時節,他便在煙田邊搭上窩棚,及時去除煙花,觀察煙葉顏色的變化。碧綠泛黃、大而飽滿的煙葉在微風中蕩起層層的波浪,讓父親感到欣慰:“這煙葉就像你們上學的試卷。一年一季,種煙也要交卷。”父親不僅是種煙的能手,更是方圓十幾里有名的炕煙匠。他烤出的煙葉均勻平貼,透著金色的質感,能夠賣出更高的價錢。所以,附近的煙農總是將自家的生鮮煙葉,托我父親在煙爐里烘烤。父親為人厚道,以為別人托自己是看得起自己的手藝:“半爐煙是炕,一爐煙也是炕,咱不落錢財落人情。”在他眼中,炕煙雖辛苦,卻是最好的營生。有一次,他喝醉了,把我弟弟叫到跟前,語重心長地吩咐:“長大了,你要有門養家的手藝。你們弟兄幾個,就看你是個干活兒人!我要把種煙的手藝傳給你。”弟弟在父親面前總表現出一副地道的農民形象,熱愛勞動。但聽了父親要傳他這門手藝,弟弟雖沒直接反對,卻在摘煙葉時故意摘下尚未成熟的葉片。父親大失所望:“看走眼了!又是一個假農民!”
記得有一年,頂著灼熱的太陽,我和父親拉著架子車走了十里鄉路,去公社的煙站賣煙葉。當時,賣煙葉的農人已是人山人海,都在炎炎烈日下排隊,等候質檢和過磅。我和父親擁擠在長長的隊伍中間,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動。饑渴和炎熱折磨著每個人,人們汗流浹背,心浮氣躁。賣冰棍的小販在旁邊不停地叫賣,讓我垂涎三尺,卻不敢向父親吭聲。
“你家的煙葉烤得真好啊,金黃厚實,均勻妥帖,一定能賣上大價錢!”周圍煙農的夸獎是對父親唯一的安慰。我能看出父親笑容的背后,充滿了對這車煙葉的無限期待。
終于輪到我家了!煙站驗級員也就二十歲出頭兒,穿著綢衫,敞著懷,打著酒嗝兒,走了過來。他用手掂起幾張煙葉,對著太陽瞇眼看了看:“嗯,還不錯!”父親湊過去,笑著附和:“是呀,張干部好眼力!您多關照!我家孩子多,可全指望著這車煙呢。”
接過父親遞來的紙煙,小張卻突然變臉了:“我秉公辦事,和你家孩子多少沒關系。”父親連忙低頭,不知道該如何接話。
一個瘦高的街痞青年這時走上來,嬉笑著對小張說:“這車煙葉還行,依我看,給定個二級吧?”然后,轉頭對我父親低聲說:“下次你賣煙葉時就找我黑龍,我幫你賣個好價錢!然后,你多少給我點兒煙錢。”父親有些不淡定:“定二級?這咋行?”小張眼睛一瞪,挺了挺肚子,指著車上的煙葉:“咋不行?就定二級。”他邊說著,邊從口袋里掏出驗級單便要填寫。父親急了:“這車煙葉,我不賣了!”小張吃了一驚,勃然大怒:“你敢不賣?”黑龍上前,用手指著父親:“你敢抵抗國家煙葉政策?今天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
父親滿臉屈辱!看到父親受了侮辱,我頓時火起,不知從哪里得到的勇氣和神力,竟將高我半頭的黑龍攔腰摔倒在地,和他廝打起來。黑龍的同伙正要過來圍攻,引起了排隊煙農們的憤怒。幾個膽大的農民也上前幫我和父親:“你們欺負農民算啥本事!”他們截住黑龍的同伙廝打起來,連躲閃不及的小張也不知道被誰打了黑拳,眼窩發青。煙站充滿戾氣,場面混亂不堪。
憤怒激發的力量讓我在與黑龍的搏斗中絲毫不落下風。他有些怯:“你小子練過功夫?”嘴上卻不服軟:“別打了,你以后跟著我混!”我回道:“我才不跟你混呢!”
在眾人廝打時,忽聽高處一聲斷喝:“都住手!”眾人聞聲望去,魁梧高大、黑臉環眼的派出所所長老侯正站在煙堆上,后面跟著煙站的李站長。老侯又吼了一聲:“你們要造反嗎?”都是賣煙葉的農民,沒人要造反,便都住了手。我也站起身來,黑龍沒羞沒臊地讓我把他拉起來:“不打不相識,以后咱們是朋友了!”
老侯是老革命,人正派,有威望。他瞪著牛眼,從煙堆上走下來,對著那幾個街痞青年呵斥:“你們想干啥?私販煙葉是犯法,知不知道?”又盯著驗級員小張:“活該!”小張的綢衫不知何時被撕破了,胸前多了幾道滲血的抓痕。老侯說:“你私自壓級,是犯罪!”小張頓時收起了往日的傲慢:“侯叔,沒有的事兒。”顯然,他與老侯有些交情:“我爸還說過幾天請你喝酒呢!”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見老侯向我走來,父親終于爆發了:“你們官官相衛!”父親使勁兒攥著我的手:“咱煙葉不賣了,回去!”煙農們一聽這話,也都叫著:“不賣了,不賣了。”
“老程,親家,別置氣!”老侯在包村時曾經在我家吃過飯,對我父親有六個兒子,很是羨慕。他有五個女兒,沒有兒子。微醺時,他還說要在我家選個女婿。此時,他叫了一聲“親家”,讓我父親眼圈發紅,想掉眼淚:“侯干部,高攀不起啊!”老侯笑了,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這小子,中!身手不錯,又疾惡如仇,將來……做我的女婿,接我的班!”他這么一說,讓圍觀的煙農們也笑了起來:“侯干部可要說話算數!”老侯大咧咧地回著:“算數!”大家又笑:“看得起農民,這才是好干部!”一場風暴頓時化作無形。
看著老侯遠去的背影,煙農們又自覺地排好隊,等著賣煙葉。小張滿臉通紅地低著頭,跟在李站長的后面,看著戴眼鏡的站長仔細地驗著煙葉,他負責記錄。黑龍依然咋咋呼呼地跑前跑后,卻已經沒有人搭理他了。他顯得很無趣,跟我套起近乎,問我跟誰學的拳路。我忍住笑,說:“我是從書上學的。以后,你多看些書。”他狠勁兒地點頭。我家的煙葉最終被定為一級,多賣了二十六元五毛錢。拿到了錢,父親破天荒地去供銷社“奢侈”了一把,給自己買了盒“黃金葉”紙煙,給我買了一根冰棒和一支鋼筆。而且,父親竟然還遞給了我一根煙!要知道,此前他是根本不讓我摸煙的。我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是個勞動力了!
許多年后,我回故鄉,正巧遇見小張——當然現在已經是老張了。他見我竟很親熱。他說:“侯叔走了!不過,黑龍現在發達了。他從農學院畢業后,弄了個豬場,成了豬狀元!豬肉漲價,他跟著數錢。他經常說,當初多虧聽了你的話,多讀了些書。”聽他說著這些故人,我心里竟一漾一漾暖融融的,化不開的鄉情,說的就是這吧。
姐 姐
棉花開花的時候,我隨祖母去姑姑家小住。姑姑家與竹園一河之隔。那些日子里,我幾乎與表姐形影不離,而表姐一直在棉田里忙活兒。我熱愛棉花,開花的棉田像一片花海。小樹林般茂盛的棉花枝上,開著一串串雙層的喇叭花兒,純白色、乳黃色、粉紅色、紫紅色等多種顏色的花朵被鵝掌般的棉葉托著,引來成千上萬只蝴蝶和蜜蜂在棉田里起舞、采蜜和傳粉,空氣中散發著泥土和花朵混合的馥香。只是,此時也正值棉花蟲害的高發期,姐姐不分晝夜地勞作在希望的田野上。她常常在如水的月光下,背著噴霧器為棉花噴灑藥露和花肥。我為她提著燈,形影相隨。姐姐見我有些累乏,便略微直了直腰身,給我輕聲說著花事……
“……她的一雙小手幾乎凍僵了。啊,哪怕一根小小的火柴,對她也是有好處的!”姐姐站在月光下的棉田里,低聲為我背著《賣火柴的小女孩》,“哧——!火柴燃起來了,冒出火焰來了!她把小手攏在火焰上。多么溫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簡直像一支小小的蠟燭……”姐姐的眼里已泛著淚花:“弟,姐有一個夢想:將來有一天,把棉花種滿天下,讓所有的小女孩兒都不再受凍。”她略帶激昂地望月述志時,面若皎月,目若燦星,是多么圣潔和美啊!我說:“姐,你真好看!”姐笑了:“我說胡話呢!”彎腰在我額頭親了一口,順勢屈身去為腳下的棉株補肥。“不說胡話了,姐教你種棉花。”她撥開一條棉枝,“你看這株棉被旁邊那棵高的棉株壓住了,就好像被欺負了。姐最不喜歡以大欺小,我要為它多施肥,讓它快點兒長。”姐姐再一次揚頭看那月亮,又低頭看我,竟羞澀起來:“要是姐姐將來嫁人了,受婆家欺負了,你咋辦?”我咋辦?光聽姐姐這么說我就心痛。姐姐還在望著我。我想了想,說:“先把你接回我家!再說了,姐這么好,誰會欺負你呢?”姐忽然哭了:“弟真好!”她俯身折去身邊棉株上的雜枝:“我的雜念太多了。記著,一個人在長大的過程中,要有目標,不能有太多雜念。就像這棵棉株,只有主枝才能掛上棉桃,結出棉花。”
夏末時,棉株已經長得茂盛,枝條粗壯。棉枝上結滿了青玉般的棉桃,沉甸甸的,微風一吹,上下擺動。在我眼中,這些棉桃似乎在向姐姐致意,也在向我告別——我要回去上學了。在棉田邊告別姐姐,她舍不得我——那個曾在夜晚為她提燈的人!她緊緊地摟著我,低聲說:“待到棉桃開嘴的時候,你來幫我一起收棉花,一起用雪團似的棉花去溫暖冬天,一起去裝飾這個世界。好嗎?”多年后,我想這個姐姐真不該在那個年月生落在農家;或者,裝滿憂愁的心,本就是詩意的淵藪。
在回家的路上,祖母才給我說,表姐不是姑姑親生的,所以,她從小就勤快,聽話。又說,姑父前幾年做糧食生意,折了本錢。若非侯家幫忙,就過不了那道坎兒。姑父也是義氣人,與侯家喝了一場酒,就把表姐許給了侯家在新疆當兵的兒子。表姐長得好看,又勤勞善良,姑姑私下里以為,侯家的兒子根本配不上表姐。姑姑心疼表姐,要用今年的棉花為她多做幾條新被,算是陪嫁。祖母的話,讓我隱隱地為姐姐傷心。
霜降過后,我便來看姐姐和她的棉田。早降的嚴霜將棉花的葉兒染成五顏六色,炸蕾吐絮的棉田里,一朵朵白絨絨的棉花開得正旺。星星般的棉花、玫瑰般的棉花簇擁著姐姐,我看見姐姐的手和臉龐被棉花映得潔白,姐姐的眼睛被棉花照亮,姐姐是棉田里最美的花!見我應約而來,姐姐很高興,讓我陪她去鎮上的棉站賣棉花。姑姑好像有些顧慮,對姐姐說了句:“城里人,咱攀不起。你們早去早回吧!”烏云涌上姐姐的臉,我在姐姐的臉上看到了云層里欲落的雨滴。
姐姐喜歡上一個棉花技術員。他叫楊樹,是下鄉的知青,瘦瘦高高的,長得白凈,還真像一株白楊樹。他在輔導姐姐種植棉花時,死勁兒地愛上了姐姐!甚至,沒有隨著大批知青回城。見姐姐來了,他連忙回辦公室換上新衣服,這才站在棉站門口和姐姐說話。“我聽說了,過幾天你要出嫁了。我該為你高興。”他的表情卻沒一點兒高興的樣子,眼圈有些發紅。姐姐靜默著。他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英雄”牌鋼筆,遞給姐姐:“這支筆送你,我以后也不能再給你寫信了。”姐姐輕咬嘴唇,接過鋼筆:“你不介意把這支筆送給我弟吧?”楊樹點點頭。姐姐把鋼筆放在我手心里,勉強地笑了笑,說:“我賣棉花時,存了一百元在棉站的賬上,留的是你的名字。算是為你送行了。”說完這話,姐姐還是忍不住哭了:“不是因為我,你早回城了。走吧,你是個有大出息的人,不能在這里耽誤前程。將來,你還能記得種花人的辛苦就好。”楊樹緊抿著嘴唇,最后說了句:“我忘不了的。”
姐姐出嫁的日子,冬日燦爛的陽光讓她分外好看。姐姐上車時,執意讓我坐在婚車的前座,認真交代我:“見了那個當兵的,你要不喜歡,就不讓姐下車。如果他家給的紅包太少,你也不要下車。”我不敢問姐姐為啥,只是點頭。結果,婚車剛進侯村,那個身著軍裝的人快步上前,對著婚車就是一個標準的軍禮。我自幼崇拜解放軍,哪見過這樣的場景?待婚車剛剛停下,就急忙下車,對著姐夫就嚷:“你以后不能欺負我姐!”姐夫笑了,一把將我抱起:“放心吧!軍人就是保家衛國的!”
婚后不久,姐姐便隨姐夫去了數千里外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她來信說,那里的棉田連綿不斷,像天上的白云。姐姐說,她熱愛棉花,她要把棉花種到天上,成為白云!白云棉花啊,都是山川穿不盡的衣裳!
[責任編輯 易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