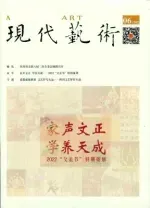關于“家學”的一點感悟
錢道遠

1942年冬,抗日戰爭勝利之前,黑云壓城,國土淪喪,生靈涂炭,是國家民族最苦難沉重的時候。我有幸出生在四川一個普通的錢姓家庭,是家里的第五個孩子、第四個男孩。今天,讓我倍感榮幸的是,由于有了吳越王錢镠和以錢謙益、錢大昕、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錢玄同、錢穆、錢復、錢鐘書、錢其琛等歷代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的輩出,錢氏家族已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家族,應該說是絕對名副其實的“家學淵源”了。
然而,同時也讓我深感遺憾和缺欠的是,我家僅系吳越錢氏家族江蘇無錫分支下的一個小小的分支。由于舊時代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凋敝及連年戰亂,這一小分支也早被沖得七零八落,逃奔及散居于四川及西南各地,各自艱難生息繁衍,甚至連完整的家訓、家學和家譜也難以找到。
父親作為一個早已定居蓉城的普通小知識分子,為了讓我們兄弟四人記住自己的家學、家教與家傳,特地給我們四人取名為“道震”“道澤”“道源”“道遠”。他告訴我們:太湖古稱“震澤”,我們兄弟四人名字的最后一個字加起來“震澤源遠”,就是要讓我們及我們的子孫后代永遠記住我們的根——我們這一支小小的錢姓支脈是從江蘇無錫太湖邊遷徙過來的。但除了這一點和父母以自己一生之求學謀業、處世成家、待人接物,對我們進行不懈的身教之外,其實并無其它更多形式上的東西存在。因此,可以說,從小父母和長輩對我們的家學、家教,就處于一種“無形勝有形,身教重言教”的氛圍和狀態中。
同樣,對于1971年出生,之后一直在峨眉電影制片廠職工宿舍里長大的錢路劼來說,他能在1977年考入成都石室中學,1989年在石室中學讀完初中高中后,考入北京電影學院。1993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分配到峨眉電影制片廠,并經過那時電影廠的由助理編輯、編輯、場記、助理導演、副導演、執行導演,到成為編劇、導演的嚴格規范的錘煉和成長的階梯,也走上了一條電影創作道路,也完全是“無形勝有形,身教重言教”的家學和家教的延續和結果。
因為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后中國電影的一個黃金創作周期,作為年輕創作人員的我,劇本創作任務本來就很重,而且自身的創作激情也噴涌高漲,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在了深入生活和劇本創作上,基本上沒有時間管他,更說不上有一套完整而持續的家學和家教了。教育的重任完全擔在他學校的老師和他母親的身上。
一個小故事:上世紀70年代初期至晚期,位于成都老西門外羅家碾的峨眉電影制片廠,還處于一片典型的成都平原市郊的農村田野中——溪水淙淙、蛙聲不斷、黃花遍野、稻浪滾滾。經過十年“文革”折騰、剛剛粉碎“四人幫”,全廠職工不多,僅一百余人左右,但所有職工的戶口均在郊區的蘇坡橋派出所。平時,買個手紙火柴、油鹽醬醋之類,要到隔壁戰旗大隊的鄉村小賣部去買(此戰旗大隊系當年羅家碾之戰旗大隊,非現在郫都區著名的戰旗村)。逢年過節,市里要統一供應白糖,城里人若是每人每月4兩,我們則只有2兩,因為我們是農村戶口。
很快,適齡的孩子們要上學了。正好峨影廠旁,有一所戰旗大隊所辦的村小。雖僅有幾間破屋,系當年典型的農村袖珍小學,但一出廠門,走幾段田坎便是,很近便。于是,峨影廠適齡的孩子們都去。1977年9月,6歲半的錢路劼也去了。因桌椅不夠,還得自己帶一個高凳和一個矮凳,去做課桌課椅。條件艱苦還是其次,讀了兩三個月后,有一天他放學回來,在家背誦課文。他媽媽發現有一句路劼總是背成“地道里有了——望孔”。他媽媽覺得不通,讓他拿書來看,并問他為何這樣斷句。錢路劼說,老師就是這樣教的,“地道里有了——望孔”。
他媽媽頓時便明白,那位年輕的臨時來“湊數”的“語文老師”,肯定是不認識這個“瞭”字,把課文《地道戰》這一課里的“地道里有瞭望孔”這一句,讀成了“地道里有了——望孔”。他媽媽頓覺問題嚴重,立即予以糾正,并從此加強在家輔導錢路劼。一段時期后,又將他轉至市區人民公園旁的小南街小學就讀。不久,由峨影廠工會出面,經與主管教育部門協調,其他孩子也全部轉學到了市區的勝西小學校……
講這個小故事,絕無貶低當年農村村小教學水平之意,當時“四人幫”之破壞和影響還遠未肅清,這樣的事屢見不鮮。只是想說,我們所應提倡的家學和家教,決不僅僅是父學和父教,而應該是集全家之力和全家之智的家學和家教,是見微知著、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的家學和家教,而且應該讓這種家學和家教,與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緊密結合、相得益彰,形成的一種完整、科學而持續的教育氛圍和教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