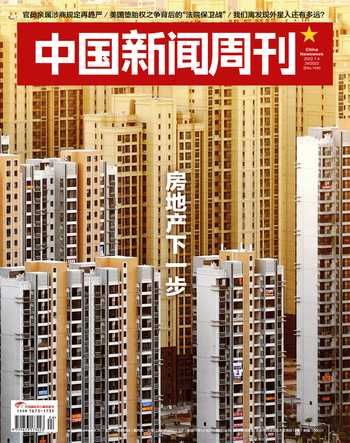為三星堆測年齡
倪偉

6月1日,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考古現場,工作人員正在清理8號“祭祀坑”。圖/IC
自從2020年三星堆再次啟動系統考古發掘以來,已經數次公布階段性成果,新發現的金面具、青銅大面具等文物已經逐步面世。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廣漢又一次發布新成果,宣布六座器物坑中已經發掘近1.3萬件文物。
另一個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新成果,實際上也有著突破性的意義。
四川考古院宣布,對近200個樣品進行測年后,發現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前1012年,相當于中原的商代晚期,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該院稱,這一結果解決了過去30年來關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
關于三星堆的一系列謎團中,年代是位于核心地帶的一個。在考古學家們看來,年代和性質,一直是解答三星堆文化終極問題的鑰匙。
由于上世紀80年代發掘時技術手段的不足,年代問題沒有得到較為確切的答案。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朱乃誠在一篇文章中所說,“長期以來,學界對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即三星堆文明何時形成、何時結束,整個三星堆文明延續了多長時間等問題,尚未進行過深入探索。”
2020年重啟發掘的是六座埋藏著大量文物的器物坑,器物坑是三星堆遺址中最受關注的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不過,確定了器物坑埋藏年代,對于研究整個三星堆遺址乃至三星堆文化,走出了重要一步。
為三星堆器物坑測年作出關鍵貢獻的,是碳十四技術。
負責此次檢測的機構,是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合組建的“考古年代學聯合實驗室”。聯合實驗室位于北大一幢灰瓦白墻的老房子里,今年3月剛掛牌成立,而實際上,北京大學的碳十四測年已經有近50年歷史。中國考古領域有兩家最為知名的碳十四測年實驗室,另一家歸屬于社科院考古所。
全國的考古項目如果需要做碳十四年代檢測,都要送到這兩個機構之一。據此前報道,北大每年要檢測的碳十四樣品達兩三千份。
三星堆前后陸續送來了200多份碳十四樣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考古年代學聯合實驗室主任吳小紅撰文稱,此次測年力求6座坑每個坑至少有6個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數據產生。首先在每個坑選出10份樣品,送到實驗室進行前處理:植物碎屑要進行酸堿酸的處理,以排除環境中的碳污染;骨渣樣品除了酸堿酸的處理之外,還要提取膠原蛋白,并進一步水解、離心、冷凍干燥,制備明膠蛋白。
這一過程中,不少樣品因為保存狀況不好,陸續被淘汰。這樣就需要補充新的樣品進來,所以樣品總量達到200多份。五號坑和七號坑樣品保存狀況不好,最終產生可靠數據的樣品不足6個。
也許是祭祀儀式,也許是掩埋廢品,也許是失火燒毀,三星堆器物埋藏坑普遍經過了火燒。吳小紅說,植物火燒后主要呈現三種形態,其中最適宜測年的狀態是:植物在燃燒中高溫脫水,但因為沒有接觸到氧氣,植物形成碳化塊,沒有充分燃燒成為灰燼。這部分有形的植物碎屑,大都質地相對緊實致密,很好地保存了植物原生的含碳組分,經過后期處理可以有效排除埋藏環境帶入的污染,有利于準確測年。
動物骨骼通常是很好的碳十四測年樣品,因為骨骼中的膠原蛋白基本不受環境的碳污染。然而三星堆器物坑里基本看不到成形的骨骼,都是骨渣,膠原蛋白大多降解殆盡,很可能是因為燃燒得不充分,又受到濕熱氣候、酸性土壤侵蝕。吳小紅說,目前得到的4個埋藏坑的38個碳十四數據,全部來自植物碳屑,沒有能夠從骨渣樣品中成功提取到膠原蛋白。
碳十四是碳的一種放射性同位素,首次發現于1940年。由于碳十四的半衰期長達五千多年,并且廣泛存在于有機物體內,所以根據生物體殘余的碳十四成分,就可以推斷其年齡,只要其生活年代不超過5萬年。
1949年,芝加哥大學化學教授威拉得·利比發明出碳十四年代測定法,11年后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5年,由中科院物理所調入社科院考古所的原子能專家仇士華、蔡蓮珍夫婦,通過自主研發設備,建立起中國第一個碳十四實驗室。北京大學的實驗室是1973年成立的。
碳十四檢測技術,就像一把伸向遠古的年代標尺,自然而然地在考古學和地質學中獲得了最廣泛的應用。在有碳十四技術測年之前,通過地層學和類型學,專家可以為遺址確定模糊的年代范圍,但只能是定性的,不可能定量地獲知具體年份數據。打個比方,學者可以判斷這座古墓是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的,那座城址是仰韶文化的,但并不知道距離我們是5000年、6000年,還是7000年。
仇士華曾說,在碳十四測年應用前,“史前年代學幾乎完全建立在主觀臆測或推論上面”。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在2000多個碳十四測年數據的基礎上,才建立起舊石器晚期以來中國史前考古年代框架。
1986年,三星堆一、二號坑在一座磚廠下面被發現,出土的器物使其“一醒驚天下”。發掘時沒有特意提取樣品進行測年,一、二號坑的測年是1997年做的。但也只是零星地檢測了一些樣品。

8號“祭祀坑”出土的銅神壇局部。圖/新華

7號“祭祀坑”出土的龜背狀網格形器。圖/IC
那時的年代結果并沒有一錘定音。關于三星堆的年代始終沒有停止爭論,各類說法層出不窮,大多數說法都傾向于將三星堆年代提前到商代早期——也就是說,提前到中國出現青銅文明最早年代以前,似乎是憑空冒出來的。
這種毫無根據的猜想,順應、助長了將三星堆打造成“神話”的趨勢。“以此為基礎,就產生出各種頗具想象力的說法,比如三星堆青銅文明是‘天外來客’。”吳小紅說。實際上,這些猜測都來自于民間,學術界并未出現過這類推斷。
究其原因,主要是沒有產生被廣泛信服的年代測年數據。當時采用常規碳十四測年法,所需的樣品量很大。兩座器物坑中的動植物經過火燒后,有機組分保存較差,很難提取足夠量的純凈有機組分。 以至于最終得到的兩組數據誤差很大,95.4%置信度的年代范圍大到500到600年,在考古學家眼中,不足以用于細致的討論。一、二號坑缺乏可靠的絕對年代數據作支撐,這就為廣泛的爭議留下了空間。
機會在30多年之后降臨。2019年,三星堆工作站的考古人員在一、二號坑復原模型的土石構筑臺邊緣,發現了類似于埋藏坑的轉角。隨即,6個祭祀坑重見天日,次年起啟動田野發掘。這一次,考古人員系統地采集到了碳十四測年樣品。而且這六座坑夾在一、二號坑之間,八個坑看似有緊密聯系,或許能同時搞清楚它們的年齡。
如今,國內碳十四測年技術與當年已有天壤之別。吳小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北京大學已配備加速器質譜儀器,使得測量微小碳十四樣品成為可能,可測量1mg的碳樣品,比常規碳十四測年方法可測碳量小了上千倍。對于三星堆的碳化植物碎屑,加速器質譜技術派上了大用場。
結果顯示,已經得到足夠碳十四年代數據的三、四、六、八號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010之間。就這一結論,吳小紅在文章中總結:“三星堆埋藏坑的埋藏年代處于商代晚期是沒有懸念的。若問是否可以說進入到了周初,目前從年代數據分布情況來看,這是有可能的,只是這樣的概率很低。”
年代雖已確定,爭議尚未平息。關于三星堆的疑問太多太多,此次發掘和研究能夠廓清的問題也十分有限。借用考古學家許宏的話,考古工作總是“不知道的永遠比知道的多得多”。比如這幾個被喻為“盲盒”的坑,其基本性質都尚未形成共識。
關于八個坑的性質,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偶然事件造成的“掩埋坑”,一種是有計劃多次建造的“祭祀坑”。“掩埋坑”意味著這些坑是一次性形成的,支持這一觀點的考古學者推測,三星堆古國遭遇了重大乃至災難性變故,以至于要把大量被毀的精美器物挖坑掩埋。具體是何變故?有“戰爭說”“政變說”“神廟失火說”等。
而如果是“祭祀坑”,則意味著埋藏器物是更為日常性的、儀式性的,是在較長時間內逐步掩埋的。持這一觀點的,包括發掘主持單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部分專家,1999年出版的正式考古報告就被命名為《三星堆祭祀坑》。
四川省考古院三星堆考古所所長冉宏林在論文中提及“祭祀坑”時,也得特意解釋:“本文沿用以往使用的‘祭祀坑’名稱,但不代表我們同意‘祭祀坑’所代表的K1和K2的性質為祭祀坑,相反,我們認為二者并非祭祀坑。”這意味著在四川省考古院內部,也存在不同意見。
關于器物坑的兩種不同觀點,在理解三星堆的一些未解之謎時,可能會導向不同的結論。
長期研究三星堆的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三星堆器物坑是“掩埋坑”。他向媒體解讀稱,此次測年結果落在公元約前1100年至1050年之間,正是商王朝衰落、周王朝崛起的年代,根據這個背景,三星堆的神廟被燒毀、埋藏坑的形成,可能與當時三星堆王國內部的紛爭有關。或許在選擇親善對象方面,有的貴族贊同依附商人,有的貴族主張支持周人,不同的政治主張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導致了三星堆國家的動亂。
而認同“祭祀坑”觀點的專家,則認為三星堆作為祭祀中心的國家性質,導致了過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社會財富消耗,為突顯奇異的觀念而營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大大超過了古國的承受能力,大約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權古國逐漸失去了控制,最終發生了嚴重的生存災難和社會恐慌。
那么,此次碳十四測年的結果,可以解決關于器物坑性質的爭論嗎?
測年工作負責人吳小紅指出,初步可以判斷三星堆所發現的幾個埋藏坑形成時間大致相當。目前還沒有辦法得到更加精細的年代數據,在這樣的情況下從碳十四年代數據的角度進一步比較每個埋藏坑之間的早晚關系,也是無益的。
通過此次測年,尚無法判斷這些器物是一次性掩埋還是有序分批掩埋,從而解決器物坑的性質問題。而且,這次的測年結論與此前根據地層學和類型學形成的判斷大體接近。
1999年的考古報告《三星堆祭祀坑》給出的結論是:一號祭祀坑器物埋藏時間應在殷墟一期末與二期之內;二號祭祀坑器物埋藏的時間應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間。殷墟即為商代晚期都城,這意味著,三星堆器物坑年代與商代晚期吻合,早已確知。
在此之前,專家通過三星堆器物與中原文物的關聯,推斷出三星堆與中原的夏商時代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有一些典型的器物線索,比如青銅人像頭頂的尊、手里的牙璋,以及大量龍的形象,顯示了中原文化對西南的深刻滲透。三星堆出土的銅尊、銅罍、銅瓿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玉琮來自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陜西、山東及華南地區都有發現,大量的金器則與半月形地帶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傳統相符。
“可以說,古蜀人與中原地區在核心價值觀或認知體系上有相當程度的契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盡管沒有被(中原)直接統治,但是在文化的認同方面應該早就是一個大的家庭了。”
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問題,僅僅研究祭祀區發現的8座坑還不夠,這些坑只能代表三星堆文明的后期。而三星堆早期的文化遺存,包括三星堆遺址西側仁勝村墓地、三星堆大城二期城墻,以及月亮灣燕家院子玉石器坑類遺跡、高駢坑類遺跡、月亮灣倉包包坑類遺跡等。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朱乃誠的推斷是,三星堆文明開始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前1500年之間,結束的年代在公元前1050 年前后,存在大約500年。
“我覺得三星堆的問題需要慢慢來,整個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是開始階段。”一位曾深度參與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專家說,關于三星堆的年代、來源去向、重要建筑等各方面分歧都很大,“還有很多現象非常重要,要一點兒一點兒去研究,不要急于去做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