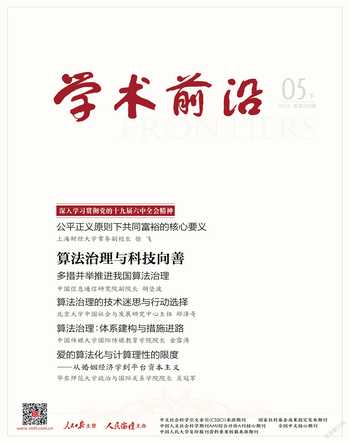日本地方自治發展中的法治變革及經驗借鑒
劉韜
【摘要】日本具有悠久的地方自治歷史,日本政府又分別在20世紀40年代和90年代通過改革對地方自治制度進行了發展。在制度變遷中,地方自治法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地方自治的法治變革,日本的行政體制的權力配置形成更為良好的對應關系,這對中國地方治理發展中如何處理集權與分權關系也具有一定的啟示借鑒意義。
【關鍵詞】日本? 地方自治? 法治? 變革
【中圖分類號】D73/77?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0.011
地方自治是現代日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中央與地方權力博弈的關鍵所在。有學者認為地方自治的發展體現了日本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日本的地方自治搞得比較成功,但這恰恰是和民主齊頭并進的結果,市町村自治與頒布憲法、召開國會大體同步,現行的地方自治法也是和新憲法一起制訂的。”[1]因此,對日本地方自治發展過程中的法治變革進行深入的研究,既有利于更好地認識和理解當代日本地方自治的特色,也對中國地方自治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日本歷史上的地方自治傳統及法治背景
日本是有著漫長自治傳統的國家。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聯同中臣鐮足等人發動政變并于翌年開始進行統治制度的改革,史稱“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的目的是維護以天皇為首的中央政權,建立以古代中國為模板的具有中央集權特色的封建國家,但是這種使多數人處在生存艱難前提下的社會體制顯然是無法持久的,“迫使90%以上的人民處于立即需要救濟的生活狀態的社會體制,無論其上層的貴族們如何歌頌繁榮,也是不久就要崩潰的”。[2]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逃離自己的土地投奔外鄉的豪族和富農,掌握地方土地的名主階層的權力逐漸擴大。在幕府建立以后,幕府對地方的統治都是通過設置他們在地方的代理人——“守護”和“地頭”來進行管理,“他們不斷侵吞莊園,將領國的國人變成自己的家臣團,逐漸發展為守護領國的守護大名”。[3]在室町幕府統治時期,幕府的實力日漸衰弱,大名成為各自領地內事實上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領土并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各大名紛紛加強了領地內的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富國強兵的政策,建立起規范而嚴厲的法治體系,堪稱日本地方自治法制建設的先導。
在更為微觀的鄉村治理層面,自治的傳統則更加久遠和穩固。“我邦原來設立的五人組、莊屋、名主、總代、年寄等制度中,本來就存在著自治制度的精神”[4],這里的自治制度就是建立在稱作“惣”的日本村落共同體基礎上的。從鐮倉幕府末期到室町幕府時期,“畿內、近國農村出現的村落共同組織,在名主等農村上層農民領導下,地位正在提高的中小農民階層組織起來進行鄉村自衛、管理灌溉用水和入會地”。[5]
江戶幕府時期,幕府建立了“幕藩制”的統治體制強化中央集權,這一體制的特征是幕府將土地分給各個藩國,在允許各藩具有一定自治權的前提下加強了幕府對各藩的統治。這種體制是守護將軍及其家族的牢固屏障,但對于代表地方力量的大名與下級武士來說,則是一種變相的限制。當武士離開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以后,他們在地方的影響力日漸衰落,便不再能夠對幕府的統治形成威脅。
現代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建立過程中的法治變革
江戶時代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明顯地體現出官僚化的幕府的集權思維與地方藩主追求藩內自治意愿的內在矛盾。而倒幕運動得以成功的先決條件,即為幕府的衰落和長洲、薩摩這些雄藩的傾力支持,因此,地方自治也成為明治維新一項基本的內容。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地方自治的法治變革。1878年,根據首相大久保利通的建議,被稱作三新法的《郡區町村編制法》、《府縣會規則》和《地方稅規則》正式頒布,這三部法律的頒布標志著日本地方自治進入了以立法為基礎的新階段。但這一自治體系只是給予地方有限的選舉和自治形式,最終目的還是要建立中央集權的天皇專制制度。“明治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目的是為了通過有限制的地方選舉和地方自由形式,建立中央集權的天皇專制制度的廣泛的社會基礎”[6]即使在那些有限的地方自治領域,地方自治體獲得的也僅僅是非權力性的服務工作,在行使這些有限自治權的時候,地方行政官員必須要在中央委派的監護人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完成。“在當時的地方制度中,中央政府的監督權得以嚴格保留,自治的要素未得到充分的保障。”[7]20世紀20年代,一批思想開化、具有現代民主思維的內務省青年官員認為在地方自治問題上,應該“致力于在地方實行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針對地方存在的現實課題摸索解決的方策”,在他們的推動下,地方自治制度曾經得到一定的加強。[8]遺憾的是,此后的日本隨著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興起,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得到無限加強,地方自治制度的完善無法沿著正確的道路持續發展。
二戰之后日本地方自治的法治變革。二戰之后,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推動之下,日本重新開始推動地方自治制度的建設。1947年發布的《日本國憲法》的第八章即為專門的地方自治條款,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第92條,該條款規定必須要根據地方自治的基本宗旨和法律規定設置地方工團組織并規范其運營事項。在憲法頒布的同時,日本《地方自治法》也于1947年5月同步開始實施。該法對之前已經形成的包括東京都制、府縣制、市制、町村制等進行了全面的修改與整合。這種整合改變了過去各地方之間相互隔絕、利益復雜多變的局面,但是也有觀點認為,新法的頒布并沒有體現各個地方、各個層級之間的差異性。在憲法—地方自治法的法治體系中,地方公共團體在制度上從以前的集權官僚制約束中獨立出來,成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自治體。但問題在于,在地方自治宗旨的兩個方面中,團體自治的保障充分卻凸顯出居民自治的缺陷。對于普通民眾來說,自主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途徑仍然是缺少保障的。
日本地方自治的當代困境與解決思路。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全球范圍市民運動興起的背景之下,日本基層治理中來自于居民和合作組織的謀求參與政治決策的呼聲也逐漸高漲。“隨著全球化的到來和冷戰的終結,國家權力的比重有所下降,自覺已步入后工業化時代的居民意識的變化,成為推動上述直接民主主義運動開展的動力。”[9]為了應對這種局面,避免地方自治制度再次被官僚集權所控制,20世紀90年代,日本開啟以對“地方自治的宗旨”所蘊含的理念的再理解為基礎的地方自治改革。日本參議院于1999年7月通過《地方分權一攬法》并于2000年4月開始正式實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1)以立法的方式確定中央政府和地方負責公共事務的組織之間的職能分工,轉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2)廢除機關委任事務的制度,將地方公團體的職能重新劃分界定為自治性質的事務與法律規定的受托事務。(3)將中央對地方進行干預的基本原則、類型、程序以及具體處理程序進行了進一步的明確,從而以全新的視角審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4)進一步推動權力的下放,將中央政府的權限下放到地方政府,或者將地方政府的權限下放到市町村等基層組織。(5)重新審視“必置規制”。對地方公共團體在人員、組織機構設置等方面的規定進行調整,進一步提高地方公共團體的行政效率。通過這一系列改革,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得到了明顯完善,地方行政服務的品質得以優化,居民的服務需求和參與愿望也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日本地方自治變革的總體特征與經驗總結
結合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各個階段的變革過程,我們可以將其實踐經驗總結為以下方面。
第一,以法律的方式明確中央與地方權力配置。日本憲法和地方自治法當中都有對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明確界定,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明確的憲法地位,進一步的權限分工、職能配置則通過地方自治法中的相關條款加以設定。在此基礎上,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間在進行權力委托和業務往來過程中始終能夠有清晰的標準。因此,明確中央與地方的法律關系,是實現權力合理配置的前提條件。
第二,以立法作為行政改革的保障條件。這種做法一方面以法律的力量推動改革的進程,可以更好應對改革當中所面對的阻力,減少失敗的風險;另一方面,由于采取法律預設的方式,改革的結果有具體的藍本可作依托,并且在成文法律的規范下,改革在完成之后出現反復和倒退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這樣就保障了改革的成果。
第三,減少干預、下放權力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關鍵。差異性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各國可以進行權力下放的尺度,但盡可能多地進行授權,在體制框架內給予地方公共團體更多的參與公共治理的機會,是提高行政效率和民主參與程度的有效途徑。日本政府在《地方分權一攬法》中所做的廢除機關委任事務制度等改革措施,其本質就是通過弱化政府的干預力度,給地方公共團體參與公共事務治理提供更多的自主選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現代日本管理的歷史演進與啟示研究——基于管理哲學的視角”、黑龍江省政府博士后資助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6YJC630074、LBH-Z17025)
注釋
[1][4]郭冬梅:《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和村落共同體》,《日本學論壇》,2004年第1期。
[2][日]井上清:《日本歷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頁。
[3]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歷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頁。
[5][日]竹內理三等:《日本歷史辭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頁。
[6]劉小林:《當代各國政治體制——日本》,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52頁。
[7]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250頁。
[8]郭冬梅:《日本大正民主時期新內務官僚的地方自治論》,《日本學刊》,2017年第1期。
[9][日]五十嵐曉郎:《日本政治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3~154頁。
責 編/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