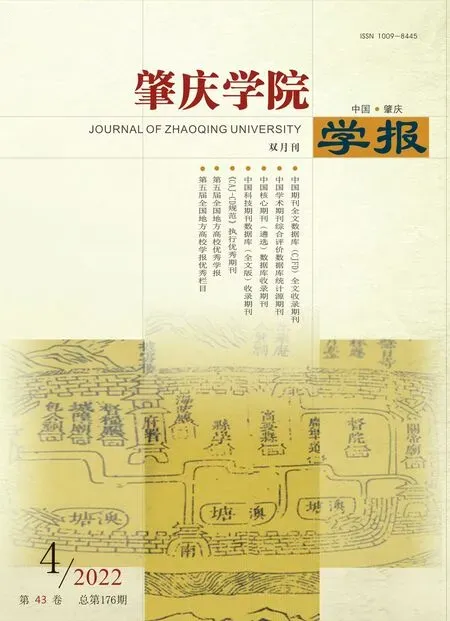論《西廂記》許淵沖英譯本的再敘事
楊嘉儀
(廣州工商學(xué)院 外語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850)
一、引言
戲劇是通過舞臺視覺與情感表達展現(xiàn)故事情節(jié)的文學(xué)藝術(shù),其敘事策略是戲劇創(chuàng)作的核心要素。在戲劇漢英翻譯過程中,如何動態(tài)對等地再現(xiàn)敘事風(fēng)格,一直是譯者關(guān)注的焦點,也是譯作成敗的關(guān)鍵。中西文化交流推動了中國戲劇典籍的外譯,如《牡丹亭》的國內(nèi)外不同版本、類別的英譯本已逾二十余種[1]iii。《西廂記》被十幾位譯者以全譯本、改譯文、英文劇本等形式翻譯出版。新譯本競相涌現(xiàn),但與小說和詩歌的翻譯比較起來,戲劇翻譯受到的關(guān)注較少,尤其是對古典戲劇英譯的微觀實踐研究內(nèi)容更少。《西廂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劇,也是演出歷史最長、數(shù)量最多的古典戲劇[2]387。同時,《西廂記》也是我國元明清三個朝代小說的菁萃合集《十大才子書》中的“第六才子書”,是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中的瑰寶。因其在藝術(shù)上的近乎完美,故又被選為四大古典戲劇名著之冠,有“西廂記天下奪魁”“古戲扛鼎之作”的說法。美國大百科全書稱其為“以無與倫比的華麗的文筆寫成的,全劇表現(xiàn)著一種罕見的美”[3]。本文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xué)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國際翻譯與跨文化研究學(xué)會副會長、著名翻譯理論家蒙娜·貝克(Mona Baker)教授提出“翻譯即再敘事”的理論為依據(jù),剖析《西廂記》許淵沖英譯的策略,從選擇性采用、標示性建構(gòu)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三個角度探討譯者在對原語文本英譯過程中所做出的處理,如何體現(xiàn)原文戲劇詩學(xué)形式,做到“傳神達意”,很好地向目的語讀者呈現(xiàn)絢爛的中國戲曲文化、文學(xué)經(jīng)典。
二、《西廂記》英譯本選擇
《西廂記》大約寫于元貞、大德年間(1295—1307),是元代著名雜劇作家王實甫的代表作。王實甫創(chuàng)作的《西廂記》,區(qū)別于唐代元稹所作的傳奇小說《鶯鶯傳》,講述了一個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禁錮而私下結(jié)合的故事,表達了人們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對美好愛情的追求。作品通過描寫崔鶯鶯和張生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提出“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理想。摒棄了庸俗的封建觀念,被賦予了鮮明的反封建禮教色彩,《西廂記》是一首有生命的人性戰(zhàn)勝無生命的禮教的凱歌。它的文辭以富麗華美受到人們喜愛,許多曲文都膾炙人口,廣為傳頌。明清以后寫婚戀愛情題材的戲曲小說,幾乎沒有不受之影響的,湯顯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紅樓夢》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均受其啟發(fā)。域外對《西廂記》的評價很高,男女主人公兩人經(jīng)歷了“邂逅——磨難——團圓”的過程,這類似于道德獎勵或救贖的敘述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最終完滿結(jié)合,不是借助皇權(quán)圣諭這種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類似于超越的基督教上帝,故而可能更受歐洲讀者喜歡。
從16世紀末開始,隨著航路的開通,傳教士來華,中國與西方開始了直接的交流。中國攝取外域新成分,不斷豐富自已,同時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輸送到國外。1897年《中國評論》首次提到《西廂記》,其外譯主要包括4個節(jié)譯本,6個改編本譯本和4個全譯本。筆者整理列出以下全譯本及其相關(guān)信息。筆者整理列出《西廂記》全譯本及其相關(guān)信息,詳見表1。

表1 《西廂記》全譯本信息
踏入21世紀之初,我國組織出版漢英對照版《大中華文庫》,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系統(tǒng)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國古籍整理和翻譯的重大文化工程,全面系統(tǒng)地翻譯介紹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籍,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歷史。2014年,許淵沖先生獲得了國際翻譯界最高獎項“北極光”文學(xué)翻譯獎,是迄今為止亞洲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翻譯家。許淵沖先生的《西廂記》英譯本于2000年被《大中華文庫》收錄,更是證明其重要的文學(xué)價值與歷史意義。筆者選取了《大中華文庫》收錄的許淵沖先生英譯的《西廂記》最新譯文作為研究文本,希望從新時期新視角去研究挖掘此譯文在再敘事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三、再敘事翻譯理論的生成與發(fā)展
敘事學(xué)理論受結(jié)構(gòu)主義的影響,經(jīng)歷了從古典敘事學(xué)到后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發(fā)展過程。蒙娜·貝克教授是首位將敘事學(xué)應(yīng)用于翻譯研究的理論家,她認為翻譯不是簡單地受政治和社會環(huán)境影響的活動,而是一個重構(gòu)的過程。Mona Baker 敘事理論發(fā)源于社會學(xué)和認知學(xué)的敘事理論,借鑒以Somers、Somers & Gibson、Bruner 和Fisher 為代表的社會敘事學(xué)理論,將翻譯作為敘事,闡述了翻譯如何參與國際政治話語建構(gòu)和國際傳播[4]23。蒙娜·貝克教授在一開始就指出,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zhuǎn)換,翻譯對戰(zhàn)爭、權(quán)力、政治和社會產(chǎn)生影響。翻譯甚至可以被定義為:譯者推翻原文而去構(gòu)建一個全新的“故事”[5]12。蒙娜·貝克提出了新的敘事理論,即“再敘事”理論,具體闡述再敘事理論如何充當翻譯原則對產(chǎn)出的譯文產(chǎn)生影響。譯者作為原文的介入者,其對原文的敘事轉(zhuǎn)換和介入必定會影響譯文。再敘事理論在政治和社會變革中扮演著重要的框架角色,甚至積極參與到“故事”的框架空間里。蒙娜·貝克在《翻譯與沖突——敘事性闡釋》提出“故事”即“再敘事”,敘事理論框架強調(diào)敘事的力量和功能,而不是其結(jié)構(gòu)構(gòu)成[6]19。人們生活在多變、發(fā)展中的環(huán)境里,在這個動態(tài)互動的空間中,參與者的再敘事活動總是在進行著,是一個不斷塑造與重構(gòu)的過程。
由于敘事是由敘事因素按照一定的順序組合而成的,譯者在進行翻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原文敘事要素進行調(diào)整或重構(gòu)的過程。譯者按照時間、問題或因果關(guān)系的發(fā)展順序,根據(jù)自己的偏好或習(xí)慣進行框架建構(gòu),此時原文本的因素可能就與目的語文本的因素不同。基于敘事特征,蒙娜·貝克教授提出適用于再敘事翻譯中的四個翻譯策略,分別是對文本材料的選擇性采用、空間建構(gòu)、標示性建構(gòu)以及參與者的再定位。本文將從其中三個翻譯策略分析許淵沖先生對《西廂記》的再詮釋。
四、再敘事翻譯策略在《西廂記》譯作中的有效性分析
對文學(xué)作品進行翻譯時,譯者總是或明或暗地強化或弱化參與表達的原文內(nèi)容。譯者需要思考如何協(xié)調(diào)原文本的敘事特征,從而在目的語境中進行敘事重構(gòu),引起讀者的反響。譯者可以通過多種手段在翻譯中進行建構(gòu)和重新建構(gòu)敘事,筆者主要從以下三種主要策略進行探討。
(一)選擇性采用
對于文本素材的選擇性采用是通過省略和添加的方式實現(xiàn)的,目的是要抑制、強調(diào)或者鋪陳原文中隱含的敘事或更高一個層面敘事的某些方面[7]173。發(fā)生在文本內(nèi)部的選擇性采用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學(xué)者尤其是文學(xué)翻譯研究者的關(guān)注。一個社會的行為模式和道德觀念可以反映在譯介外國作品過程中所進行的文本改寫。因此,譯者的選擇性采用策略會影響目的語讀者對原語作品所意圖傳達的道德倫理意義。
《西廂記》之所以成為經(jīng)典,在于它深刻的思想體現(xiàn)在近于完美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之中。王實甫表達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理想。這恰好照應(yīng)人類在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上所向往的婚姻自由的要求。愛情總是與自由平等聯(lián)系在一起而與專制格格不入的。許淵沖先生的譯本在主人公人物形象塑造上,堅持“有情”,他本人在訪談中也多次提出自己對愛情的向往,歌頌以愛情為基礎(chǔ)的婚姻。把難以言喻的愛情體驗提升到禪理的境界,是《西廂記》淺而能深之處,不僅僅是“郎才女貌”,更沒有“門當戶對”等財勢的考慮,強調(diào)了男女之間感情上的和諧融洽。在選擇性采用方面,尤其突出表現(xiàn)在張生和鶯鶯的幽會偷歡部分。由于寫得比較刻露,《西廂記》曾被人詬病,被譏為“濃鹽赤醬”。
比較東西方的愛情故事,可以說東方的情人更加含蓄婉轉(zhuǎn),西方的情人更加直截了當。王實甫對此的描寫是通過審美體現(xiàn)的,比如“軟玉溫香”“春花弄色”“露滴牡丹”,等等,許先生把直譯與意譯有機結(jié)合,遵循目的語表達習(xí)慣,適時添加,把原文中的比喻“柳腰”“花心”加上物主代詞“her”,不直白淺露,超出了生物水平而升華到精神層面,也體現(xiàn)了中國區(qū)別于西方開放性描寫的較為含蓄的禮節(jié)文化傳統(tǒng)。在翻譯曲子的時候,元曲使用到韻腳,許淵沖先生都會在同樣的位置使用韻腳。許先生在力圖保留原文形式美的同時,運用深厚的文學(xué)功底,創(chuàng)造押韻美,如表2 中“untie, shy, eye, nice, paradise, dyed,side”,“drips, sips, lips”。在唱詞和詩文等關(guān)鍵點的翻譯上,許譯文顯示出了更高的音韻美,這甚至比原文略勝一籌。

表2 第四本第一折《西廂記·酬簡》原文譯文對照
(二)標示性建構(gòu)
這里所說的標示是指使用詞匯、用語或短語來識別人物、地點、群體、事件以及敘事中的其他關(guān)鍵元素[7]187。用來指示或識別敘事中的關(guān)鍵元素或參與者的任何標示都提供一個詮釋框架,引導(dǎo)和制約讀者對當前敘事的反應(yīng)。其中,命名和標題是非常有力的建構(gòu)手段。
1.命名
以《西廂記》許淵沖譯本為例,人物的命名體現(xiàn)和表達了原作者王實甫和譯者的敘事立場。譯者在鋪陳和傳播文學(xué)作品敘事過程中發(fā)揮作用,并為此承擔相應(yīng)的責(zé)任。《西廂記》中的紅娘,是崔鶯鶯的丫鬟。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丫鬟作為下人,社會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加之重男輕女的觀念,她們往往是年輕的未婚女子,連姓名都不配擁有,所以對于戲劇《西廂記》中重要的配角,僅僅用紅娘這個名字指代。除了作為丫鬟外,紅娘在促成張君瑞和崔鶯鶯的愛情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是他們的傳話人,是他們在封建家長制層層重壓和阻礙下聯(lián)系的紐帶。紅娘這個詞的引申意義也由此而來,指代幫助有情男女終成眷屬的牽線搭橋人。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紅娘一詞的翻譯就值得斟酌了。許淵沖先生沒有按照現(xiàn)代漢語的意思將其簡單翻譯成“match—maker”,而是翻譯成“Rose”,在英文中,這是一個女子的名字,又指玫瑰花,正好對應(yīng)紅娘這樣一個妙齡女子。對于“紅娘”一角,有讀者認為她應(yīng)該有屬于自己的名字,就像鶯鶯和張生一樣,可以音譯為Hong,作為她自己獨特身份的代名詞。
2.標題
標題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用來有效地建構(gòu)或重構(gòu)敘事。通過標題翻譯重構(gòu)敘事通常伴隨著文本內(nèi)部的細微改動,以配合新標題的敘事立場。如《西廂記》第一本第四折“鬧斎”,普救寺法本和尚告訴紅娘,二月十五,佛供日,請夫人小姐拈香。中國古代有修齋供佛,善男信女做好事的做法。許淵沖先生英譯時,把“鬧齋”翻譯為“Religious Service”,從目的語讀者的角度闡釋“齋堂”指的是“按照約定規(guī)則進行公開崇拜的地方”,在中國是“寺院”,在西方是“禮拜場所”。在該場所作出的神圣或有宗教意義的行為儀式。筆者整理對比了《西廂記》五本二十折各個標題的漢英對照如表3。

表3 《西廂記》五本二十折標題原文譯文對照
《西廂記》五本二十折原標題都以二字為題,并且都是動詞結(jié)構(gòu),語言簡練且鏗鏘有力。許淵沖先生在標題的處理上,也是堅持“簡要”原則,加上英語介詞,不超過四個單詞。英文標題都是名詞結(jié)構(gòu),并且突出中心詞,為讀者閱讀的心理預(yù)設(shè)設(shè)下了很好的鋪墊,如第二本第三折鶯鶯母親崔夫人賴婚,譯者翻譯為“The Promise Broken”,完美詮釋了原文意思。第四本第三折中的“哭宴”,譯者沒有單純譯出“cry”或“tears”,而是用“farewell”概括了主要故事內(nèi)容。譯者在標題翻譯處理時能夠很好地把握原文敘事要素,巧妙地總結(jié)突出情節(jié)關(guān)鍵點。
(三)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敘事的關(guān)聯(lián)性可能不會允許其他敘事的“局部”直接地引入,一篇敘事包括組成整體的各個不同部分,但是這個整體敘事的可行性和連貫性取決于各部分的組合方式和共存方式[9]8。我們不可以不參照任何已有的結(jié)構(gòu)框架和該敘事所處社會文化背景來孤立地解讀敘事的單個部分,原作讀者如此,譯作讀者也是如此。譯者需要通過做部分或者全面的建構(gòu),并將這些建構(gòu)置于另一個新的時空背景中,以重構(gòu)新的敘事。
1.副文本中的再定位
《大中華文庫》收錄的《西廂記》英譯文前,許淵沖先生寫有5 620字篇幅的前言,使用目的語文化敘事世界的這個元素,即副文本,帶入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有助于目的語讀者解讀《西廂記》文本敘事的關(guān)聯(lián)語境。許淵沖闡述了《西廂記》故事的起源,與《國風(fēng)》的繼承與發(fā)展關(guān)系,及其與中國詩詞的傳承與發(fā)展。最后,把《西廂記》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人物與故事情節(jié)上進行簡要比較。許先生通過介入此副文本來引導(dǎo)讀者理解原文敘事中的人物定位。
2.話語內(nèi)的再定位
翻譯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文本特征都可以在微觀或宏觀層面上重新調(diào)整,以重新定位原文敘事內(nèi)外參與者之間的關(guān)系。Mason 和Serban 曾指出,這些調(diào)整不斷重塑譯者和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使譯者得以拉遠或拉近譯作和讀者之間的距離[10]290。第一本第二折《借廂》中的開頭部分是夫人和紅娘對白,法本和法聰對話。這些屬于散白,許先生也把這些話翻譯得非常口語化。由于各個人物的性格不同,許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們的身份差別。老夫人是相國夫人,說話相對文雅,說話又是以上對下,所以翻譯中那種命令的口吻就比較明顯。例如,夫人上云:“紅娘,你傳著我的言語,去寺里問他長老……問的當了,來回我話者。”許淵沖先生英譯為“Rose, go and ask the abbot……When you are told the time,come back and let me know it.”法本和法聰說,“山門外覷著”,這是相對書面語一點的說法,翻譯的時候許先生就沒有把它直接翻譯成一個“watch”(看),而是翻譯成“去而且持續(xù)看”的意思“Go and keep watch”。主持的那個威嚴感、命令語氣,就在這個詞的選擇中表現(xiàn)出來了。法本是一位老僧,上來之后自報家門,散白之中多少有一點韻腳,所以許先生翻譯的時候,就在兩句中加了一個韻腳。紅娘和法聰是老夫人和法本的下屬,所以,他們的回答“Yes, Madame.”和“Yes, master.”就符合他們自己的身份。許淵沖先生英譯時也力求還原人物身份的話語特征。
3.文本內(nèi)的再定位
王實甫創(chuàng)作了五本二十折的《西廂記》在元代雜劇中是首創(chuàng),打破了一本戲由一個腳色獨唱的限制,不僅一本戲里不同腳色都可以唱,劇中主要人物上場不受限制,又都可以唱,展開劇情,刻畫人物靈活。元雜劇的特點是一折中一人主唱,這個主唱的人每次唱的時候并不一一標明,因為約定俗成。這個習(xí)慣,我們現(xiàn)代中國人看起來可能都會有一點認知的難度,對外國讀者來說,這更是一個難題。再加上主唱并不是一人一唱到底,唱的過程中還有和其他人對話的情景出現(xiàn),主唱一個人唱了兩句,然后下面有人插進來說兩句話,緊接著不加任何標明,就又是原來主唱的人唱。許先生意識到這對外國讀者來說是一個難處,所以在翻譯唱詞時,不論原著標與不標,都會很細心地把唱者標示出來。比如第三本第一折《前候》,鶯鶯盡夜相思盡日眼,使紅娘到書院中看張生一遭并回來傳話。《寄生草》《賺煞尾》是紅娘唱的,唱了幾句之后,張生插話,紅娘應(yīng)答,這個原著中并無標明著這后半支曲子也是紅娘唱的,許先生在翻譯的時候,在后半支曲子前面加上了“She continues to sing”(紅娘繼續(xù)唱這只曲子)。同樣,在第一本第二折《借廂》里,張生唱完《中呂·粉蝶兒》后法聰和尚因聽不懂張生的意思而中間插話。原文中沒有標明接著是誰唱曲,但是許先生明確地注明“Master Zhang continues to sing”,此類例子在許譯本中比比皆是,明確地為讀者擬清角色的出場。
另外,在每一本的末尾,王實甫采用了六字排比句,總結(jié)概括前文的故事情節(jié),語言華美典雅,借用或化用古代詩詞中凝練的語句,具有詩化的特點,如表4。

表4 第四本第四折末尾原文譯文對照
許淵沖先生保留原語文本的格式特點,分別增添了原文中省略掉的句子主語“The lovers”和“Master Zhang”,再次體現(xiàn)出“讀者友好型”的翻譯風(fēng)格。
五、結(jié)語
古詩詞、古典戲劇是我國文學(xué)寶庫中的瑰寶,也是我們民族的文化精髓。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幾千年文明發(fā)展中創(chuàng)造的美學(xué)風(fēng)潮和寶貴財富,具有超越時代、跨越國界的巨大魅力。翻譯巨匠許淵沖先生歷時數(shù)十年,從浩如煙海的中華文化古籍中精選了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傳統(tǒng)文學(xué)經(jīng)典《西廂記》進行重構(gòu)敘事,在選擇性采用、命名、標題、副文本、人物話語以及唱詞等多方面采用了靈活的翻譯策略,對文中人物對話、唱詞注意形式與意蘊進行了再現(xiàn)。在對原文正確解碼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有效編碼,不僅力求保留原作形式藝術(shù)美,而且在英譯曲詞上做到的韻律美,更是近乎完美地傳達了原文對情的詮釋。該譯本體現(xiàn)了譯者用出神入化的翻譯手法把中國戲劇巨作《西廂記》進行英譯,讓海內(nèi)外讀者即使在英文語境中,也能體會愛情經(jīng)典,欣賞到中華古典文學(xué)的美與魅力。再敘事翻譯理論的誕生與發(fā)展不僅體現(xiàn)了戲劇傳播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強烈需求,也對我們在新時代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戲劇文化在世界各國人民心中地位的提高,會有更多中外學(xué)者助力于再敘事翻譯理論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