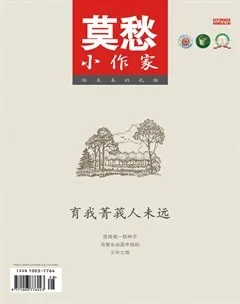母愛永遠是年輕的
1
端午前一天的下午,我在家看書。剛泡了一杯花茶,就接到母親的電話,說煮了粽子,讓我去拿幾個。放下茶,合上書,換了件衣服,我走出門去母親的住處。
過了支農橋,就看見母親沿著竹墅園的圍欄蹣跚而行。離了有二十米吧,我故意站定了,看著母親一步步地迎面走近。她抬頭看了三次,只一步之遙了,還是沒認出我來。我鼻子一酸,叫了聲“老娘”,趕緊上前扶住她。母親抬頭看看我的臉說,哦,是老二啊。我責怪她不該一個人出來,眼神不好,千萬別再跌倒了。母親小聲辯解道,太陽有點晃眼,不然還能看不出來是你?
母親今年九十歲了。身體羸弱的母親,晚年多災多病。七十五歲時,有一天突然暈厥。檢查的結果是肺癌,右肺中葉的腫塊已經雞蛋大小,沒辦法做手術了。我們四處打聽良醫偏方,遇上了江蘇省中醫院的國醫奚老。從每周一次,慢慢到兩周一次、一月一次,請奚老號脈開方。國醫圣手果然非同一般。奚老對癥下藥,不斷微調藥方,母親堅持煎服中藥幾年,肺部的腫瘤竟然漸漸縮小、鈣化了。八十三歲時,母親因胃癌動了手術。八十五歲時,因眼底血管堵塞,突然一目失明。八十八歲時,不小心摔倒,手臂骨折。每次安排母親住院治療,她都長長地嘆息一聲,說一把年紀了還再三再四地受罪干什么,在家等死算啦。一輩子都要強的母親,晚年就像個孩子,一生病就得我們去哄著,才肯就醫。
2
我記事起,就覺得母親是個外表柔弱、內心堅強的女子。整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父親似乎一直厄運纏身,免職、下放,一次次被揪斗、被審查、被關押,母親在擔驚受怕中帶著孩子們艱難地苦挨。母親跟人打交道,永遠帶著笑容,話語不卑不亢。表情柔和,聲音也柔和。只有老師來家訪的時候,母親才顯得局促不安。給老師遞上用紅糖沖泡的甜茶,把剛出鍋香噴噴的瓜子鋪在桌上,再小心地聽老師繞來繞去的話語。其實母親知道,孩子們在學校的表現不差,成績也挺好,老師家訪的原因,只是學期過半了,學費還沒有交齊。母親的殷勤招待、謙恭態度,讓老師也不好意思提學費的事了。
從我上中學起,父親就因肺氣腫、肺源性心臟病常年住院了。母親養豬養羊養雞養鵝,種地種菜縫補漿洗,既要竭盡全力讓兒女吃飽穿暖,又要照顧住院的父親。如今,母親偶爾也會抱怨,抱怨命運對自己不公,這輩子受了太多的困苦和委屈。她說自己命不好,生在重男輕女的家庭。母親是外婆的幺女。外婆連生五個女兒,連坐月子、吃雞蛋的資格都沒有了,幺女更不招待見,八九歲就要獨立負責割牛草、放牛。小牛犢子初駕犁杖,不大聽話,脾氣火爆的外公舍不得抽牛犢子,揮舞的鞭子抽在女兒的后背上。母親回家跟外婆哭訴,外婆只是陪著哭,一句安慰的話都不敢說。母親嫁了我父親,依然是看不到邊的苦日子。母親八十大壽時,環顧滿堂兒孫,說你爹從前常說“有兒窮不久,老太婆你以后會享福的”,現在日子好了,可惜老頭子沒有過上這好日子啊。
3
父親去世后,母親在老家的小鎮上住了十幾年。起先是三弟一家陪伴著。后來三弟的孩子進城讀中學,她堅持要獨自留在小鎮上。母親人緣好,每天都有一撥又一撥的老太太來陪她。有的是住在鄉下的,早上到鎮上買菜或者送孫兒上學,喝杯茶,拉拉家常,快到做午飯時才起身。有的是小鎮上的鄰居,午飯后就來跟母親玩一種紙牌游戲。老屋成了母親和閨密們聚會的俱樂部,母親在小鎮過得很開心。
四弟的孩子小的時候,母親進城照看孩子。母親想念小鎮的閨密們,孫兒開始讀小學時,又回到小鎮。直到母親突然暈厥,被查出身患重疾,才不得不接受我們的安排,到城里來生活。
母親不管到哪里,都會很快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在溧陽,住在學校的家屬樓里,鄰居都是老教師。滿頭白發、戴著眼鏡的母親,被鄰居們說像個教授呢。處久了,又說湯媽媽的言行舉止像老式的千金小姐,就給母親取了個“湯小姐”的綽號。老太太們傍晚結伴去散步,或者做了什么好吃的送上門,就直呼“湯小姐”。姐姐接母親去南京住了一個多月,我接她回溧陽時,老太太們一個個聚過來,拉著我母親的手,依依惜別。從樓道到小區門口的一百多米,走了半個多小時。我不知道母親是怎么學會了荒腔走板的普通話,與說著南京話的老太太們交流的。
母親年輕時手巧得很。家里男孩子多,衣服總是擊鼓傳花似的——老大穿著嫌小的衣服,給老二;老二的舊衣服再傳給老三、老四。衣服舊了,膝蓋、肘部等容易磨破的地方就一次次地打補丁。男孩子免不了調皮打架,揪領子還好,要是抓胸襟或是拽袖子,用力一扯嘩啦一個大口子,衣服就扯爛了。被父親發現跟人打架了,必定要被摁在長凳上,打得皮開肉綻。母親為了掩護我們,就把扯破的衣服悄悄地藏起來,趁父親不在家時穿針引線縫補勾連,或者借上街的機會,去她表弟家用縫紉機修補衣服。修補過的衣服,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破綻。
母親不僅有一手裁縫活,烹飪手藝也好。秋稻收割前,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是“山芋季”。一天三頓、日復一日,吃山芋噎得人真是懷疑人生。母親卻能把山芋變成各自花樣的菜肴和主食,順帶把春節消閑的零食,也都預備下了。因為母親廚藝好,哥哥姐姐的同學都愛找個借口,到我家來蹭一頓。
母親八十歲以后,視力減退,生活起居就由我四弟照料。耄耋之年的老母親,內心里依然住著一個講究生活質量的人。餛飩不能隔夜包,否則皮子就像面疙瘩,口感不滑嫩。魚無論紅燒還是熬湯,第一頓沒吃完,回鍋加熱她就不伸筷子,說魚肉“木渣渣”的。炒胡蘿卜要用刀切絲,炒出來才爽溜,而刨刀擦出來的胡蘿卜絲,一翻炒就糊了。四弟雖然曾經做過大廚,但面對母親的種種不滿意,也只能嘿嘿嘿了。
我去上大學前,母親教會我洗衣服、縫被子。工作以后,母親希望我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哪怕只有半間屋。她說年輕人難免浮躁,有個自己的地方,可以讓你靜下來。把心放寬些,你才會快樂。天塌下來都不要慌,也不要抱怨。我當了單位的一把手后,母親更是把“安守本分,按規矩做事”掛在嘴邊,時常跟我嘮叨。每次給母親帶點東西,她都要問,是你自己買的吧?千萬不要拿人家的東西啊。
其實,母親對所有子女都是千叮嚀萬囑咐。四弟有幾年在外地打工,母親會打電話去,囑咐他注意安全,照顧好自己,辛苦一點不要緊,生活會慢慢變好的。有的兒媳沒有工作,相夫教子一日三餐總會有雞毛蒜皮疙疙瘩瘩,母親借著去暫住一段的機會,耐心點撥開導。
4
如今,孫輩也陸續成家立業,去了不同的城市。只有過年的時候,全家才能一起吃頓團圓飯。讀書和工作,給了兒孫們看世界的不同視界,但我們卻很少與母親分享外面的世界。這幾年的過年團聚,母親還是那么的歡樂,但話語卻很少了。母親視力不佳,連電視也不看了。平日里關注的,只剩下兒孫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順利,親友和鄰居健康與否,生活的小城天氣晴朗還是飛雪。只有老家來人看她,或者我們主動提問,她才把藏著的往事慢慢地講給我們聽。
那天我去取粽子時,母親豎起三根手指,說用三個小時,摸索著包了三十二個粽子,兩兩相連的是紅豆粽子,獨個兒的是白米粽子。窗外的光投射在母親身上,那是母愛的光輝。
拎著幾個粽子回家,忽然想起一首聽過的歌:“母親已老,只愿陪伴在你的身旁。萬水千山,只愿換回你青春時光。夢回故鄉,母親的雙手依然芬芳 。少年萬里,母親的淚水日漸冰涼。浮生歸來,兒時的家鄉星海茫茫。縱情半生,江湖的快馬輕狂。人生回首,你已是白發如霜。”
母親已老。但母親的恩寵,讓我收獲了世間所有的美好。
湯全明: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多部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