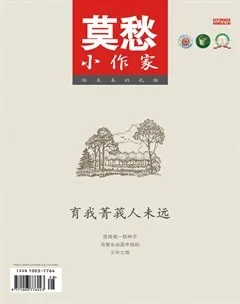希望的田野
我的家鄉是江蘇省高郵市一處偏僻的小村莊。父母出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們養育了六個女兒,都是農民,土里刨食,種田為本。養牛耕地、育種下秧、行船撐篙、取魚摸蝦,樣樣農活都不在話下。
1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大地推廣開來。勤勞善良的父母除了種好責任田,還承包了一條荒圩埂,帶著女兒們開荒種地。一年四季,圩堤上種滿了山芋、土豆、蘿卜等各種應時的農作物。人勤地不懶,那些山芋長得又大又多,運回家,機器粉碎,過篩,做成山芋粉,四時八節挑出去賣。其他水靈靈的瓜果蔬菜,大多裝到船上直接去賣,瓜果新鮮,不打一滴農藥,所到之處都搶著買……不到兩年,家里砌起了大瓦房,那可是莊上第一家大瓦房啊!
很快,鄉鎮工業也蓬勃興起,村里人年輕人進廠打工,農田拋荒潮一浪一浪地掀起。父母老實本分,篤信靠土地吃飯,靠勞動致富,一直守著莊稼。父親一邊種田,一邊開拖拉機耙田、開機泵船灌水、開大船在長江沿線跑運輸,日子一天天更好。
2
1991年,江蘇里下河地區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無數農田絕收。幸虧老家劉家舍的圩口沒倒,保住了糧田,留下一口吃食勉強度日。那年我被大學錄取,家人亦喜亦憂。父母已五十大幾,種田漸漸力不從心。招婿在家的二姐二姐夫的兩個孩子陸續開始上學,生活的重擔壓得人心頭沉甸甸的。
為了解開家中的困局,二姐咬咬牙壯著膽,承包了全鎮最低洼偏僻的黃泥工上一塊19畝大的地。二姐夫外出打工掙錢,二姐什么活兒都自己干,播種、施肥、鋤草、除蟲、收割、脫粒,不細說這些農活的繁重,僅黃泥工交通不便這一條,就把二姐累慘了。二姐用自行車或三輪車一趟趟地往返,累得肩頭脫了幾層皮,一季下來,原本高挑水靈的女子變得又黑又瘦,像一棵干枯的老樹。
一天傍晚,我放學回家,正趕上全家人農忙,將收割好的麥把挑上船,用船運到打谷場上。生產河道淤塞嚴重,二姐撐篙,二姐夫下河踩在淤泥中推著船向前走。遇到小橋過不去,只得將高于橋面的麥把一個個翻到橋上,船撐過去后,再將麥把裝回船上,繼續運到場頭。父母和我負責將麥把從船上運上岸,大姐夫、二姐夫負責喂把,將麥把輕輕放入脫粒機,滾輪在轟鳴聲中將麥把圈進去,又轟的一聲將秸稈吐出,麥粒落在脫粒機下方。大姐二姐戴著頭巾,一會兒拿鐵锨運麥粒,一會兒抬草垛。每個人都有條不紊地忙活著手里的活兒,我憋足勁不停地上船下船、運把解把,生怕耽誤進程,終于體力不支,眼冒金星,倒了下去。媽媽趕緊示意停機,扶我到場邊躺下,灌點涼水,待我蘇醒之后,他們又開始了流水線操作。待麥粒全部脫完,已是半夜,月色如洗,一家人懷著收獲的喜悅,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路上還不時打趣我這個學生娃吃不了苦,才做這么點活就累趴了。
3
2006年,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民種田的積極性重新調動了起來。
在外打工的四姐四姐夫也回鄉種田了,他們買了農用卡車,一邊種田,一邊做糧食經紀人,開著卡車幫村民收糧運糧,肩扛手提、爬上爬下,汗珠子能淌一大碗,一趟賺個二三百塊錢,心里就高興得不得了。一家子團團圓圓和和美美的,比什么都強!
2013年,“家庭農場”的概念在中國的農村大地上誕生,正好老家劉家舍有一片210畝農田發包。四姐四姐夫頭腦活絡、信息源廣,嗅到了商機,回娘家與大姐二姐商量,想將那片田包下來,姐妹們一起來搞家庭農場。
大姐、二姐都將頭搖得像撥浪鼓,“不行不行,種田不掙錢,種田太苦啦!”四姐說,如今都是規模種植,收種機械化,農資團購批發量大,有賺頭呢!本錢不用怕,大頭我來出,有錢一起賺。
大姐二姐終于被說服了,姐妹聯合起來種田,并申報了家庭農場。大姐二姐家都是種田的老把式,負責日常生產;四姐家聯系化肥農藥經銷商,買良種,聯系雇工、農機大戶,成本得到控制,勞動強度大大下降。父母樂當“后勤部長”,大忙時為工人燒飯做菜。姐妹倆給二老發獎金,父母越忙越開心。姐妹齊心聯合種田,各展所長,加上農機補貼、良種補貼、秸稈還田補貼、農田改造補貼等等國家對農業的補貼政策,姐妹們的收入如芝麻開花節節高。
四姐帶我參觀了她的農業機械設備,個個如數家珍,她開心地說,如今種500畝地還沒有以前種10畝地苦,甚至還想再租點田種呢!這不,這幾年我的姐妹、我的表兄妹等紛紛加入種田大戶的行列,家族種田總規模達2000畝。
種田人不再抱怨種田苦了,對這片希望的田野重又燃起了熱情。土地還是那片土地,農業科技化機械化吹響農業發展的號角,黨的政策如春風吹過田野,古老偏僻的村莊奏響現代化的進行曲。
韓粉琴:江蘇省高郵市婦聯副主席,曾在地方媒體做記者20年,后調任文聯工作4年,耳濡目染文藝風,舞文弄墨大自在。